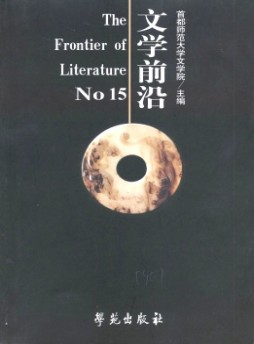文學審美結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審美結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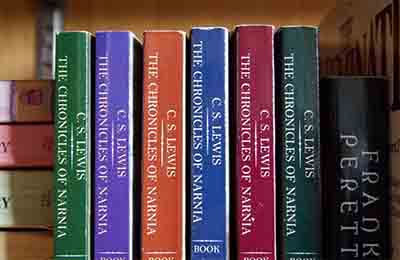
“文學終結”近幾年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從《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發表了美國知名學者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還會存在嗎?》以后,這種討論就開始了。米勒先生在這篇不長文章中說:
新的電信時代無可挽回地成為了多媒體的綜合應用。男人、女人和孩子個人的、排他的“一書在手,渾然忘憂”的讀書行為,讓位于“環視”和“環繞音響”這些現代化視聽設備,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現在也不是非現在、既不是具體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這兒也不在那兒、不死不活的東西沖擊著眼膜和耳鼓。這些幽靈一樣的東西擁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擾那些手持遙控器開啟這些設備的人們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還可以把他們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們所喜歡的樣子。因為許多這樣的幽靈都是極端的暴力形象,它們出現在今天的電影和電視的屏幕上,就如同舊日里潛伏在人們意識深處的恐懼現在被公開展示出來了,不管這樣做是好是壞,我們可以跟它們面對面、看到、聽到它們,而不僅是在書頁上讀到。我想,這正是德里達所謂的新的電信時代正在導致精神分析的終結。[i]
米勒相信:這是電信時代的電子傳播媒介的“幽靈”,“將會導致感知經驗變異的全新的人類感受”,并認為“正是這些變異將會造成全新的網絡人類,他們遠離甚至拒絕文學、精神分析、哲學的情書”,從而導致文學的終結。文學終結了,“那么,文學研究又會怎樣呢?文學研究時代已經過去了。再也不會出現這樣一個時代――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撇開理論的政治的思考而單純去研究文學。那樣做不合時宜。”[ii]
中國的年輕或不太年輕的學者對于米勒的關于文學的終結論深信不疑,以至于產生一種恐慌,有人相信文學在電子圖像時代必然終結,而文學研究的合法性也受到根本的威脅,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有的學者就提出,文藝學的邊界如果不越界不擴容,文藝學豈不要自取滅亡嗎?趁現在的“文學性”還在那里“蔓延”,在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中蔓延,在城市規劃、購物中心、街心花園、超級市場、流行歌曲、廣告、時裝、環境設計、居室裝修、健身房、咖啡廳中蔓延,趕快抓住這些“文學性”的電信的海嘯中的稻草,茍延殘喘,實現所謂的“文化轉向”,去研究城市規劃、購物中心、街心花園、超級市場、流行歌曲、廣告、時裝、環境設計、居室裝修、健身房、咖啡廳吧!文學已經在電信王國的海嘯中頻臨滅亡了。
米勒先生篤信德里達的解構主義,他的文學和文學研究終結論,并不是他自己的獨創,也是從德里達那里販賣來的。雅克·德里達在《明信片》一書中說:在這個電信技術時代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電信時代的變化不僅僅是改變,而且會確定無疑地導致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情書的終結。”[iii]
我讀了米勒先生的文章,很不以為然。我當時讀完他的論文的感覺是,也許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但過分夸大電子圖像的影響,文學的終結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2001年8月我們北師大文藝學研究中心召開了題為“全球化語境中文化、文學與人”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米勒也應邀來參加這次我們的會議。在會上我作了題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與米勒先生對話》的發言。米勒就坐在我的面前靜靜地聽了我的發言,在他的答辯中并沒有跟我辯論,他認為我的看法也許是有道理的。佛克馬則完全贊同我的意見,認為文學終結論是一個奇怪的問題。米勒自己在這次會上作了《全球區域化的文學研究》,他的主要論點是文學研究既包含全球性因素,也包含地域性因素。他認為來自一個地域文化的文學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處于另一個地域文化的人們所接受呢?這里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他不但沒有否定文學和文學研究的存在,而是在探討處于不同地域文化之間的文學如何實現相互理解的問題。他似乎把他發表在中國那篇文章的主要論點忘記了。順便說一句,2004年米勒又一次來中國,他在接受《文藝報》編審周玉寧的采訪時,說:文學是安全的。意思是文學不會終結。米勒改口了,可是他的文學終結論的中國支持者拒絕改口。這就使我為什么還要來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我在那次國際會議上的文章在刊物發表后,被好幾個刊物一再轉載。在那篇文章里,我一方面承認電信媒體的迅猛發展必然會引起文學的變化,我說:“的確,舊的印刷技術和新的媒體都不完全是工具而已,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影響人類生活面貌的力量,舊的印刷術促進了文學哲學的發展,而新的媒體的發展則可能改變文學、哲學的存在方式。”[iv]另一方面,我認為無論媒體如何變化,文學是不會消亡的,我提出“文學和文學批評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存在于媒體的變化?還是人類情感表現的需要?如果我們把文學界定為人類情感的表現形式的話,那么我認為,文學現在存在和將來存在的理由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誠然,文學是永遠變化發展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沒有固定不變的文學。但文學變化的根據主要還在于――人類的情感生活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主要不決定于媒體的變化。”[v]并認為米勒的“文學終結”論很難說服人。后來的發展是,我的文章遭到一些為米勒的“文學終結”論所傾倒的學者的嘲諷,說我提出的觀點根本不在米勒的層次上,言外之意是我的層次低,米勒的層次高。反正你同意米勒的看法層次就高,你不同意米勒的看法層次就低。在這個迷信美國學術霸權的時代,事情就是這樣。
“文學邊沿化”不等于“文學終結”
米勒和他的支持者的意見長篇大論,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的,但他們的觀念可以歸結為一點,那就是認為現在的社會已經處于電子高科技時代,在文化領域圖像的霸權已經勢不可擋,視覺圖像統治一切、覆蓋一切、吸引一切,那里還會有文學這種非圖像的文字的立足之地呢?文學該到消亡的時候了。(順便說一句,這些人是由文學的乳汁喂養長大成人的,為何現在那么急切地希望文學消亡?這豈非咄咄怪事嗎?)
更有的論者把目前文學的邊沿化與文學終結論混為一談。認為邊沿化就是文學的終結或者是文學終結的預兆。其實,關于文學邊沿化問題,多年前我就我反復說過,文學的確已經邊沿化,并認為這種“邊沿化”與中國上一個世紀的50、60、70、80年代相比,恰好是一種常態,那種把文學看成是“時代的風雨表”,看成是“專政的工具”,把文學放到社會的中心的時代是一種“異態”。把文學政治化,把文學放在社會的中心,究竟給文學帶來什么呢?經歷過“”的人們,應該都還記得,那時候,幾部“革命樣板戲”處于統治一切,結果把其他的文學都說成是“封資修黑貨”,8億人只能看8個樣板戲,這就是文學“中心化”的結果。這種情況發展到后來,連也受不了,1975年對鄧小平說現在大家“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vi]文學中心化的結果是沒有文學,這難道是正常的嗎?這難道不是文學“中心”化的悲劇嗎?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文學創作動不動就引起“轟動效應”的盛況,也是一種“異態”。那是因為由于思想解放運動,人們的思想感情空前活躍,文學更多作為一種思想解放的產物而存在,“文學為政治服務”的陰影并沒有散去,這還是反常的,是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果然,到了80年代中后期,文學就失去了“轟動效應”,也即逐漸“邊沿化”,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常態,當時我就說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為什么要把作為文學常態的文學“邊沿化”理解為文學的終結呢?其實文學“邊沿化”是文學發展的常態。一個社會常態應該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只有經濟目標和經濟的實踐真正成為中心的時候,人們才能滿足人的吃喝住穿這第一位的物質需要,這個社會的運轉才處于常態。當然,我并不是認為經濟發展就是一切,以經濟文明為中心,同時也要配合文化的、政治的文明的發展可見才是可行的。不難看出,文學的邊沿化與文學的終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為什么要把它們混淆起來呢?
文學生存和繼續生存的理由
隨著電視、電影、互聯網絡和其他新媒體的流行,文學受到挑戰,文學也在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的境況,這些很多人說過了。也許無需再多說了。為了回答米勒的文學終結的問題,為了說明文學生存的理由,似乎要從兩個層面來加以闡述:
第一層面,如前所述,文學是人類情感的表現形式,那么只要人類的情感還需要表現、舒泄,那么文學這種藝術形式就仍然能夠生存下去。這一點在我發表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的短文中以作了表述,這里不再贅述。但僅僅說“人類情感的表現需要文學”還不夠,也不足以說服那些文學終結論者。不論德里達還是米勒還是國內的某些年輕或不太年輕的學者,他們認定的文學終結的理由,是由于電子媒體的高度發展,電影、電視、互聯網、多媒體的發展,圖像(而不是文字)已經統治一切,占領一切,人們對電子圖像的喜歡必然超過對文字語言的喜歡,文學作為一種文字語言的藝術必然要終結,而完全讓位于電子媒介所寵愛的電影、電視和互聯網的日子遲早要到來。人類的情感表現不需要通過文學這種語言文字形式來表現,完全可以通過人們更為喜歡的電子圖像來表現。這樣一來,我們必須給出第二層面的理由,一個文學不會終結的獨一無二的理由。
第二層面,文學始終不衰的這個獨一無二的理由在哪里?我在《文學評論》2004第6期發表了一篇題為《文藝學邊界三題》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我認為文學不會終結的理由就在文學自身中,特別在文學所獨有的語言文字中。在審美文化中文學有屬于自己的獨特審美場域。這種審美場域是別的審美文化無法取代的。這種見解我想可以從生活于5-6世紀的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受到啟發: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有屬于自己的“心象”,而不是面對面的直接的形象。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說:“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這里是說文學創作的時候,作家想象和情感凌空翻飛,并且窺視著由想象和情感凝聚在自己心中的“意象”來動筆。這里的“意象”不是外在的直接的形象,是隱含了思想情感的內心的仿佛可以窺見的形象,是內視形象。“內視”形象是文學創作的特點之一。就是說,作家創作出來的形象,在創作前、創作中和創作后,都是內心視象,而不是如現在的電影或電視劇創作那樣,要根據演員這個直接形體形象去創作,或開始于內心視象,而最終要落實于直接的實體性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又在《隱秀》篇說:“隱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旁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隱”作為文學的體制,意義生于文字語言之外,好像秘密的音響從旁邊傳過來,潛伏的文彩在暗中閃爍,又好像爻卦的變化在互體里,珠玉埋藏在川流里,因此能“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無極”。這里說的是讀者閱讀欣賞的時候,所領會到的不是文字內所表達的意義,而是文字之外所流露出來的無窮無盡的意味。進一步說,讀著所面對的不是如電影、電視中的演員所表演的直接形象,而是文字語言之外的意義、氣氛、情調、聲律、色澤等。我覺得劉勰所論的正是文學那種由于文字的藝術魅力持久綿延于作者和讀者內心視像的審美場域,唯有在文學所獨具的這個審美場域中,文學的意義、意味的豐富性和再生性是其他的審美文化無法比擬和超越的。后來唐代王昌齡也說:“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會于物,因心而得。”[vii]在這里,王昌齡力圖說明,文學雖然也要寫物,但這物必須與人的心、神想相互交融,是因心而得之物,可見這物也是內宇宙之物,不是外宇宙之物,或者說這就是內心視象。這可以說也是對文學的獨特審美場域的很好的解釋。還有中國古人談到文學的時候,總是強調“文約辭微”、“言近旨遠”、“清空騷雅”、“一唱三嘆”、“興象玲瓏”、“虛實相生”、“不言言之”、“不寫寫之”、“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等等,中華古代文論優長之一,就是把文學審美場域的獨特性,說得比較細微和透徹。舉例來說,李白的《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如羅帷。”在這里,寫春天到來了,少婦思念外出的丈夫更佳殷切了,盼丈夫能盡快歸來。最后兩句,“春風不相識,何事如羅帷”,完全是少婦的內心視點的表現,我盼的是丈夫速歸,可我不認識你春風啊,你春風為什么進入我的羅帷之中呢?這一切在詩里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詩意盎然,但在影視圖像中如何可能呢?影視如何能把少婦這種心事如此有詩意地表現出來呢?
值得體會的是德國文論家萊辛在《拉奧孔》中提出的文學的“心眼”和“無明”這兩個概念。萊辛在比較詩與畫的不同的時候,替密爾頓辯護:“在密爾頓與荷馬之間的類似點就在失明。密爾頓固然沒有為整個畫廊的繪畫作品提供題材,但是如果我在享用肉眼的視野必然也就是我的心眼的視野,而失明就意味著消除了這種局限,我反而要把失明看作具有很大的價值了。”萊辛是在反駁克路斯的意見時說這段話的。按照克路斯的意見,一篇詩提供的意象和動作愈多,它的時的價值就愈高。反之,詩的價值就處于“失明”狀態,詩的價值就要遭到質疑了。萊辛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詩人抒發的感情可能不能提供圖畫,可能是朦朧的、意向性的,是“肉眼”看不見的,即所謂“失明”,它不能轉化為明晰的圖畫,更構不成畫廊,但這并不等于詩人什么也看不見,實際上詩人是用“心眼”在“看”,能夠看出濃郁的詩情畫意來,這不但不是詩的局限,而是詩的價值所在。萊辛的所謂“心眼”顯然是說詩人不是以物觀物,而是以心觀物,以神觀物,最終是一種“內視”之物,從這里看到的比之于圖畫那里所看到的更空靈更綿長更持久更有滋味。我們是否可以說,早在18世紀萊辛就在歷史的轉彎處在等待著德里達和米勒了。
按照我的理解,對于文學獨特審美場域的奧秘,還可以做進一步申說。在文學創作過程中,思想感情在未經語言文字處理之前,并不等于通過語言文字藝術處理以后審美體驗。在真正的作家那里,他的語言與他的體驗是完全不能分開的。不要以為語言文字只是把作家在生活中感觸到的體驗原原本本地再現于作品中。語言是工具媒介,但語言又超越工具媒介。當一個作家在運用語言文字處理自己的體驗過的思想感情的時候,實際上已悄悄地在生長、變化,這時候的語言文字已經變成了一種“氣勢”、一種“氛圍”,一種“情調”,一種“氣韻”,一種“聲律”,一種“節奏”,一種“色澤”,屬于作家體驗過的一切都不自覺地投入其中,經歷、思想、感覺、感情、聯想、人格、技巧等都融化于語言中,語言已經渾化而成一種整體的東西,而不再是單純的只表達意義的語言媒介。因此,文學語言所構成的豐富的整體體驗,不是其他的媒介可以輕易地翻譯的。歌德談到把文學故事改編為供演出的劇本的時候說:“每個人都認為一種有趣的情節搬上舞臺也還一樣有趣,可是沒有這么回事!讀起來很好乃至思考起來也很好的東西,一旦搬上舞臺,效果就很不一樣,寫在書上是我們著迷的東西,搬上舞臺可能就枯燥無味。”[viii]同樣,一部讓我們著迷的文學作品,要是把它改編為電影或電視劇,也可能讓人感到索然無味。我們不能想象有什么電影和電視劇可以翻譯屈原的《離騷》給予我們中國人對于歷史、君王和人生的沉思。我們不能想象有什么電影和電視劇可以翻譯陶淵明的那種“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歸隱的感情,同樣的道理,對于唐詩、宋詞的意味、意境、氣韻,對于有鑒賞力讀者來說,難道有什么圖像可以翻譯嗎?像王維的詩那種清新、雋永,像李白的詩的那種雄奇、豪放,像蘇軾詩詞那種曠達、瀟灑,任是什么圖像也是無法翻譯的。對于以古典小說為題材的電視劇和電影,如果我們已經精細地讀過原著、玩味過原著,那么你可能對哪一部影像作品感到滿意呢?不但如此,就是現代文學中那些看似具有情節的作品,也是難以改編為電子圖像作品的。你不覺得這些導演、演員、攝影師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無法接近文學經典嗎?并不是他們無能,而是文學經典本身的那種“言外之旨”、“韻外之致”,那種內視形象,那種豐富性和多重意義,那種獨特的審美場域,依靠圖像是永遠無法完全接近的。例如像臧克家的《送軍麥》中的幾句:
牛,咀嚼著草香,
頸下的鈴鐺
搖的黃昏響。
香氣如何能被牛咀嚼?黃昏又怎么會響?我們從這里立刻會感受到那詩意。但這詩意來自何方?來自內視形象和內在感覺。這種內在的形象和感覺,看不見,摸不著,只能體會和感悟,這些東西如何能變成圖像呢?或者在圖像中我們怎能領悟這種詩意呢?不但詩歌的內視形象很難變成圖像,就是散文作品中,盡管可能有外視點的形象,可能改編為某種圖像,然而散文作品仍然要有詩意。列夫·托爾斯泰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但他不認為寫小說就只要描寫圖畫,就可以不要詩意。他在談到《戰爭與和平》的創作的時候說:“寫作的主弦之一便是感受到詩意跟感受不到詩意的對照”。[ix]
還有,圖像(電影、電視劇等)對于被改編文學名著猶如一種過濾器,總把其中無法言傳的無法圖解的最可寶貴的文學意味、氛圍、情調、聲律、色澤過濾掉,把最細微最值得讓我們流連忘返的東西過濾掉,在多數情況下所留下的只是一個粗疏的故事而已。而意味、氛圍、情調、聲律、色澤幾乎等于文學的全部。我們已經拍了電影《紅樓夢》,隨后又拍了電視劇《紅樓夢》,據傳還要以人物為單元拍攝電視劇《紅樓夢》,但對于真正領會到小說《紅樓夢》意味的讀者,看了這些“圖像”《紅樓夢》,不是都有上當之感嗎?我們寧愿珍藏自己對于小說《紅樓夢》那種永恒的鮮活的理解和領悟,寧愿珍視《紅樓夢》的文學獨特場域,也不愿把它定格于某個演員面孔、身段、言辭、動作和畫面上面。也許有人會說,你所講的都是古典作品,要是現代的情節性比較強的作品,改變成電子圖像作品是完全可以的。可以是可以,問題在于改編者還能不能把被改編的現代作品的原汁原味保存下來。我認為這是基本不可能的,你沒有聽到嗎,多少作家指責電影或電視劇編導把他的作品韻味改編掉了。圖像就是圖像,圖像藝術的直觀是語言文字不可及的;但語言文字就是語言文字,作為語言文字藝術的文學,它的思想、意味、意境、氛圍、情調、聲律、色澤等也是圖像藝術不可及的。例如,現在有不少人說,魯迅的《野草》才是魯迅最優秀最具有哲學意味的作品,可至今還沒有任何人敢把《野草》中的篇章改編為電影或電視劇,為什么?因為電子圖像無法接近《野草》所描寫、抒發的一切。
我始終認為文學和其他藝術,都各有自己的獨特的“指紋”,就像我們每個人的指紋都是不同的一樣。生活中有不少人更喜歡電影、電視指紋,但仍然有不少人更喜歡“文學指紋”,也因此“文學人口”總保留在一定的水平上。既然有喜歡,就有了需要。既然有了需要,那么文學人口就永遠不會消失。而且“文學人口”還由于語文教育永遠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中小學的語文課本、大學的語文課本,絕大多數都是經過時間篩選的文質兼美的文學作品,語文教師要教這些文學作品,學生要學習這些文學作品。還有。社會上總有那么一群熱愛文學讀者,他們寧可不看那些或者是吵吵嚷嚷的或者是千部一腔的或者是粗糙無味的電影、電視劇,而更喜歡手捧文學書籍,消磨自己的閑暇時光。就是在年輕人中,這類人也是不少的。前幾年《中華讀書報》曾有一篇文章專門統計當前文學作品的發行量,很多文學作品印到幾十萬到上百萬部。恰好,今天我讀到了《參考消息》轉載了德里達的故鄉法國《費加羅報》網站2005年1月19日的一篇題為《法國十大暢銷消小說家》的文章,作者列了2004年文學作品的銷售情況,評選出十大暢銷小說家。我這里不想全文照抄。只抄其中發行量最大和最小的兩位作家。“1、馬克·李維(MARCLEVY):作品消量152.1萬冊。第一部小說《假如這是真的》2000年一經出版便引起巨大反響,作品被好萊塢看中,買走改編權,將由影業巨頭夢工廠影片公司搬上銀幕。去年3月出版的小說《下一次》是他的第四部作品,同樣在書店熱銷。李維擅長寫充滿懸疑氣氛、以真亦幻的愛情故事,其作品充滿想象力。……10、朱麗葉·本佐尼(JULIETTEBENZONI):作品銷售42萬冊。朱麗葉1963年開始寫作,83歲高齡仍然筆耕不輟,他擅長寫歷史題材作品,會利用歷史文獻資料,以細膩溫婉的筆觸,寫出扣人心弦的故事,擁有一批忠實的讀者。去年她出版了兩部小說《女巫的珍寶》和《艷情瑪麗》。”其他作家小說的銷售量介乎這兩人之間,有131百萬的,有123.7萬的,有111.8萬的不等。可以試想一想,在一個老牌的發達國家,影視圖像決不比中國發展得差,況且還有如此多的文學人口,那么在影視圖像還不那么發展的國家,文學的銷售量必然更大,文學人口也會更多。這就是說,無論中國還是外國,文學人口就永遠不會消失。既然文學人口不會消失,那么,文學研究就是必需的,文學和文學研究也就不會在電影、電視和網絡等媒體面前終結。
德里達和米勒的文學終結論,與他們主張的解構主義相關。解構主義力圖打破西方傳統的“邏格斯中心主義”,力圖沖擊形形色色的教條主義。看來,他們現在也要這種消解的態度對待文學和文學研究。然而他們遇到的困難是,他們在沖擊邏格斯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時候,還是要用邏格斯中心甚至教條主義所濡染過的概念和范疇。同樣,他們試圖消解文學和文學研究,但困難的是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仍然舉文學作品做例子,仍然要用文學研究的術語說明問題。這就像魯迅諷刺過的那樣,他們站在地球上,卻要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他們離不開,他們苦惱著,但是最終仍然站在地球上面。
對于中國學界的那些談論“文學終結”的朋友,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他們在談論文學和文學研究終結的時候,能夠不用文學做例證,也完全不用文學研究的名詞術語。然而,他們做得到嗎?
參考文獻:
[i]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會繼續存在嗎?》,《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
[ii][ii]同上。
[iv]童慶炳:《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社會科學輯刊》2002年第1期。
[v]同上。
[vi]見《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頁。
[vii]王昌齡:《詩格》,見《中國歷代詩話選》一,岳鹿書社1985年版,第39頁。
[viii]愛克曼輯錄:《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頁。
[ix]托爾斯泰《日記-1865》,見《列夫·托爾斯泰論創作》,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