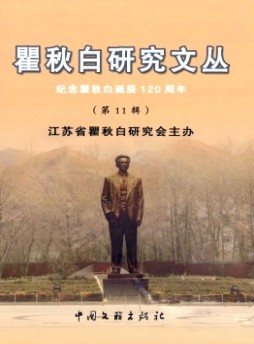瞿秋白文學對革命話語貢獻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瞿秋白文學對革命話語貢獻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對無產(chǎn)階級革命合理性的探求與論證
從政治倫理的角度講,無產(chǎn)階級革命是要以強制性的方式實現(xiàn)占國民人口大多數(shù)的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社會理想。然而問題不僅是按照政治生活的習性變革社會體制、確立的一個基本政治秩序那樣簡單,在革命政權建立的初期,為了擺脫國家的疲弱狀態(tài),往往需要在在一個具有行動力和執(zhí)行力的政黨的領導下,采取統(tǒng)一、有效的行動,對付一切階級敵人。也就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本質是要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在行動上,要以階級為分野,將無產(chǎn)階級以外的階級一掃而光。那么,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社會情況是怎樣的呢?中華民族受帝國主義幾十年的剝削,已經(jīng)切實感受到殖民地化的況味:“家族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破產(chǎn),舊社會組織失了他的根據(jù)地,于是社會問題更復雜了。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哲學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起,縈繞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在這種情況下,“有”變“的要求,就突然爆發(fā),暫且先與社會以一震驚的激刺。”瞿秋白引用克魯泡特金的話說“一次暴動勝于數(shù)千百萬冊書報”。①顯然,這種“變”的要求是依托于一定的社會狀況的,要進行社會變革乃至社會革命,“肯定革命的合理性”的這種價值判斷需要尋找其社會歷史依據(jù),對中國社會基本階級關系的論斷將導向人們對制度正義的追求。二十世紀初,舊的社會關系已經(jīng)無法維持,新的穩(wěn)定的社會關系尚未產(chǎn)生,如何在旁流雜出的社會思潮中確立新的社會理想呢?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對國外的異己理念僅是隔著紗窗看曉霧,我國與他國缺乏共同的社會土壤,那些西歐已經(jīng)在重新估定的所謂的“德謨克拉西”(民主思想)或者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所謂的“社會主義”等等,雖然蕩開了國人的視野,但難免泥沙俱下,讓人“飄流震蕩于這種狂濤駭浪之中。”①為“擔一份中國再生時代思想發(fā)展的責任”,瞿秋白成為前往俄國取經(jīng)者中的一員。中國是悲慘慘的生活、烏沉沉的社會,而經(jīng)過冰雪之區(qū),就可到“自由”之國。中國與俄國同是傳統(tǒng)因襲很重的國家,但是俄國卻通過十月革命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國家,雖然當時有種種扭曲變形的關于新俄的傳言,但也讓探索中的中國人看到了希望,瞿秋白前往俄國帶著兩個疑問:其一,“非現(xiàn)代的”經(jīng)濟生活里,如西伯利亞,如哈爾濱,怎樣實現(xiàn)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社會?其二,“殖民地的”剝削政策下之經(jīng)濟,依社會主義的原則,應當怎么樣整頓呢?①如果能認識真實的新俄,就為中國的新的社會體系的構建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最佳范本。瞿秋白在俄國發(fā)現(xiàn)了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社會圖景,“熏陶于幾千年的古文化”的“東方稚兒”到了餓鄉(xiāng),“受一切種種新影新響”,將俄國所觀察到的社會實際生活以及參觀游談、讀書心得、冥想感會等匯集為“心理的記錄的底稿”,形成“社會的畫稿”。--在他所描摹的俄國社會里,俄國正在實行所謂“軍事的共產(chǎn)主義”,即特殊時期“無物不集中”的高度集權制;在鄉(xiāng)村,貧苦農(nóng)民多分得土地,生活還象私有者。--物質水平發(fā)展的滯后與社會制度的優(yōu)越依然暫處一種不平衡的狀態(tài)之中,但是這種全新的分配關系已經(jīng)初顯了建立在社會財富公有的基礎上的政治權力關系的合理性。建立新的與無產(chǎn)階級專政相適應的無產(chǎn)階級新文化的要求呼之欲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具有合法合理的正當性由此成為一種基本的價值判斷。
2“心語”與“新語”的交替演進
與疾風暴雨式的社會革命相呼應,無產(chǎn)階級需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新文學以及新文化,因此在無產(chǎn)階級的文學中充滿了一種群眾式的狂歡。所以說,三十年代中國左翼革命文學的話語形式其來有自,它是以社會政治的需求為內容依據(jù)以及價值導向的。瞿秋白將記錄“心史”的“雜記體”與研究俄國歷史和社會制度的社會科學論文的體裁區(qū)別開來,自覺選擇了一種可以展示作者個性的紀實性文體,以紀實文學的形式來記錄在新俄的所見所想,追求坦誠、自然的論述風格。
2.1自我體認:時代風潮下的多余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明確指出,我們的出發(fā)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歷史唯物主義考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tài)中的人,而是處在現(xiàn)實的、可以通過經(jīng)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和發(fā)展過程中的人。現(xiàn)實的人的政治存在方式是階級。瞿秋白在兩個文本中記述了形形色色的從屬各個階層的人,上至俄共的最高領袖、政府機關不同部門的機要人物以及外交人員、記者,下至社會底層的小職員、勞工、農(nóng)民等等,他們在各自的位置扮演著自己的角色。瞿秋白也在尋找著自己的歷史定位,在《赤都心史•我》中,我們看到瞿秋白對自我有著清醒的認識,他雖來自破產(chǎn)的士的階層,但是,“我”不是舊時代之孝子順孫,而是“新時代”的活潑稚兒。自是小卒,卻編入世界的文化運動先鋒隊里。①可在追求個性解放、勇猛激進的同時,他對動蕩不安的現(xiàn)實社會又有一種無助感,他感嘆內在生命的“心智不調”,內心現(xiàn)實與浪漫相敵,現(xiàn)實的中國社會方方面面都處在一種“不助”個性發(fā)展的湍洵相激中,個體生命無從循著或傳統(tǒng)或現(xiàn)代的任何一條路腳踏實地、實練明察地發(fā)展,這樣,在“歐華文化”沖突中變成了既非傳統(tǒng)也非現(xiàn)代的多余的人。所以說,瞿秋白在這兩部紀實文學作品中并不是以全然的革命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他是以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身份,去體察時代與世情。從文學與文化的角度來看,因其跳脫傳統(tǒng)的寫作程式、沒有既定概念的規(guī)約和束縛,以及采用了別開生面的“心史”與“紀程”的形式,這兩部作品中透露出的作者個人的生活姿態(tài)與品位執(zhí)著與他的一線新聞報道一樣,在保留原生態(tài)的鮮活的同時也能帶有一種可貴的客觀,對社會場景與人物心理與行動的描繪都別具特色、頗有興味。比如他描寫在莫斯科聽列寧演講的一段:安德萊廳每逢列寧演說,臺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著人山。電氣照相燈開時,列寧偉大的頭影投射在共產(chǎn)國際“各地無產(chǎn)階級聯(lián)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lián)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又襯著紅綾奇畫,--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異的象征。列寧的演說,篇末數(shù)字往往為霹靂的鼓掌聲所吞沒。①他在俄蘇見到了列寧,贊其有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態(tài)度,感嘆“政治生活的莫斯科這次才第一次與我以一深切的感想”,而這個場景對此時的瞿秋白來說,是“新奇的”、“特異的”,他是帶著新鮮的觀感來描述這一共產(chǎn)主義運動蓬勃開展的現(xiàn)實場景的。我們可以想象,這個熱火喧騰的紅色場景是引起了瞿秋白內心怎樣的變化、讓他最終從革命運動的旁觀者進入革命的主流,并最終擎起引導人民進行革命的大旗。
2.2歷史參與:學理與性情兼具的個性化演繹瞿秋白在赤塔閱讀了赤塔共產(chǎn)黨委員會送來的書刊雜志,如《俄羅斯共產(chǎn)主義黨綱》、《共產(chǎn)國際》、《社會主義史》等,已經(jīng)粗略知道俄共產(chǎn)黨的理論。到了莫斯科東方大學后,更因為職務的關系對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多有研究。所以當他介入對新俄社會歷史的考察時,能在保持獨立審慎態(tài)度的前提下,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思考社會變遷的哲理。《赤都心史•三〇》描述十月革命勝利4周年紀念會盛況。再次寫到無產(chǎn)階級革命領袖列寧的光輝形象與卓越才華:“工人群眾的眼光,萬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寧身上。大家用心盡力聽著演說,一字不肯放過。列寧說時,用極明顯的比喻,證明蘇維埃政府之為勞動者自己的政府,在勞工群眾之心中,這層意義一天比一天增勝,一天比一夭明繚。”在對新俄革命形勢發(fā)展熱情描繪與對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目標及精神精準把握的同時,他也關注大的歷史進程下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精神創(chuàng)傷。比如《赤都心史•二三•心靈之感受》某村的村蘇維埃的秘書所敘述的農(nóng)民被迫從軍的觸目驚心的苦情,以及他屢經(jīng)困厄的遭際但是他卻通過忘卻小我的“為人服務”將煩悶的心緒轉為舒泰①--主人公身上的善良、豁達和無私等美好品質和人性的光輝在瞿秋白的筆下是那么深厚與真摯。這既是心靈的紀實,更是政治生活中最生動的場景。瞿秋白用主人公的具有人道主義色彩的現(xiàn)身說法側面印證了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的合理性。人生的溫情樂意在俄國由家庭的范圍拓展到社會,進一步說,赤俄革命后的社會生活,“混相異的社會為一”,如在《赤都心史•三十七•離別》中描述的場景那樣,女仆和博士兩個不同階層的人在新年到來之際可以攜手同歌。不僅是家庭,在更大的社會的范圍內,人們也可以部分階層地過一種“親切高尚優(yōu)美”的精神生活。①而現(xiàn)實的中國,相對的平等喜樂局限于家庭之內,家庭外則不外乎是麻雀牌桌與燒酒壺底,更不用說相當于俄國女役的中國“老媽子”與上層的高級知識分子歡歌暢舞了。瞿秋白不只一次地記述了新政下的俄羅斯人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們在物質條件匱乏,每天只有一點黑面包的情況下,依然載歌載舞,不改對文學與藝術執(zhí)著的熱情。其中,這種對普羅大眾的精神生活的由衷贊譽其實隱含著對中下層勞動人民的歷史主體性地位的確認,這種價值判斷隨著革命的繼續(xù)向前推進,逐漸演變?yōu)楦锩膶W中走向模式化的修辭策略以及政治要求。
2.3話語構建:形象與意象的空間拓展在瞿秋白對新的政權體制由感官認識到逐步深入的過程中,體現(xiàn)在文本中,就呈現(xiàn)出一種新的話語方式,并在敘事中生成了一種新的修辭品格。尤其是他對比喻、象征、對比等修辭手法的嫻熟運用,建立了語詞與革命間的新的聯(lián)系,并初步形成了一套頗具特色的革命話語體系。首先,他用晨曦、光明、紅色等象征革命的力量,用陰影、夜余、黑暗等象征衰朽的力量。在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下,強化兩者的對比,突出先進力量必然最終取締落后保守勢力的歷史必然性。在《餓鄉(xiāng)紀程•緒言》中,他描繪的中國的現(xiàn)實是“陰沉沉,黑魅魅,寒風刺骨,腥穢污濕的所在”,中國有識知識分子無法忽視這“陰影”的存在,但是“微細的光明”會給人帶來希望。“燦爛莊嚴,光明鮮艷,向來沒有看見的陽光,居然露出一線,那‘陰影’跟隨著他,領導著我。一線的光明!一線的光明,血也似的紅,就此一線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紅花染著戰(zhàn)血,就放出晚霞朝霧似的紅光,自鮮艷艷地耀著。①此時仍因襲著傳統(tǒng)士的階層的色彩的瞿秋白尚未踏入俄蘇的土地,也就無法全盤肯定這”紅“的色彩的意義。”紅“既是陽光的顏色,也是戰(zhàn)血的顏色,暴力革命式的社會變革讓他多少有些不適應,但他也不容置疑地肯定了這”紅“的色彩盡管讓驟見光明的人覺得不適應,但比黑暗的”黑“多少總含些生意。革命的進程是充滿了曲折和艱險的,在對革命形勢保持樂觀展望的同時,他也用具有鮮明色彩特征的形象化的語言表達了他對暴力革命某種程度的懷疑:“光明的究竟,我想決不是純粹紅光。他必定會漸漸的轉過來,結果總得恢復我們視覺本能所能見的色彩。--這也許是瘋話。”①將這“瘋話”和后來具有“左”傾色彩的革命文學聯(lián)系起來看,在特殊的時代環(huán)境下,“紅色”排他性地茁壯成長,“唯我最革”是備受推崇的價值取向,直到提出“百花齊放”,其他“色彩”才在革命話語體系中具備的合法性地位才被認可。瞿秋白的“瘋話”可謂是對未來的一種理想化的期許,同時也是一種充滿睿智的預見和警示。其次,紀實文學本身是一種敘事藝術,但因為瞿秋白對內心感受的捕捉與攝錄,文本具有一種靈動的氣韻,從而創(chuàng)建了一個具有浪漫的詩化色彩的藝術空間。在兩個文本中,進步青年對革命的向往,不僅是外在的政治要求,同時是生命內力的張揚的需要。“心史”與“紀程”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性化人物的心靈寫照與成長歷程,這種關注個人內心感受的對自我的敘寫,真實再現(xiàn)了“新青年”到“革命者”的歷史性轉變的一個斷面。女作家丁玲曾以瞿秋白為原型創(chuàng)作了革命戀愛小說《韋護》,男主人公韋護是瞿秋白的筆名,女主人公麗嘉以瞿秋白第一任妻子王劍虹為原型,小說描寫的是韋護因革命)信仰而放棄浪漫個性與愛情的悲情故事。小說中的韋護在革命工作與私人情感間始終存在難解的矛盾,文學史上將這種早期的普羅小說概括為“革命+戀愛”的模式。其實,在兩部紀實性文本中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自在心性與社會責任間的某種程度的對抗。一方面,目睹“倒懸待解”(《無涯》)的民眾,油然而生一種社會的責任;另一方面,心上又常常“念念不已,悲涼感慨,不知怎樣覺得人生孤寂得很。”①奮力脫離“過去的留戀”,而留戀卻是隨著自性與生俱來似的。雖然后來革命文學中的那種僵化模式為后人所詬病,但是在瞿秋白那里,所有的孤獨感、空幻感都是鮮活而真誠的。另外,瞿秋白以辯證唯物論為認識基礎的對社會現(xiàn)象的本質特征的揭示也為后來的革命文學奠定了基礎。他認為“社會現(xiàn)象吞沒了個性,好一似洪爐大冶,熔化鍛煉千萬鈞的金錫,又好象長江大河,滾滾而下,旁流齊匯,泥沙畢集,任你魚龍變化,也逃不出這河流域以外。”①他常常用明喻或者暗喻的修辭方法揭露社會的弊病。例如,他這樣記述國人的無知蒙昧:“中國的社會生活,好象朦朧曉夢,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時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帳子里有巨大的毒蟲以至于蚊納,爭相吸取他們的精血呢?“①--在痛惜社會力量孱弱與不覺醒的同時,也愛憎分明地將社會黑暗勢力比喻為吸血的蚊蟲,具有一種力透紙背的情感力量。
3結語
在這兩部紀實文學作品中,瞿秋白以親身經(jīng)歷記述了發(fā)生在新俄十月革命后的盛況,他兼具詩人的氣質與政治家的卓識。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更加重視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對左翼文學運動的直接領導,而實際上,他對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不是一語能道盡的。在尋求真理的道路上,他堅守對歷史真誠的同時,難得可貴地保持著對自我的真誠。在學理與性情之間,在歷史體驗與自我體認之間,彰顯了一個具有真情實性的知識分子的光輝形象。無論從政治思想史的維度或是革命文學史的維度來看,這兩個在紀實品質中包蘊著新鮮的文學質素的文本,對中國革命文學話語的啟迪與構建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