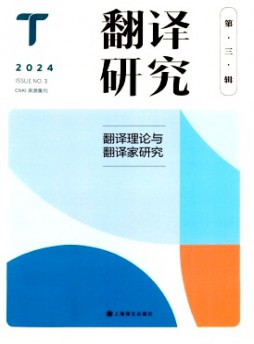季慕林翻譯理論與成就評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季慕林翻譯理論與成就評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著名的古文字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東方學(xué)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xué)家、作家。精通12國語言。在語言學(xué)、佛教學(xué)、印度學(xué)、文化學(xué)、歷史學(xué)和比較文學(xué)等方面有很深厚的造詣,研究翻譯了大量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jīng)典,2006年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一、季羨林的成就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zhèn),10歲時開始正式學(xué)習(xí)英文,高中開始學(xué)習(xí)德文,并對外國文學(xué)發(fā)生興趣。18歲時在省立濟(jì)南高中求學(xué),其國學(xué)老師,翻譯家與教育家董秋芳的指教決定了季羨林一生的寫作活動。1930年進(jìn)入清華大學(xué)西洋文學(xué)系,專業(yè)方向是德文。向吳宓、葉公超學(xué)習(xí)東西詩比較、英文,同時選修陳寅恪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xué)等,在此期間對梵文產(chǎn)生了深厚的興趣。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xué)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至哥廷根大學(xué)學(xué)習(xí)。在長期的學(xué)習(xí)研究中,季羨林認(rèn)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影響巨大,1936年決定選擇梵文,對中印文化關(guān)系進(jìn)行徹底的研究。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xué)梵文研究所期間主修印度學(xué),學(xué)習(xí)梵文及巴利文。同時選修英國語言學(xué)、斯拉夫語言學(xué),加學(xué)南斯拉夫文。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xué)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時也是他唯一的聽課者。1941年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斯拉夫語言、印度學(xué)、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yōu),獲得博士學(xué)位。同年成為語言學(xué)家艾密爾西克的入室弟子研究吐火羅語。10月在哥廷根大學(xué)漢學(xué)研究所擔(dān)任教員并繼續(xù)研究佛教及梵語,在德國期間季羨林發(fā)表了多篇重要論文,獲得了高度評價,奠定了其在國際東方學(xué)和印度學(xué)界的地位。因戰(zhàn)爭歸國無路的季羨林在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不久經(jīng)瑞士輾轉(zhuǎn)取道東歸,經(jīng)恩師陳寅恪推薦于1946年進(jìn)入北京大學(xué)任教至1983年,創(chuàng)建東方語言文學(xué)并一直擔(dān)任系主任,從事系務(wù)、科研和翻譯工作。北大是我國最早成立東方語文系的大學(xué),培養(yǎng)出了大量東方學(xué)的專業(yè)人才。1956年季羨林任中國科學(xué)院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部委員。期間歷經(jīng)磨難受盡屈辱。結(jié)束后于1978年復(fù)出任北京大學(xué)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及北京大學(xué)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改任北京大學(xué)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11日因病辭世[1]50。
二、季羨林與外國文學(xué)的翻譯
季羨林在佛典語言、印度古代語言、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中印文化關(guān)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和比較文學(xué)等領(lǐng)域創(chuàng)作頗多,著作等身,他還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閱俄、法文,同時還是世界上精于吐火羅文的幾位學(xué)者之一。成為享譽海內(nèi)外的東方學(xué)大師。季羨林曾評價自己是雜家,梵學(xué)、佛學(xué)、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xué)、比較文學(xué)、文藝?yán)碚撗芯魁R飛。季羨林一生著述頗豐,著作書目有《中印文化關(guān)系史論叢》、《〈羅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潤集》、《季羨林散文集》、《糖史》等,大都被收集入24卷的《季羨林文集》中。其中翻譯方面的著作包括有譯自德文的馬克思所著《論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譯自英文的《家庭中的泰戈樂》等;譯自梵文的印度古代長篇史詩《羅摩衍那》、印度著名劇作家迦梨陀娑的七幕詩劇《沙恭達(dá)羅》和五幕詩劇《優(yōu)哩婆濕》、反映印度民間故事的《五卷書》等等,涵蓋了印度古代語言、佛經(jīng)、梵語、吐火羅語、印度的歷史和文化等內(nèi)容。《羅摩衍那》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被奉為印度敘事詩的典范,在印度文學(xué)史上占據(jù)著崇高的地位,對整個南亞地區(qū)和宗教都產(chǎn)生過深遠(yuǎn)廣泛的影響。在中飽受折磨,被下放看門的季羨林在創(chuàng)作與研究都不能進(jìn)行的困境中,繼續(xù)堅持翻譯方面的工作,并選中了這部氣勢恢宏的史詩巨篇《羅摩衍那》,由于歷史環(huán)境的限制,季羨林只能偷偷地進(jìn)行翻譯,由于《羅摩衍那》是以詩體的形式寫就,季羨林堅持譯文也應(yīng)是詩體,要將每首三十二音節(jié)的頌譯成四行漢詩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何況還要考慮到八萬行詩的押韻,常常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詞而失魂落魄,在四年時間里,七篇的《羅摩衍那》譯了還不到三篇。結(jié)束后,季羨林的翻譯工作才光明正大地進(jìn)行,終于在1983年2月將《羅摩衍那》翻譯完畢,這是除英譯本之外世界上僅有的外文全譯本。十年風(fēng)雨、十載心血,方鑄就了這部長達(dá)兩萬頌,譯文達(dá)九萬行,五千余頁的巨著。《羅摩衍那》的翻譯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件大事,為中印的文化交流鑄起了一座豐碑,季羨林因此被印度指定為印度和亞洲文學(xué)會分會主席,被印度文學(xué)院授予名譽院士,2008年印度更是首次將印度公民榮譽獎授予當(dāng)時已97歲高齡的季羨林[2]101。季羨林在梵文翻譯上的成就眾所周知,而在吐火羅文的譯述上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種本已經(jīng)失傳的語言,僅憑著20世紀(jì)初在中國新疆發(fā)現(xiàn)的一些殘卷而重新面世。季羨林在德國留學(xué)時曾經(jīng)師從艾密爾西克對吐火羅文進(jìn)行過學(xué)習(xí)與研究。1974年時,在新疆又出土了44頁88面殘卷,當(dāng)時全世界只有不到二十個人懂這種語言,而整個中國只有季羨林懂這些文字,時年63歲的季羨林經(jīng)過17年的研究,終于破譯了全部殘卷,并譯著出《彌勒會見記》,那時候他已經(jīng)是80歲高齡的老人了。《彌勒會見記》的譯釋,對佛教傳入中國的經(jīng)歷,佛教在中亞的傳播史等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依據(jù)。季羨林多年從事各種文字文學(xué)作品的研究與翻譯,出版的譯作將近四百萬字。中國翻譯協(xié)會2006年將首次頒發(fā)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給予了季羨林,是對他為中國翻譯事業(yè)所作貢獻(xiàn)的一種肯定。
三、季羨林的翻譯思想
季羨林一生所獲榮譽與頭銜非常多,但他自己樂于接受并承認(rèn)的只有兩個,一是教授,一是翻譯家。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季羨林謝絕所有聘任,唯獨在2004年欣然出任中國翻譯協(xié)會名譽會長,其目的竟是為了便于為翻譯工作提意見。季羨林認(rèn)為,中國文化從未枯竭的原因是因為不停地有新思想注入,而最大的兩次思想注入,一次是來自印度,一次是來自西方。這兩次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因此翻譯之為用大矣哉。季羨林與他在清華的恩師之一吳宓一樣,贊同嚴(yán)復(fù)在翻譯上提出的信、達(dá)、雅的標(biāo)準(zhǔn)。他認(rèn)為信是忠于原著,達(dá)是忠于讀者,雅則是對于文學(xué)語言的忠誠。即譯者需要同時忠于作品、作者和語言。同時做到這三個字,就是上等,可以說是盡翻譯之能事了。若是能信而達(dá)雅不足,則是中等,而不信不達(dá)不雅則為下等。他認(rèn)為信是翻譯的基礎(chǔ),如果不能做到忠實于原文,就不叫翻譯。
直譯是壓倒一切的原則。這點在他翻譯《羅摩衍那》這部印度原始的詩時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為了將原文的詩體譯成中國的詩體,他決定采用順口溜似的民歌體。同時將原文分兩行寫的32個章節(jié)的頌譯成四行,每行的字?jǐn)?shù)基本整齊,并且押大體上能夠上口的韻,季羨林可謂用心良苦。譯至第六篇《戰(zhàn)斗篇》下半部時,季羨林更為嚴(yán)格地將每行定為七言絕句,間或也有五言,從而更接近于民歌體。除了譯文更加簡潔精練,保留了原文的節(jié)奏,盡可能地忠實于原文。季羨林在翻譯中不但忠實保留了原詩的信息,還盡量押大致上口的韻,在忠實原著的前提下追求文體之雅[3]133。在音韻上以偶數(shù)行押韻,韻腳靈活,音韻協(xié)調(diào)上口,譯文達(dá)到了信與美的效果。
季羨林的翻譯思想還體現(xiàn)在《羅摩衍那》的音譯上。為了保持忠實于原文,能準(zhǔn)確地選擇譯音,他通過研究中國古代佛經(jīng)翻譯的實踐與翻譯文化,基本上使用過去中國和外國和尚翻譯經(jīng)文時使用的對音方法,盡量符合印度的原音。季羨林所主張的直譯,在信的基礎(chǔ)上,還在漢語習(xí)慣以及文法允許的范圍之內(nèi),適當(dāng)引進(jìn)一些外國語法中比較周密的表達(dá)方式,使?jié)h語表達(dá)方式更加豐富,從而更適應(yīng)需要。這與魯迅寧信而不順的直譯觀頗有相似之處。但與魯迅不同的是,季羨林反對重譯,即不通過原文而對某國譯文進(jìn)行的二次翻譯。他認(rèn)為科學(xué)與哲學(xué)類必要時可以進(jìn)行重譯,文學(xué)作品則不行,并用淮南之桔淮北之枳來形容重譯對文學(xué)作品的影響。
季羨林認(rèn)為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關(guān)重要的,否則思想就無法溝通、文化無法交流、人類社會就難以前進(jìn)。正因為翻譯的重要性,季羨林十分重視翻譯職業(yè)的道德,主張翻譯行業(yè)的工作者,應(yīng)該多學(xué)幾門外語,提高自己的專業(yè)水平,同時改革大學(xué)外語學(xué)法,大力培養(yǎng)職業(yè)翻譯家,建立保證翻譯質(zhì)量機(jī)制,并再三公開請設(shè)國家翻譯獎,足見他對中國翻譯事業(yè)的關(guān)切與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