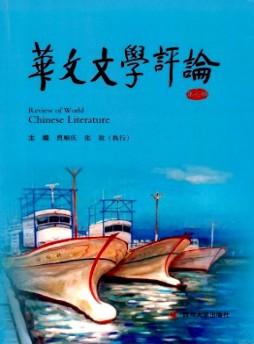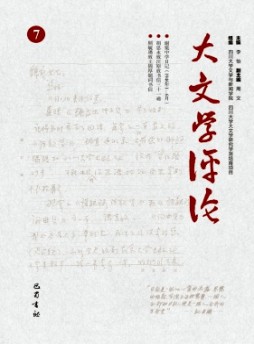莎劇文學評論發展足跡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莎劇文學評論發展足跡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起始于“”之后的中國莎劇文學評論至今已歷一世紀有余,其間,成果豐碩,星輝燦爛,老一輩莎學專家學者留下了大量翔實的文評資料以及寶貴的精神財富。但由于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側重點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且與政治因素有著太多的糾葛,以至于招致國外學界對中國莎學的政治功利性非議不斷,誤解否定“具有中國特色的莎學理論體系”。為使中國莎評得到世界全面、客觀、公正的認識,有必要對產生這種現象的社會歷史背景及影響主導因素進行深入探析,以期把微觀研究與宏觀分析有效交織起來,深層次地揭示國人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社會視角下對莎氏認知方面的限度和拓展。
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的名字首次在中國被提及是在鴉片戰爭期間,當時出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組織人才翻譯外國書籍,以求“師夷長技以制夷”,其任務中心在于引介、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至于莎氏的戲劇絕不在此之列。雖說其后莎氏的名字多次出現在清末外國傳教士的著述譯作或具有民主進步人士的言論之中,但都是些只言片語,沒有針對任何一部劇作進行學術探究,中國莎評尚處邊緣地位。而國人還莎氏本來真面目還是在田漢1921年成功以話劇形式翻譯了《哈姆雷特》之后。故此,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莎劇文學評論始于20世紀20年代。
一、20世紀20、30年代西方莎評的譯介
莎士比亞作為西方最著名的文學巨匠是世界文學中評論最多的作家之一,西方莎評始于17世紀,迄今300余年,評論內容豐富全面,且逐漸形成了系統清晰的批評理論和脈絡。相對西方國家的莎學研究來說,中國對莎士比亞的認識、接受與評論起步較晚,故在還沒有初步形成系統批評理論前提下,學習和借鑒國外成熟的莎論來發展中國的莎學研究成為一種必需。
在對西方莎評的譯介過程中,西方學界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也理所當然地傳到了莎學評論剛剛起步的中國。《文藝月刊》第2、3期連續刊發了譯文《托爾斯泰論莎士比亞》,轉述了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不屑一顧和完全否定。在他看來,莎氏簡直就是個微不足道膚淺的作家,缺乏思想,有著最低下最庸俗的世界觀,對社會、宗教問題沒有一丁點的興趣,作品里到處都是些矯揉造作,玩弄文字的游戲。但這個謾罵詆毀莎氏的態度很快就遭到了學界同行的不滿與反對。兩個月后,同家雜志又譯發了《小泉八云論莎士比亞》,表明日本莎學家對莎士比亞是推崇的,甚至到了頂禮膜拜的地步。
實際上,在中國贊同托爾斯泰貶斥莎氏的大有人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中國文人大多對莎士比亞持有否定態度,認為他只是個宮廷御用文人,憑著他對伊麗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奉迎而成為貴族階級的玩偶。左聯旗手之一的茅盾,對莎氏的認知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轉變過程。起始曾持反對態度“:莎士比亞的劇本人人視同拱璧,然而徹底講來,莎老先生若不是得著女士的喜歡,貴族的趨奉,能到這個地位么?”[1]P450之后從文本本體的審美情趣鑒賞角度,茅盾得出了人性是莎氏劇目的主題結論。在1930年出版的《西洋文學通論》中認為:哈姆萊特是人性的一種典型的描寫。“他永久厭倦這世界,但又永久戀著不舍得死;他以個人為本位,但是他對自己也是懷疑的;他永久想履行應盡的本分,卻又永久沒有勇氣,于是又在永久的自己譴責。”[2]P255
1934年茅盾在《文史》雜志發表了《莎士比亞與現實主義》轉述了狄納摩夫評議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莎士比亞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者的觀點,是第一個引介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莎士比亞評論的,并介紹了馬克思“莎士比亞化”這一重要觀點。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莎評自此開始走上了中國莎評的舞臺,為以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的莎評研究基調起到至關重要的引導作用,20世紀50、60年代甚至達到了頂峰。
此后,茅盾將莎士比亞的現實主義價值和意義發揮到了極至。究其態度轉變的原因,用茅盾自己的一句話可以說明,“莎士比亞這位心理學家,用他深刻的觀察和犀利的筆尖,剝落了他那時代的一切虛偽者的面具”,而“剝落這一切的面具,還是現代的文藝戰士的任務,這又是莎士比亞的作品為什么對于我們是親切的原因了”。[3]P470-471
從中不難看出,他是從愛國文人、文藝戰士的政治使命的視角來解讀莎氏的,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功利性使然。當時日本已占領東三省,狼顧中原,而國民政府腐敗、軟弱,作為愛國文人、左翼戰士的茅盾有著救國圖存的歷史使命感,急切聽到能喚起國民自覺性、革命性的號角,而這來自社會主義陣營中樞的聲音正是他所向往和趨同的。在今天看來,茅盾的點評雖然就莎學全面性而言有失偏頗,但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歷史大潮的沖擊下,出于愛國使命感為推動民族的解放與進步做出了積極貢獻,故應求其真,而少薄其失。“在30年代魯迅同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文化派別斗爭的過程中,中國文化戰線上的這場斗爭波及到了莎士比亞批評這個領域。”[4]P228
五四之后的中國倡導新文學、新文化,積極主張引進西方文學以改變中國傳統文學概念,但在處理外來文化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接受態度。魯迅做為最活躍的左聯旗手是自始至終“堅持了文學階級性的觀點,肯定群眾歷史作用的觀點和借鑒外國文學的正確方針,他主張老老實實地從外國文化、外國文學中吸收對中國社會有益處的東西。”[4]P15-16
針對杜衡1934年在《文藝風景》雜志上的《<凱撒傳>里所體現的群眾》里提到的群眾“沒有明確的利害觀念,他們底感情是完全被幾個煽動家所控制著,所操縱著,讀這個劇,我們在到處都會無可奈何地得到一種群眾老是在受欺騙的感覺”,魯迅先生書寫了《“以眼還眼”》給予了猛烈的抨擊,駁斥杜衡的群眾盲目性,強調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以此來喚醒民眾意識,推動歷史進步。施蟄存在否定魯迅作品“有宣傳作用而缺乏藝術價值的東西”的同時又否定蘇聯莎評“……這種政治方案運用于文學的丑態,豈不令人齒冷”。對于施批評的無知,魯迅嘲弄道:“蘇俄將排演原本莎士比亞,可見丑態,而馬克思談莎士比亞,當然錯誤”[4]P18,從而肯定了蘇聯莎學。梁實秋不僅是中國第一位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者,而且是這個時期撰寫莎評最多的學者,主張文學的人性論,但“就其主體來看還是評介性的,主要是介紹西方莎評各派的觀點”[4]P231。
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留美學者梁實秋對莎士比亞持有“中庸路線”的評判,但著重強調“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殊情形,但是主要的人性是大致不變的”。這個觀點遭到了魯迅先生的異議:“上海的教授,對人講文學,以為文學當描寫永遠不變的人性,所以至今流傳,其余的不這樣,就都消滅了云。”[4]P16-17
從文學鑒賞學術立場來說,梁氏的人性觀不無道理。但其人性論與當時魯迅先生“文學階級性”至上的觀點格格不入是二人論戰的導火線。魯迅先生的反對具有積極意義,是符合“文以載道”的特質的。反言之,梁先生的這樣另類的聲音完全出于維護文學藝術價值以純文學的視角來對待外來文學文化,“沒有讓學術研究態度遷就于現實政治的直接需要,力求客觀全面表現出了可貴的求真務實的精神……也為后來中國莎評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5]P216當然,在圍繞譯介西方莎評是否要服務于社會階級性的熱鬧紛爭之外,也有另外的微弱聲音———單純地從藝術學角度去解析莎士比亞的。這個時期那些有著良好英文基礎或在英、日國家直接接受莎士比亞研究熏陶的學者對莎氏的經典劇目進行了解讀和闡釋。袁昌英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榮獲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的女性,曾于愛丁堡大學研習英國文學,回國后先后在北平、上海講授英國文學。1935年她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上發表了《沙斯比亞的幽默》,就莎氏戲劇中典型人物的幽默性格進行了挖掘剖析。
二、20世紀40年代抗戰莎評
20世紀40年代中國莎評著重凸現人民大眾是民族解放的決定性因素和主導力量。張天翼1942年在《文藝雜志》發表了《談哈姆雷特——一封信》。在文中,他就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人物性格進行了對比探討,特別主張哈姆雷特的懷疑否定精神,認為那是當時中國所急需的,以此來激泄國民壓抑許久的不滿情緒,憤然反叛國民黨的獨裁。“惟大勇者才敢去發掘一切真相,他竟敢去懷疑,總要比任何獨斷都來得進步、可貴”。[4]P241從表面看來,莎評一直以來所遵循五四時期主張文學要發揚“解放人”的人文主義精神已被傳統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所取代,民族性增強而世界性卻淡薄了。然而從深層解讀,方知這是一種錯覺,中國當時的戰爭環境在這個變化之中起到了主導作用。
20世紀40年代初,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逐步進入相持階段。淪陷區大學也紛紛內遷至西南一隅,還時常遭到日本飛機空襲,不少學者作家的“象牙塔”被侵略者的飛機大炮粉碎,不再沉浸于西方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莎評的論說,不再幻想莎學的世界化。血與火的戰爭開闊了他們狹窄的視域和胸懷,從文學觀念到文本創作上對“世界化”與“民族化”二者關系的理解和實踐都更加辨證、深入了。他們重新站立在一個新的制高點上來認識世界與民族、審美與功利、借鑒與繼承等之間的辨證關系。1942年,著名導演焦菊隱在后方物質條件匱乏的抗戰環境下,就地取材,利用四川江安一座孔子大殿上演了《哈姆雷特》。同時發表文章《關于<哈姆雷特>》,表明哈姆雷特王子反抗命運支配、反抗專制壓迫的革命進取精神“對于生活在抗戰中的我們,是一面鏡子,一個教訓”。國民要學習哈姆雷特那種爭取擺脫和解放的反抗精神,力爭齊心協力,一致對外:“抗戰的勝利系于全國人民的和諧行動,更系于毫不猶豫地馬上去行動。”[4]P241-242
正是對這些張力關系有了新的理解,中國莎學研究者才把抗戰時期國內莎氏文學評論的世界化與民族化推上一個新的美學境界,對民族和世界關系的理解更加真實也更為全面了。由于中國民眾的奮起抗戰是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在這種世界性戰爭背景下創作的“抗戰莎評”充分發揮了莎學外延功能,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再次為世界莎學圈添加了一道與中國社會政治環境密不可分的靚麗風景線。文學作品本身的意識內涵和藝術價值是永遠追求和探究不完的。中國偉大莎劇翻譯家朱生豪從世界文學史的角度評估莎士比亞的卓越與不朽:“蓋莎翁筆下之人物,雖多為古代之貴族階級,然彼所發掘者,實為古今中外貴賤貧富人所具之人性。故雖經三百余年之后,不僅其書為全世界文學之士所耽讀,其劇本且在各國舞臺與銀幕上歷久搬演而弗衰,蓋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與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6]由此可以看出,中國莎學翻譯史上作出杰出貢獻的梁實秋和朱生豪先生都是從舞臺文本本身出發來探討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與內涵魅力,強調莎劇中的人性論觀點。
三、20世紀50、60年代效仿蘇聯莎評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中國莎評出現了第一個高潮。”[4]P31單就1956年一年之間,卞之琳的《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亞的悲劇<奧瑟羅>》,李賦寧的《論莎士比亞的<皆大歡喜>》與陳嘉的《莎士比亞在“歷史劇”中所流露的政治見解》分別運用了社會學研究方法系統分析了莎劇悲劇、喜劇和歷史劇創作的社會背景,作品中所反映的社會關系和階級斗爭問題以及人民性,著重揭示莎氏對封建勢力及資產階級的批判。
以移植傳播西方莎評為主的中國莎學研究在這一階段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蘇聯莎學者的馬克思主義莎評在中國掀起了影響的高峰。“是否以蘇聯馬克思主義莎學作為研究方針和方法,成為衡量論文標準和研究者立場的惟一原則。”[7]P35920世紀50年代的新中國為鞏固新生政權,進行了一系列以政治運動為主的社會統合,其思想核心是“階級論”。1951年在全國范圍內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形成建國后第一次思想戰線的重大斗爭。
以1953年為界,之前,在建國初進行了急風暴雨般的“鎮反”和“”運動,;之后,社會統合向縱深發展,波及面擴大,特別是“反胡風”和“肅反”運動,傳統的思想及制度資源、革命年代的經驗與蘇聯因素融為一體,都被運用其中,被用來統合社會大眾的意識。政治思想領域不斷升級的階級斗爭也理所當然地波及到了莎學研究。由于蘇聯馬克思主義莎學導向、1951年要求知識分子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及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使得人人自危,一言不慎即被打為右派,受到迫害。此階段的莎學批評研究呈現出清一色的蘇聯馬克思主義莎學的風格,階級之間對立成為研究的重點,繼續挖掘莎學的外延功能,將莎氏作品現實主義功用進一步向縱深拓展。
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作家自身改造問題的宗旨在這一時期文學創作實踐得到了更好的闡釋。由于革命形勢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作家的階級隸屬便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在這個方針指引下,趙澧是高舉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旗幟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在《試論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和人物塑造》中,他大量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在《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對莎氏的肯定,進而把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運用在對莎氏作品人物的分析上,指出:“這些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資產階級人文主義。”[8]針對中國的莎學研究,趙澧建議要進行全面和深入的探討,“因為只有努力掌握并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方法,做到真正科學的估價,才能談到借鑒和繼承,才能在理論上和實際上與資產階級觀點劃清界線。”[9]由此可以看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強調莎氏作品中的現實主義政治標準已經遠遠超越了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標準。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和實踐導致了對莎士比亞的封殺。
1964年4月,當全世界隆重紀念莎士比亞誕辰40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卻對英國紀念莎士比亞活動給予了批判。看到這個政治的風向標,莎學人士多感覺到形勢的緊張,個別冒著極大的風險悄悄地發表了幾篇論文,郭斌和在《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莎士比亞與希臘拉丁文學》中明確提出,“我們今天紀念莎士比亞生辰四百周年”,實是勇氣可嘉,展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而此后十余年里,連說這句話的機會也沒有了。在強調“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反對“名”、“洋”、“古”的文藝路線指導下,別說莎劇,就連本土的傳統戲曲也統統被封殺光,清一色的樣板戲在全國城市鄉村搞得如火如荼,莎士比亞在中國官方的媒體只能成為資產階級腐敗落后的代名詞了。
四、20世紀80年代具有中國特色的莎評
這一階段我國莎評研究進入豐產期,據不完全統計“,從五四前后到去年年底(1985年),國內發表的有關莎士比亞的文章總數約為九百四十篇,其中1975年以前發表的有三百五十三篇,1976年以后發表的有五百八十七篇,占總數的60%以上”。[10]P27其中原因,一方面開放的輿論環境為研究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是莎學者水平的提高,在沉寂的學術背后中國莎學者從未放棄他們的追求,而是默默地耕耘,這個現象是厚積薄發的結果。
20世紀80年代莎評的社會政治語境是很復雜的,粉碎“”后學術界揚眉吐氣,欲暢所欲言,但“左”的思潮并未真正退出歷史舞臺,學術界最關注的文學的方向性問題———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的爭論空前劇烈,出現了多種學說,其中劉再復提出了“文學主體性”。陳涌、程代熙、敏澤、鄭伯農、姚雪垠等對劉文的相關論斷提出學術方面的尖銳批評。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莎評依然延續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慣性剖析莎氏劇目。孫家和孟憲強分別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與莎士比亞的戲劇》與《馬克思恩格斯與莎士比亞》,再次突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莎氏的肯定以及著作中對他的大量引用。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國文學學科規劃小組在審議國家七五科研課題時認為,首先有必要通過對梁啟超、魯迅、胡適等一些近現代文學研究大家的個案剖析———他們對莎學均有涉獵,以求探討他們在借鑒西學和繼承與發展傳統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這些都對這個時期的莎評的方向性問題有著積極而深刻的影響。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提出了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于是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莎學體系也成為莎學界力爭的目標。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1984年在上海的成立以及1986年“首屆中國莎士比亞戲劇節”的成功舉辦極大地鼓舞了莎學研究者的熱情。從宏觀分析來講,這一時期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研究總體上取得了三大矚目的成績:文學評論視野開闊,探析了幾乎莎氏所有喜劇、悲劇、歷史劇和傳奇劇目,拋棄了拘囿于悲劇鑒賞的意識傾向,是至此莎評涉及面最廣的一次;首次出現了個人的莎學專著與文集,老一輩莎學家把自己多年來的潛研心血結集出版,期翼給予后來者以啟迪,指明進一步拓展研究的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多元化,從前期以政治主題為重心向人物性格闡釋、故事結構分析以及語言修辭鑒賞等藝術方面轉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比較文學在這個時期的中國莎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成績斐然。一句話,摒棄前蘇聯莎學的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莎評,轉而從文學角度、審美情趣等藝術手法來重讀莎氏經典。誠如曹禺1983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向莎士比亞學習》一文中指出的:“我們研究莎士比亞有一個與西方不盡相同的條件,我們有一個比較悠久的文化傳統,我們受不同于西方的文學、哲學、美學、社會條件和民族風氣的影響。”[4]P253至此,中國學界開始脫離西方莎學評論的影響,探究符合中國傳統、文化思維模式的民族學術上的莎士比亞批評,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樣性的新局面,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莎評研究氛圍。
在現實主義風格解析莎學的同時,文學研究者開始注重莎學內涵的挖掘。方平先生1983年出版的《和莎士比亞交個朋友吧》是中國莎學史上第一部個人專著,收錄了他17篇評論莎氏喜劇的文章,而孫家則偏重于《論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的鑒析。由賀祥麟主編的《莎士比亞研究文集》卻收集了論證莎氏十四行詩、長詩、喜劇、悲劇、歷史劇以及傳奇劇等的多篇文章,是“這個時期比較全面論述莎氏作品的一部莎評文集”。[4]P247雖說早在莎士比亞以“講故事的人”身份通過林紓翻譯的《英國人吟邊燕語》介紹給中國讀者之時,東潤就對比了李氏(太白)與莎氏各自不同的寫作特點,同時也拿《孔雀東南飛》和《羅密歐與朱麗葉》佐證了悲劇更易打動人心的藝術效果,但大規模的比較分析卻很少見,直到20世紀的80年代才蔚然成風,畢竟開放形勢下的中國學者意識到“以不同語言的文學作為比較對象,則能夠有相對穩定的較高的比較價值”[11]P100。中國學者平行對比了莎氏與中國著名作家,如曹雪芹、關漢卿、湯顯祖、曹禺等,還進行了作品和劇中人物的比較,其中著名的有方平的《曹禺和莎士比亞研究》、陳星鶴的《<趙氏孤兒>與<哈姆萊特>》等。
五、20世紀末多元化的莎評
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的中國政治還處于敏感期,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對文藝工作保持著積極慎重態度,提出了“一手抓整頓,一手抓繁榮”的方針,并指出,在整頓中必須注意把學術行為與政治行為加以區別。主張改革開放的政府對文藝界專家學者的學術探究表現出一種積極肯定和支持的態度。1990年元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等中央領導人會見全國文化藝術工作情況交流座談會及全國話劇戲曲創作座談會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瑞環發表題為《繁榮文藝必須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講話。
講話第三部分強調:積極借鑒一切對我有用的外來文化,著力謳歌社會主義時代精神。重申要貫徹“雙百方針”,并指出要“正確處理“二為”與“雙百”的辨證關系……什么時候放棄或背離了‘雙百’方針,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動亂中,十億人民八個戲的歷史教訓,必須牢牢記取。”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更是極大地鼓舞了整個學界,國內學術氣氛開始活躍起來。重新清理思想,調整思路,尋找自己真實的位置也成為20世紀90年代莎學研究新風尚。那些富有超前學術眼光和前瞻意識的莎學者,定下神來,收視返聽,探求自己的學術路向,以莎學的內涵研究為主基調來詮釋、評判莎士比亞戲劇的開放研究方法與思維方式也越來越多。1994年孟憲強教授縱觀中國莎學研究發展歷程,撰寫了《中國莎學簡史》,為后人的莎學開拓提供了翔實的史料資源,同時針對不同歷史階段中國莎評研究進行了簡明扼要的評述。20世紀末知識信息的全球化鋪天蓋地,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學批評理論移植進來為開放的中國莎評注入新鮮的血液,莎學者也開始嘗試用新興的文學理論批評來重讀莎士比亞劇目,出現了一大批從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原型批評角度重新探討莎氏的力作。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1997年孫遇春的《論莎士比亞的宗教觀》,1998年張佑周的《“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女人!”五論莎士比亞筆下的女性》以及方達的《麥克白斯及其夫人的犯罪心理》等等。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關注基督教文化及其經典《圣經》對莎士比亞的深遠影響進而闡釋莎氏作品中的宗教觀成為20世紀末期多元化中國莎評的一大亮點。1997年肖四新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莎士比亞》借助《圣經》中具體觀點分析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并非是對基督教教義的徹底否定而是否定中的肯定———即揚棄,得出結論:“處在基督教文化大背景下和基督教家庭的小環境之中的類的合理成分,那些張揚人的個性的東西,同時溶入了新的時代內容,終于變成了‘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所有世紀的’的偉大作家,給人類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12]P58
結語
縱觀20世紀中國的莎劇文學評論,處于復雜政治變革時期,與政治、權力產生無法理清的糾葛,彰顯出鮮明的時代印痕與民族特征,那么就此可斷言中國莎評政治化了嗎?在無休止的爭論中,“政治是否決定文化”是中心問題。通過上述中國各時段莎評的特點及政治社會語境的分析,不難發現:是時代的訴求通過政治影響表現在各時段的莎評中,并決定該時段莎評走向,而非簡單的政治化。
20世紀30年代政府混亂、日本狼顧,內憂外患使自覺、圖強成為仁人志士的共識并奔走呼號,莎評表現為引介西方人性解放特點;20世紀40年代民族生存權利遭到踐踏,同仇敵愾、激發人民戰斗犧牲精神為民族所急需,莎氏筆下的哈姆雷特理所當然成為國民追隨的英雄、斗士;20世紀50、60年代新生的中國面臨廣泛敵對勢力的合圍,不得不為保衛勝利果實而對內與失權階級斗爭,對外與敵對陣營斗爭,階段斗爭觀點成為有力的武器在莎評中顯現也是必然之事;試想“”中若“”不對固有政治、文化等意識形態進行全面顛覆,如何能實現其平地奪權的夢想?但它畢竟是背離歷史發展軌跡,是反時代的,只能逞一時之快;20世紀80年代被強制“左”轉了幾十年的中國松綁后生發出無窮的外射力,莎評方向表現為百花齊放的盛況;20世紀90年代因蘇聯轉資、1989動亂使人們對資本主義“和平演變”高度警惕,是左轉還是右轉的猶豫之后,終于選擇了謹慎開放的態度,那么莎評即呈現出多元化、橫向拓展、縱深延展的態勢。
統攬以上各時段莎評,結合其時代因素深入剖析,不難發現中國莎劇文學評論曲折的衍變正沿著開放、多元的健康發展軌跡向前邁進,而其中政治因素更明確地表現在時展需求上,借助莎評這個載體表現出來。最初從西方移植而來的莎評對中國社會政治環境土壤的適應性決定了以后多種發展的方向,其表征折射出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的時代特征、思維方式以及文化淵源,具有鮮明的民族性。西方國家的莎評斷然沒有經過如果復雜的政治語境的變遷,所以大多呈現出統一面目。
由于過多注重莎氏作品社會實用外延研究,20世紀中國莎劇文學評論表現出一定社會政治功利性,使得莎氏戲劇本身的學術藝術價值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這確實是中國莎學研究上一大憾事,為今后莎評研究提供借鑒,亟須拓展研究深度,真正呈現出多元化的莎學研究。
但中國政治文化大語境限制下的莎劇文學評論典型的民族性將莎氏外延研究發展到了極致,豐富了世界莎學研究,為人類提供了一份珍貴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研究資料,有其獨特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