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筆下生命體現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康拉德筆下生命體現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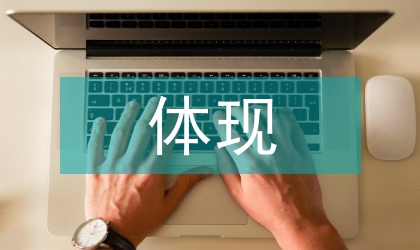
摘要:《臺風》是英國著名現代小說家約瑟夫·康拉德的海洋小說中的代表作。本文擬以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結構學說中的自我和超我為理論依據,分析小說中的兩個人物在臺風來臨前后的不同表現,從而挖掘出這兩個人物身上的內在品質,生命的價值也在臺風這種極端的自然條件下得到充分展現。
關鍵詞:《臺風》約瑟夫·康拉德自我超我生命的價值
一、引言
約瑟夫·康拉德(1875—1924年)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他出生于俄國的一個波蘭籍家庭,自幼喜歡冒險的海上生活。17歲時,前往馬賽學習航海。后來在一個英國船隊先后擔任水手與船長的職務,一生中在海上生活的時間達20年之久。20歲時才開始學習英語,近40歲時因為健康原因,結束海上生活,定居倫敦并且成為專業作家。他的作品有很多是描寫海上生活的。“《臺風》可以算是康拉德海洋小說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標志著康拉德的寫作藝術已達到成熟的程度。故事描寫了兩個方面的矛盾:一個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斗爭,另一個是人與人之間的沖突。”[1]人與自然之間的斗爭便是馬克惠船長及船員們與臺風的斗爭,而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則更多地體現在中國民工之間的爭斗。“盡管這篇小說也屬于‘專寫暴風雨之作’,但它的真正的主題‘不是惡劣的天氣,而是甲板下人為因素造成的極度緊張給船上生活帶來的復雜情勢’。”[2]在這部小說中,康拉德細致地描寫了大自然的惡劣與殘暴,但他更強調的是人在面對這種惡劣環境時所表現出的勇敢、沉著等品質。本文通過對比分析小說中馬克惠和朱可士兩人在臺風前后的反應,向讀者展示人在臺風這種極端惡劣的自然災害前的最真實的精神和生理狀況,引導讀者對人類生存價值的思考和對生命存在意義的探索。在本文中,筆者擬以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結構學說中的自我、超我為理論依據,探討作品中所蘊含的生命價值。
二、自我的控制價值的隱藏
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是在其潛意識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其三重人格結構學說中,他把人格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大部分。“本我(id)是最原始的、與生俱來的潛意識部分,其中貯藏著人性中最接近獸性的一些本能性沖動,按照快樂原則行動,一味追求滿足;自我(ego)是意識的結構部分,來自伊底經外部世界的影響而形成的知覺系統,代表理性與機智,按照現實原則活動;超我(super-ego)又稱自我理想,是從自我中分化出去的部分,代表良心,是人格中最道德的部分,按照至善原則指導自我、限制自我。”[3]總而言之,本我中充滿了人的各種受壓抑的欲望,不論何時何地都只想著滿足欲望;而自我是對本我中各種欲望的控制,同時在現實原則上尋求本我的滿足,在本我與現實中達到一種平衡;而超我則通過現實中的道德規范來約束自我,壓制本我。
在小說的開頭,馬克惠船長的形象顯得古怪可笑,看似愚笨。“南山號船長馬克惠,生的那副相貌,簡直就是他內心的副本,表里完全一致:并不顯露堅毅或呆鈍的特點;什么顯明的特點都沒有;只是平平淡淡,不起感應,不動聲色。倘使說他的外貌偶爾有所暗示,那除非就是羞澀。”[4]從這些描寫中可以看出,馬克惠船長非常善于控制自己的內心,因為有著心如止水的內心,其外在表現才會是平平淡淡,沒有明顯的特點。既看不出他有什么堅毅、勇敢等品質,也未發現他有呆鈍的缺點。從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結構學說來看,這是馬克惠船長對本能欲望的一種自我控制,而且控制得相當到位。但是,馬克惠船長并非沒有本能的欲望,其最明顯的一次表現則是他在15歲時不顧父母的反對成為了一名海員。
“想象力不多也不少,剛夠他一天又一天地過活下去,他這樣保持隨著故事的進展,在外有臺風襲擊內有中艙騷亂的雙重危機中,馬克惠船長顯示出勇敢沉著、剛毅堅定的精神。他對風暴的態度不是退讓躲避,而是“直穿過去”;他對中艙里中國苦力間的沖突采取了果斷、合理的解決辦法,表現了他思想周密、判斷正確、處理公正、為人善良的優秀品質。而這一切品質在平時的馬克惠身上并無表露,只是在受到外部強大壓力時才顯示出來。他的人格中的道德品質指導著他的行為,促使他無畏臺風和解救中國人。在臺風來臨的時刻,他達到超我的狀態,肩負起身為船長所有的特殊使命,實現了其生命的價值。
馬克惠直面臺風的大無畏精神表現在:
船長重新說道:“一艘開足馬力的輪船只好迎面承當。這樣惡劣的天氣變化到處都是,合適的辦法就是直穿過去,用不著美力達號老船長所說的‘應付暴風雨的戰略’。不久前有一天,我在岸上聽見他當著許多船主高談闊論,那些船主都走進來坐在我旁邊一張桌子面前。我覺得那簡直就是胡說亂道。他對他們說他怎樣克服了(我想他大概是這么說的)一個極端可怕的暴風,因此他沒有讓那暴風走近五十英里以內。他說這全是隨機應變。他怎么知道五十英里以外有暴風,叫我簡直莫名其妙了。”[10]
這是馬克惠船長的決定,他將帶領這條船直面臺風。平時看似木訥愚鈍的老船長在強大的臺風襲擊下顯示出沉著剛毅、永不氣餒的精神。面對瘋狂的臺風,他選擇不退讓不躲避,義無反顧地帶領整條船抗擊臺風。在臺風導致的極度危險和緊張的情形下,馬克惠船長已然達到了超我的狀態,此時他已將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而是誓與整條船共存亡。這是他的人生信仰:面對危險,他選擇采取對策直接面對,而不是懦弱地避開。他的生命價值就在這樣超然的狀態下得到了展現。
朱可士在臺風到來之后,有一段肉體和精神掙扎的過程。他并不如馬克惠船長表現得那么沉著冷靜,這與他自我狀態中更多地迎合現實利益有關。但是在馬克惠船長的影響和激勵下,他經受住了臺風的考驗,他從自我狀態跨到了超我的境界,出色地完成了當時的使命。“‘我又有什么辦法呢,先生?’朱可士渾身透濕,只是打顫,使他說話的聲音好似咩咩的小羊叫。”[11]這是馬克惠船長希望朱可士到船艙里處理中國人的事件時朱可士的回答,他對臺風很懼怕,覺得對自己的生命都無法掌控,更別說去解救那些他認為低賤的中國人了。在臺風來臨之初,他被臺風的威力震懾住了,他變得膽小,對生命失去了信心。他甚至產生了幻想,“他第一個禁不住的念頭是,整個的中國海已經爬上望臺來了。”如果任由這種心理狀態發展下去,他可能一下子就會被臺風所打敗。但是此時,馬克惠船長的堅定給他做了道德的榜樣,讓他找到了生命的支撐點,給了他戰勝臺風的信心:
于是他又聽見了那個聲音,勉強逼出而微微震顫的聲音,可是在那洪大雜亂的喧鬧里帶有靜謐的沁人心脾的效果,仿佛從暴風的黑暗荒野的那邊,從一個遙遠的和平境界里傳來的;他又聽見了那個人的聲音——纖弱而不可屈撓的聲音,能以傳達無限思想、決心和目的,縱使到了世界末日,天體墜落而正義完成的時節也會說些自信的話的——他又聽見了這聲音,仿佛正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向他叫喊(中國論文聯盟整理)——“沒有錯”。[12]
馬克惠船長的聲音就像一針強心劑注入朱可士的心田,讓他有信心有毅力去面對臺風。馬克惠船長“纖弱而不可屈撓的聲音”說明他的身體已在暴風雨的打擊下變得虛弱,但是精神卻依舊牢不可摧。聲音中所蘊含的精神力量使朱可士堅信他們必定能戰勝這場臺風,縱使“世界末日”到來,朱可士明白馬克惠船長也不會害怕。受到馬克惠不屈精神的感染,朱可士忘卻肉體,和馬克惠船長一樣達到精神的超我狀態。于是,他最終義無反顧地接受了船長的派下的任務——處理中國人的內亂。
“他來勢洶洶,將他們帶走。他這樣地來來去去——動作兇猛而迅速”[13],他去處理中國人的內亂,事實上是冒著生命的危險,因為外有臺風的打擊,內有中國人之間的廝打,一不留神他可能就會失去生命。此時的他已經不顧生命安危,只是專注地解決內亂應對臺風,所以他的動作才如此的果斷而勇猛。“‘別管我——滾你們的。我沒有什么’,朱可士尖叫道。”[14]“別管我”三個字道出了他的內心,展現了他的氣魄。達到超我狀態的朱可士出色地完成了船長交給他的任務,化解了輪船內部的危機,最終幫助整條船戰勝了臺風。他實現了他在臺風這種極端自然條件下才能實現的生命價值。在平時的生活中,朱可士不在乎也瞧不起這些中國人,更不會在乎他們的生命。但在臺風來臨之時,他已超脫了名利觀念、個人安危,全身心地投入到救援當中,實現了其生命的價值。
四、結語
康拉德把大海作為陸地的對照,以航行象征人生,展示了對人生命運的思索和生命價值的挖掘。他絕不為寫海洋而寫海洋,在他的海洋小說中,陸地上往往充滿邪惡和狡詐。“海洋雖然有時兇猛可怕,但它是純潔的,它能蕩滌人的靈魂、顯示人的本性。馬克惠船長是一個沒有受到陸地上骯臟和罪惡污染的人”,‘他航行于海洋的表面,就像有些人輕輕掠過生存的歲月,悄悄沉入一座平靜的墳墓,始終沒有懂得生活,也從來沒有機會看見生活所包含的一切奸狠、狂暴和恐怖’。”[15]正是馬克惠船長這樣一個不懂得所謂生活的人,在臺風這種惡劣的條件下,在大海這樣廣闊的環境里,他達到了超我的狀態。在他的支持和引領下,朱可士也超然地在臺風所帶來的危機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們憑借內在的優秀品質,戰勝了風浪,平息了紛爭,使這一次艱難的航行得以勝利完成。他們的生命力在臺風的極端自然條件下受到極大激發,生命價值得到充分的展現。
注釋:
[1][2][15]薛詩綺:《康拉德海洋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
[3]楊鑫輝:《新編心理學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5][6][7][8][9][10][11][12][13][14]約瑟夫·康拉德著,袁家驊譯,薛詩綺編:《康拉德海洋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