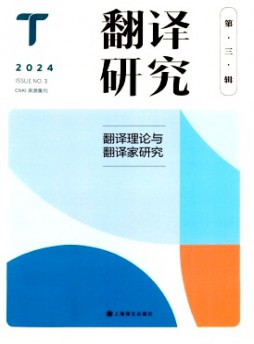林譯翻譯理念與其譯作賞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林譯翻譯理念與其譯作賞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引言
錢(qián)鐘書(shū)先生說(shuō)“譯、誘、媒、訛、化這些一脈連通、彼此呼應(yīng),引申出文學(xué)翻譯所向往的最高境界。”(1997:269)在嚴(yán)復(fù)的“信達(dá)雅”和傅雷的“神似”之外,為文學(xué)翻譯提出新的標(biāo)準(zhǔn):化境。“化境說(shuō)”要求譯文既要不能露出牽強(qiáng)附會(huì)的痕跡,又能傳達(dá)原文的味道。得其“意”比較容易,然而得其“味”確實(shí)困難。錢(qián)谷融先生認(rèn)為一切文學(xué)作品都應(yīng)該是詩(shī),都應(yīng)該有詩(shī)的意味。要再現(xiàn)它的“詩(shī)的意味”譯者必須充分發(fā)揮其創(chuàng)造性,“得意而忘言”,不能拘泥于原文受原文的束縛太大。錢(qián)先生認(rèn)為‘誘’、‘媒’說(shuō)明了翻譯的跨文化交流作用以及譯作對(duì)讀者的感召作用。它是個(gè)居間者或聯(lián)絡(luò)員介紹大家去認(rèn)識(shí)外國(guó)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不同國(guó)家的人們締結(jié)了‘文學(xué)姻緣’。他指出“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種程度的‘訛’又是不可避免的毛病。”佛經(jīng)翻譯家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之說(shuō)。中國(guó)古代翻譯理論家贊寧說(shuō)“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因此,由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譯文總有和原文不符的地方。但是不能否認(rèn)譯文在某些地方也有超越原文的可能。
1林譯小說(shuō)的“媒介”與“誘導(dǎo)”作用
林紓的翻譯是我國(guó)翻譯史上的奇葩,他翻譯的小說(shuō)被稱作“林譯小說(shuō)”。一生翻譯了180多種,數(shù)量之多,影響之大,可謂“前無(wú)古人”。第一部譯作《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后一時(shí)洛陽(yáng)紙貴,國(guó)人就如同呼吸到了新鮮空氣。它使中國(guó)人第一次接觸到了西方文學(xué)的瑰寶,對(duì)中國(guó)近代文學(xué)家和新文學(xué)都產(chǎn)生了“誘導(dǎo)”和媒介的作用,開(kāi)啟了翻譯外國(guó)文學(xué)的先河,架起了一座溝通中外文學(xué)的橋梁。首先,林譯小說(shuō)對(duì)中國(guó)近代文學(xué)家有很大的影響。林紓是大量把西方小說(shuō)介紹到中國(guó)的第一人,林譯小說(shuō)讓國(guó)人感受到了西洋小說(shuō)的魅力,之前中國(guó)的文化人總以為科技西方超過(guò)中國(guó),但是文學(xué)中國(guó)優(yōu)于西方。林譯小說(shuō)改變了中國(guó)人對(duì)西方小說(shuō)的偏見(jiàn),“五四”新文學(xué)時(shí)期的作家大多通過(guò)它的誘導(dǎo)和媒介開(kāi)始接觸外國(guó)文學(xué),如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錢(qián)鐘書(shū)、冰心等,都曾有過(guò)一段嗜讀“林譯小說(shuō)”的經(jīng)歷。后來(lái)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也走上了翻譯外國(guó)文學(xué)的道路。因此,優(yōu)秀的譯文才會(huì)誘導(dǎo)讀者去讀原文,讓讀者有一種強(qiáng)烈的欲望去撥開(kāi)面紗看到原文的真面目。就如同許多西方讀者讀了霍克斯和楊憲益夫婦的《紅樓夢(mèng)》全譯本,激起了他們的興趣學(xué)習(xí)中文,閱讀曹雪芹傾注十年心血所著的《紅樓夢(mèng)》。如果這兩個(gè)全譯本非常拙劣,想必只會(huì)掃盡西方國(guó)家讀者的興趣,同時(shí)也會(huì)破壞原作的名譽(yù)。林譯小說(shuō)引誘人們?nèi)ソ佑|外國(guó)小說(shuō),先去讀他的譯作,然而他創(chuàng)造性的翻譯挑起了人的好奇心,讓他們接近原作。由此可看出“林譯小說(shuō)”的“媒介”和“誘導(dǎo)”作用。其次,林譯小說(shuō)對(duì)中國(guó)近代文學(xué)和社會(huì)的影響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它引進(jìn)了西方的先進(jìn)的思想觀念。中國(guó)小說(shuō)從舊式的才子佳人的愛(ài)情故事到表現(xiàn)現(xiàn)代意義的愛(ài)情這一歷史飛躍中,林譯小說(shuō)是不可缺少的媒介。透過(guò)他的翻譯,西方的愛(ài)情觀展現(xiàn)在中國(guó)讀者面前,傳統(tǒng)的禮教在一定程度上動(dòng)搖了,它也推進(jìn)了中國(guó)婦女解放和婚姻自由的浪潮。林譯小說(shuō)如同一扇窗戶,打開(kāi)了人們的眼界,使近代中國(guó)人首先從這里瞥見(jiàn)了西方的文化與生活。
2攀登文學(xué)翻譯的理想境界“化”境
譯、誘、訛都有一個(gè)言字邊,惟獨(dú)化沒(méi)有,言字邊加化就是訛。因此,除非不言不譯,否則訛是不可避免的,錢(qián)鐘書(shū)對(duì)林紓翻譯中的訛基本是肯定的,持非常寬容的態(tài)度。“化境”里,“化”有兩種,一種是文學(xué)翻譯的最高境界,另一種是譯者的翻譯過(guò)程和實(shí)踐。絕對(duì)的化境是一種翻譯的理想,是不可能達(dá)到的目標(biāo),但是翻譯實(shí)踐中譯者也要努力朝這個(gè)方向邁進(jìn)。翻譯在讀者和作者之間起居間或離間的作用。好的翻譯即是居間者或橋梁,只能做到霧里看花,誘讀者去閱讀原作,從而消滅自己。壞的翻譯是離間者,雖然可能忠實(shí)于原作的字句,卻晦澀拙劣,毀滅了原作的聲譽(yù),自己的生命也不會(huì)太長(zhǎng)。“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訛”是合情合理的“訛”,是翻譯中必須要“失的本”,不失便不成翻譯。當(dāng)然林譯小說(shuō)中也有相當(dāng)多的誤譯,但是在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下他的譯作起到了積極的影響。錢(qián)鐘書(shū)在《林紓的翻譯》中提出了非常奇妙的看法:“于是‘媒’和‘誘’產(chǎn)生了新的意義。翻譯本來(lái)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們?nèi)W(xué)外文,讀原作。它挑動(dòng)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們對(duì)原作無(wú)限向往,仿佛讓他們嘗到了一點(diǎn)味道,引起了口味,可是沒(méi)有解饞過(guò)癮。他們總覺(jué)得讀翻譯像隔霧賞花,不比讀原作那么真切。”林譯小說(shuō)能挑起讀者對(duì)原作的好奇心是因?yàn)榱旨傇诜g時(shí)發(fā)揮了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這正說(shuō)明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他明知道會(huì)“失”也不得不這樣。林紓認(rèn)為翻譯小說(shuō)不在于講究具體的字句上一一對(duì)應(yīng)的翻譯,而是重在傳種聲音。而對(duì)作品的評(píng)論也被高度的認(rèn)可影響著后來(lái)的評(píng)論者,這些無(wú)疑都證明了夏志清的確具有著歷史的眼光。
夏志清對(duì)作品能有如此深的感悟,得力于他對(duì)西方批評(píng)理論的把握,如王德威所說(shuō)夏志清在他作品中廣泛的應(yīng)用了新批評(píng)的理論。夏志清對(duì)文本進(jìn)行了細(xì)讀,在夏志清的《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史》中的序言談到這樣一句話“再讀五四時(shí)期的小說(shuō),實(shí)在覺(jué)得它們大半寫(xiě)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說(shuō)家技巧幼稚且不說(shuō),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更重要的問(wèn)題是小說(shuō)家在描繪一個(gè)人間現(xiàn)象時(shí),沒(méi)有提供比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書(shū)第一章里就開(kāi)門(mén)見(jiàn)山,直指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缺點(diǎn)即在其受范于當(dāng)時(shí)流行的意識(shí)形態(tài),不便從事于道德問(wèn)題之探討”[1](P11)。從原文中可以發(fā)現(xiàn),夏志清這本書(shū)的立足點(diǎn)主要從道德的角度出發(fā)的。而且要注意的是,這里的“道德”不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所理解的道德,而是指人性,一種人性欠缺的不斷完善。因此書(shū)中對(duì)文本或多或少的都進(jìn)行了道德的評(píng)判。如,對(duì)老舍《駱駝祥子》中的祥子也進(jìn)行了道德批判。作者通過(guò)對(duì)文本的細(xì)讀從祥子與虎妞一段對(duì)話中指出了祥子道德的問(wèn)題。
“好吧,你說(shuō)說(shuō)!”她搬過(guò)個(gè)凳子來(lái),坐在火爐旁。
“你有多少錢(qián)?”他問(wèn)。
“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問(wèn)這個(gè)嗎!你不是娶媳婦呢,是娶那點(diǎn)錢(qián),對(duì)不對(duì)?”[1](P131)
這是他們倆新婚不久后的第一次吵架,夏志清從這里指出老舍表面出了驚人的道德眼光和心理深度。認(rèn)為祥子為了錢(qián)而喪失了道德,放棄了感情,帶有欺騙的跟虎妞結(jié)婚。從這里可以看出夏志清對(duì)文本的解讀更投入,更接近文本,對(duì)人物投入的感情更多。而且在作者的書(shū)中評(píng)論作品時(shí),他都會(huì)對(duì)作品的原文進(jìn)行選擇性的摘選,目的就是為了在評(píng)論的基礎(chǔ)上,讓讀者更直觀的去感受文本,這也體現(xiàn)了作者對(duì)閱讀文本的重視。因此夏志清這種對(duì)文本解讀的方法無(wú)疑打破了原有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家作品的“階級(jí)論”模式,讓對(duì)作家作品的解讀從單一走向了多元化,讓原本豐富的文本具有了更多的闡釋空間,同時(shí)也賦予了作品更多的內(nèi)涵。
總的來(lái)說(shuō),夏志清對(duì)張愛(ài)玲、錢(qián)鐘書(shū)、沈從文的重視,并將他們都列為專章進(jìn)行大篇幅的評(píng)論,可以說(shuō)這是一次對(duì)經(jīng)典秩序的重構(gòu),使人們?cè)陉P(guān)注“魯、巴、茅、郭、老、曹”這些既定經(jīng)典之外,去發(fā)現(xiàn)更多的新的作家作品,也給予他們更多、更大展示的平臺(tái)。而對(duì)一些已成為經(jīng)典的作家作品卻又有選擇性的評(píng)論,而且有些并沒(méi)有開(kāi)專章。這部小說(shuō)史的編寫(xiě)是以作家作品為主的,打破了以往文學(xué)史中文學(xué)思潮、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政治綱領(lǐng)必須貫穿全書(shū)的抒寫(xiě)模式,這對(duì)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發(fā)展有著很大的推進(jìn)作用。作為小說(shuō)史的抒寫(xiě),與文學(xué)史的寫(xiě)作又有所不同。夏志清的這本《小說(shuō)史》又是小說(shuō)史編撰方面的最早嘗試,他通過(guò)大膽的采用“新批評(píng)”的方法,著重對(duì)作品進(jìn)行審美層面的闡釋,對(duì)優(yōu)秀作家的發(fā)掘,刷新了人們對(duì)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舊有認(rèn)識(shí)。當(dāng)然在《小說(shuō)史》中仍然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他對(duì)左翼文學(xué)的漠視,對(duì)魯迅評(píng)價(jià)的偏低,及僅用西方的理論來(lái)觀照整個(gè)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等等。不過(guò)這畢竟是一家之言,作者對(duì)史的抒寫(xiě)方式,對(duì)作家的選擇,對(duì)作品的判斷都受到已有思維模式、意識(shí)形態(tài)和自身主觀意識(shí)的影響,難免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是在當(dāng)時(shí)一個(gè)單一的話語(yǔ)模式還沒(méi)有完全解體的歷史背景下,《小說(shuō)史》的出現(xiàn)無(wú)疑也像別于主流的另一種聲音,而且這個(gè)聲音對(duì)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確實(shí)起著關(guān)鍵性的作用,開(kāi)闊了人們的視野,也指引著后來(lái)的治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