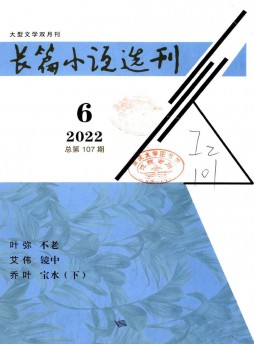長篇小說寫作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長篇小說寫作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物質(zhì)的繁榮并不能掩蓋精神的貧乏,我們正大步流星地步入一個精神苦難的時代。這個時代在中國史無前例。而更大的苦難即將接踵而至,那就是精神苦難的文化后果及其生命的深淵景象。今天,看似文化多元,話語翻飛,實則萬馬齊喑。隨著人文知識分子主動或被動地卷入資本邏輯、商品倫理,與社會潛規(guī)則同謀,被現(xiàn)代性收編,精神生產(chǎn)者實際處于集體沉默狀態(tài)。西哲曰:人是會思想的蘆葦,如今,我們只是蘆葦,并不思想,嘴尖皮厚,隨風(fēng)搖擺。當(dāng)此之時,文學(xué)何為?作為國族文學(xué)標(biāo)桿的長篇小說何為?帶著此一問題,當(dāng)我翻檢新世紀(jì)四川長篇小說的時候,四位作家的作品進入了我的視野。他們是阿來的《空山》第
一、二卷,麥家的《解密》、《暗算》、《風(fēng)聲》,何大草的《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臉》、《盲春秋》,羅偉章的《磨尖掐尖》。這些作品成就高低不一,風(fēng)格各異,但在我看來,它們足以代表新世紀(jì)以來四川乃至中國長篇小說的水平,它們的優(yōu)短劣長,使我們有權(quán)利對中國長篇小說的現(xiàn)實和未來說話。
邊緣,在今天已經(jīng)是一個俗不可耐的詞語,已被巧言令色者玷污,或其內(nèi)在之光被話語泡沫重重遮掩。但“邊緣”的任務(wù)并未完成,“邊緣”的意義在漢語文學(xué)中尚未充分彰顯。阿來、麥家、何大草、羅偉章們的長篇小說,立于邊緣歷史、邊緣現(xiàn)實、邊緣人物,重構(gòu)今天國人及人類的精神圖景,再次顯現(xiàn)“邊緣”的力量。
阿來繼續(xù)書寫著一個民族的歷史。這也許是阿來的宿命,但也是阿來的光榮。繼土司制度土崩瓦解、“塵埃落定”后,阿來在《空山》中以溫情與銳利的筆鋒伸入之后藏族的未來。阿來的過人之處,如果在《塵埃落定》中表現(xiàn)為書寫重大歷史的詩意空靈、舉重若輕、大智若愚、漫不經(jīng)心,在似與不似之間切中歷史根脈,那么在《空山》中,阿來則越出國族作家身份與狹隘“政治”界限,以普世眼光精心打量一個民族的歷史走向。《空山》的勝利不是人類學(xué)、民俗學(xué)、方志學(xué)意義上的。它不像有些描寫少數(shù)民族的作家,往往以神奇詭異的文字,炫耀居于文化邊緣的那些風(fēng)俗人情、民間神話的神秘,以吸引眼球,迎合“他者”的好奇心與窺視癖,以致于使這個民族實際落入被觀“看”、被書寫、被建構(gòu),最終面臨文化被閹割,“族性”徹底被消解的危險境地。阿來或許深深地懂得,如何去尊重、去平等地對待一個民族,如何深入到這個民族的內(nèi)部,去勘探、去發(fā)現(xiàn)不同情境中人類共同的遭際、共同的苦難、共同的命運、共同的人性,從而直逼“人”本身。在這點上,阿來仿佛已浮現(xiàn)出福克納、馬爾克斯、卡夫卡等偉大作家的面影。《空山》里的“機村”是人類文學(xué)版圖上的另一個“馬貢多”、“約克納帕塔法”和“城堡”。若是有朝一日阿來真的成了一個“偉大作家”,這一點無疑會是一個重要原因。盡管在小說中不乏阿來越出正常敘述的詩人的浪漫、多情與悲憤。可是,在言說自己的民族時誰又能夠完全控制得住呢?
一個與圣地“麥加”同音的作家“麥家”,在奔赴繆斯的朝圣路上默默前行二十年后,終于在新世紀(jì)的某一天,因長篇小說《暗算》的“觸電”,一舉成名,紅遍天涯。應(yīng)了經(jīng)上的一句話,落地的麥子不死。但是麥家的成功絕非偶然,也不僅是“觸電”等文學(xué)以外的原因。麥家長篇小說想像和虛構(gòu)的那個世界,較之《空山》更在邊緣,可以說在一個看不見的深淵。在某種意義上,麥家給我們打開了一扇塵封多年的門,一扇通向地下天空的門,讓我們突然在他文字閃過的一道亮光中,瞥見一個深不可測、黑暗無邊而又異趣橫生的另類空間。在這個森嚴(yán)可怖的世界中,一群異秉的天才——人類中的人類,在一個人的戰(zhàn)爭中,掙扎、沉淪、殊死搏斗。他們是都可以叫做容金珍的絕頂天才,隱身于一個都稱為701的保密機構(gòu),畢其一生的聰明才智破解密碼。他們在與空中飄浮不定若隱若現(xiàn)的紫密、黑密、烏密等等的“斗法”中迸發(fā)出的生命意志、生命強力可謂撼天動地。可一旦進入生活世界,他們卻如此不堪一擊:容金珍因妻子出于善心又出人意料的越軌行為,由病而瘋,由瘋而歿。他們是天才與傻瓜、堅強與脆弱的混合體。他們能破譯再玄奧神奇的人為的密碼,面對生活的密碼卻一籌莫展、無能為力,就像那個能猜透斯蒂克芬之謎,卻無法參透命運并被命運無端捉弄的俄底普斯。在《解密》、《暗算》、《風(fēng)聲》等長篇中,與其說麥家講述、建構(gòu)了另一個隱秘的世界,不如說麥家在這個世界中發(fā)現(xiàn)了一群特殊的人、一種特殊的人性,一個由特殊人性構(gòu)成的特殊的歷史。米蘭·昆德拉曾經(jīng)信誓旦旦,說“發(fā)現(xiàn)惟有小說才能發(fā)現(xiàn)的東西,乃是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①。麥家的長篇小說恐怕是米氏說法的最好注腳。不要以為麥家真要給我們破解什么密碼,其實他要破解的是人生:他探入密碼的那只手,經(jīng)由天才的靈魂,曲里拐彎、不動生色地伸進了人的生命本相。他慣用的“伎倆”:是把人逼到絕境,讓生命的殊相自己迸發(fā),自己開口說話。這個絕境就在生活世界、在人生和人性的邊緣。
歷史系出生的何大草,在上世紀(jì)“新歷史小說”風(fēng)起云涌后很快偃旗息鼓的90年代中期,已然寫出《衣冠似雪》、《如夢令》等中篇歷史小說,業(yè)已表現(xiàn)出書寫“邊緣”歷史的卓然才華。他總是在“大歷史”書寫遺漏下的瞬間和縫隙尋找詩情,鋪展想象,激揚文字。“圖窮匕見”時的荊軻面對秦王,究竟在想什么?偏居江南的著名女詞人李清照,該當(dāng)如何打發(fā)凄凄慘慘戚戚尋尋覓覓的日子?他和她們是怎樣進入我們今天的生活和我們的生命發(fā)生聯(lián)系?小說寫得開闔大氣,又精致細密;文本試驗先鋒前衛(wèi),章法有致;文字美輪美奐。2007年歲尾,他又在《十月》推出歷史長篇小說《盲春秋》,述說大明王朝崩潰瞬間的歷史故事。面臨李自成大軍壓境,江山社稷搖搖欲墜的崇禎皇帝,在難見一線希望之光的最后時日,他都在干些什么?國破家亡的時刻,他是自殺?他殺?還是杳然隱遁于某個神秘的去所?如此疑竇叢生的歷史,卻讓一個在大火中燒得面目全非、雙目失明、身份曖昧不清,僅憑聽覺和觸覺打發(fā)生命的老嫗,對清代著名史學(xué)家計六奇講述。這部由計六奇記錄的“口述歷史”文本,又被傳道士帶出帝國,流落歐美,作“跨文明”旅行,經(jīng)多國漫游、多人之手,多種語言譯,卒不可讀,幾成天書。在歷盡輾轉(zhuǎn),飽經(jīng)滄桑的幾個世紀(jì)后,由另一個敘述者——與何大草有著相同出身的作家整理,或稱“當(dāng)代翻譯”才得問世。如此“春秋”,不“盲”才怪?何大草的用心并不如前新歷史小說顛覆大歷史那樣來得簡單。這部從孕育、構(gòu)思、寫作到成書長達十余載的小說,經(jīng)作者精心撰構(gòu),日夜摸挲,堅實精美。其中的主要人物,鮮活豐滿,性格特異。巧妙的“互文本”藝術(shù),穿梭于虛實真假的歷史時空,使小說仿佛交響樂演奏、多聲部發(fā)音,意義繁復(fù)流動,生氣充盈,不同讀者,想必各有會心、各得其所。如此小說,當(dāng)以“大智慧”稱之。閱讀這篇文字,一種蒼茫悲涼的氛圍,漫上身來,揮之更甚,猶如佇立廣漠之上,抑或易水河邊,有秋風(fēng)乍起,長發(fā)飄飛,無邊落葉蕭蕭而下、漫天而來。大廈將傾,誰之奈何?無限喟嘆,奪胸而出,小說寫盡人世與人性的滄桑與悲涼。末代皇帝朱由檢,面對紛繁世事、大國朝政、宮廷陰謀,游走于“無為”“有為”之間,所表現(xiàn)的另一種政治智慧、雄韜大略、心志玄機,深得華夏文化精髓。而由生動逼真的細節(jié)累積所還原的歷史場景,生氣靈動,體溫可觸、心律可感。小說構(gòu)思之巧、結(jié)構(gòu)之妙、意境之魅、文字之美、涵蘊之豐厚,堪稱獨步。很多時候我想,其實何大草的那些歷史小說才是今天中國“純文學(xué)”的代表,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小說所達到的高度才真有漢語界博爾赫斯的味道。
阿來的《空山》由上世紀(jì)
五、六十年代走來,麥家的“解密三部曲”當(dāng)屬民國以來內(nèi)戰(zhàn)、抗戰(zhàn)的歷史幽曲,何大草的《盲春秋》則把時間上溯到明代,我要說明的是,他們的這些小說書寫的都是邊緣的歷史。但何大草給我們的是兩只手,一只手撫摸歷史,另一只手則伸進現(xiàn)實。2003到2005年,他相繼發(fā)表了長篇小說《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臉》。前者被改編為《十三棵泡桐》,獲2006年東京國際電影節(jié)評委會特別獎。這兩部寫當(dāng)下中學(xué)生的青春小說、成長小說,依然是關(guān)于“邊緣”的小說。這不僅在于“中學(xué)生”題材最近幾十年一直在中國文壇的主流視線之外,除王朔發(fā)表于上世紀(jì)90年代的《動物兇猛》,再難數(shù)出幾部描寫中學(xué)生的優(yōu)秀長篇。更為主要的是何大草指尖敲打出的中學(xué)生,不是我們?nèi)粘K姡麄冸[藏在井然有序、表面平靜的校園生活后面,離我們很遠很遠,又近在身邊。那些叫“陶陶”或者“韓韓”的中學(xué)生們,殘酷、血腥、暴烈,他們的行為、思想、情感、心理,處處演繹成人世界,讓我們在閱讀時不得不常常回首人類的童年和青年,思索人之初人性的真實狀態(tài)。《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臉》可以說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原欲——暴力和性,如何推動人的成長,如何鋪展和扭曲人的生命道路,使人成其所是。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這兩部長篇是關(guān)于人的“存在”的小說。《刀子和刀子》出版之初,葛紅兵說,這是他近年來看到的最好的青春小說,“青春的酷烈、無奈的傷痛被演繹得那么好:懵懂時期的愛情和友誼,叛逆時代的幻想和渴望,仿佛獲得了文字的首肯,突然間露出了真相;血肉橫飛的身體遭遇與黝暗無謂的靈魂處境是那么真切地遭遇到一起”,它召回了我們最隱秘的青春經(jīng)驗,有助于青少年的自我理解,也有助于成人世界在回味當(dāng)初中自我體認。無獨有偶。以底層敘事,關(guān)注民工苦難,發(fā)表《我們的成長》、《我們的路》、《故鄉(xiāng)在遠方》、《大嫂謠》等小說贏得最初聲譽的作家羅偉章,繼中篇小說《我們能夠拯救誰》、《奸細》之后,在2007年推出長篇《磨尖掐尖》,講述中國高考制度下重點中學(xué)背后的故事:高考制度實行三十年后,重點中學(xué)演變成冷漠無情、不見血腥的“殺人機器”。功利心、拜物教、商品邏輯,使小說中的重點中學(xué)成為一處又一處“名利場”。學(xué)生以無生命的“產(chǎn)品”被分為三流九等,置于“火箭班”、“重點班”“普通班”等分類培養(yǎng)、“制造”——“磨尖”。日思夢想多出“高考狀元”、多上清華北大而使學(xué)校獲名獲利,在一場場不見硝煙卻異常慘烈的爭奪尖子生——“掐尖”的戰(zhàn)斗中,學(xué)校耍盡手腕,教師費盡心機,家長擺足架子,學(xué)生占盡風(fēng)頭。重點班主任手上的學(xué)生花名冊是重要“情報”,持有之則人人自危,難逃“奸細”之嫌。結(jié)果,真正的天才被認為“精神異常”,流落街頭,拾荒度日。考上名校的“尖子”,又傲慢冷漠,心理犯罪,被校方開除。普通的學(xué)生,則遭受歧視,未出校門,就深感社會等級森嚴(yán)、人世炎涼、生活荒誕、甚至懷抱仇視心理。在此一過程中,教師顏面丟盡,尊嚴(yán)盡失,與校方同謀,無形中扮演扭曲和戕害學(xué)生人性的幫兇或罪魁禍?zhǔn)住!办`魂工程師”的稱號和“素質(zhì)教育”豈止成為笑談?小說的深刻之處還在于使我們在掩卷之余恍然大悟:近二十年學(xué)歷水平的愈來愈高并未能阻止甚至可能是加快了全社會的道德淪喪和精神沙漠化的速度,原來還在中學(xué)階段,那些稚嫩的苗子已被“功利化”改造,一朝步入社會,情何以堪?這也使何大草在《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臉》中那群中學(xué)生騷動、迷惘、暴烈、放縱和叛逆的精神狀態(tài)有了一種現(xiàn)實的解釋。《磨尖掐尖》對重點中學(xué)弊端的袒露是如此的觸目驚心,使我多次不忍往下閱讀。
終于談到了道德淪喪,觸及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苦難。當(dāng)然,這是由阿來、麥家、何大草和羅偉章們長篇小說的邊緣書寫引發(fā)出來的。“邊緣”的力量在這里顯現(xiàn)出強大的威力。
現(xiàn)代性反思,是時至今日阿來《空山》的總主題。這也使阿來在舒緩的敘述節(jié)奏中,露出鋒利的刀刃,從邊緣切入人類中心,與一個人類死結(jié)也是一個巨大的悖論遭遇:崇尚進步的現(xiàn)代性,是否正在使我們大踏步地后退?我們在嫦娥登月即將進入太空得到表面的轟轟烈烈、耀眼輝煌和春花秋月后,是否正在喪失腳下的根基?人類是否在追求“無限的進步”中走向一條終結(jié)的道路?我曾經(jīng)在幾年前全國首屆多民族文學(xué)論壇上說,那些正在從原始森林走出來進入現(xiàn)代社會過上“幸福”生活的民族,諸如鄂倫春等最易感到“現(xiàn)代”給他們的肌膚和內(nèi)心帶來的尖銳刺痛,他們?nèi)绱诉@般的文學(xué)和詩學(xué),是我們審理今天人類癥候的寶貴財富。記得就在那次會上,阿來的一句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隨著拖拉機、打米機、洗衣機的進入,邊遠的藏區(qū)已經(jīng)開始和外界過起共同的生活,它的文化意義正在喪失。說到這里,阿來環(huán)視四周,悵然若失。《空山》第一卷,伴隨汽車開進機村,外鄉(xiāng)人、私生子格拉的靈魂,在謊言的包圍和冷漠的敵視中隨風(fēng)飄散。時到如今,還沒有人對其中的深意做出恰如其分的解說。不是阿來,也難以在樸素瑰麗的文字中做出如此深入的思考;不是阿來,我也不能說出:阿來實際在反思“民族主義”的文化后果。接下來的“天火”,以森林之火象喻人內(nèi)心的大火。阿來在這里實際反思的是構(gòu)成20世紀(jì)中國現(xiàn)代性題中要義,被“”推向極端的“激進主義”。它給人類造成的災(zāi)難之深重,就如人類的縮影——機村一樣,是毀滅性的。正是在“民族主義”和“激進主義”的交互作用下,在《空山》第二卷中,機村最后迎來的是《荒蕪》,是綠色家園、生存空間的徹底喪失。“現(xiàn)代性”的豪邁征程,在一派“謊言”之中,將機村逐漸“抽空”,變成一座廢墟。《空山》的寓意正在這里。
“邊緣”的巨大力量,在羅偉章那里體現(xiàn)為“制度文化批判”。當(dāng)一種制度,無論它看起來如何正當(dāng),怎樣合法,一旦與資本邏輯、商品倫理、市儈習(xí)氣、貨幣鬼魅相勾結(jié),就會違背初衷,走向公平、正義和真理的反面。阿來在《空山》中已然暗示,在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tài)面前,無人幸免。羅偉章的《磨尖掐尖》具體到高考制度,人為制度而存在,人被制度所塑造,人——學(xué)生、老師、家長為制度所宰割,成為這種制度文化的奴婢和犧牲品,更有甚者成為冤魂。莊嚴(yán)的人在冷漠的制度面前凄愴地倒下。還有什么樣的悲劇比之來得疼痛和深刻?所以,有理由說,《磨尖掐尖》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它從制度文化批判的角度參與了現(xiàn)代性反思。
對于何大草、麥家的上述長篇,“邊緣”的威力來自于“人性發(fā)現(xiàn)”的光芒。何大草和麥家似乎對鏡子的前面不感興趣(當(dāng)然有時也會注意到鏡子的兩端),他們更愿意鉆到鏡子的后面,給我們提供猙獰恐怖的另一種景觀:與原初的生命意志糾結(jié)在一起的非凡的人性景觀。所以才有了何大草《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臉》中那些中學(xué)生人性的畸變:畸形的暴力、戀愛和性欲,直接進入“磨尖掐尖”的“陰面”,而把“陽面”留給了羅偉章們。正是靠著這張“左臉”,麥家和何大草獨步當(dāng)今文壇。他們對“戰(zhàn)爭”有著共同的愛好。“戰(zhàn)爭”是他們多數(shù)長篇故事展開的背景,是他們想像的出發(fā)點和施展才華的陣地。何大草《盲春秋》的戰(zhàn)爭在古代,但穿越歷史的眼光卻在當(dāng)代。當(dāng)崇禎皇帝無計可施的時候,快馬傳來李自成的手書,希望面見一次,共商“天下”大計。商討的結(jié)果是皇帝對“禪讓”一事毫無興趣。這個故事顯然超出歷史“真實”,但里面卻蘊藏了豐富的人性況味和現(xiàn)代意識。麥家“解密三部曲”的戰(zhàn)爭發(fā)生在20世紀(jì)上半葉。戰(zhàn)爭制造密碼,戰(zhàn)爭依賴密碼;天才破譯密碼,密碼折磨天才。天才隔著一層神秘的幕布——密碼,參與殘酷的戰(zhàn)爭,從而彰顯出與戰(zhàn)場中作戰(zhàn)者不一樣的人性。這種彰顯即是發(fā)現(xiàn),這種人性發(fā)現(xiàn),即是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新的戰(zhàn)爭,新的人類戰(zhàn)爭的歷史。
就這樣,立于“邊緣”,阿來、麥家、何大草、羅偉章在“現(xiàn)代性反思”、“制度文化批判”和“人性發(fā)現(xiàn)”中證實了文學(xué)力量的偉大。而這正是今天這個時代最為缺乏的。這也集中展示了四川長篇小說在新世紀(jì)的重要收獲,也是四川文學(xué)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中不可小覷的原因。“邊緣”哪來那么大的力量?邊緣是一種立場。是一種與主流社會、主流文化保持距離的獨立姿態(tài)。是獲取道義和批判目光的精神支點。是真理處身和顯身的位置。要立于邊緣,談何容易?邊緣在商品化、市俗化社會意味著犧牲,甚至是巨大的犧牲。邊緣很難堅持,稍不留神就被收編。但我要強調(diào)的是:一當(dāng)文學(xué)站立“邊緣”,就可能觸摸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實質(zhì)。上述四位作家的長篇小說,其實在最深刻的層次上啟示我們:我們已進入精神苦難的時代:精神的人已然死去。“空山”其實是靈魂的空殼。羅偉章、何大草的《磨尖掐尖》、《刀子和刀子》等則形象地展示了一群無根漂泊的生命的苦難。麥家、何大草的歷史小說,又從另一個側(cè)面告訴我們,無論是多么的出類拔萃甚或是“超人”,一旦失去精神支撐,離開生命的根基,任一歷史或生活風(fēng)浪輕輕一碰,就將瞬間化為齏粉。盡管這些小說,有的寫的是歷史,有的描述現(xiàn)實的一隅,但他們提供的永遠是這個時代的精神現(xiàn)實、精神圖景。缺失精神根基,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癥結(jié),也是我們這個時代苦難的根本。
然而,對上述這些作品,我還是有我的不滿意:它們似乎都不愿在黑暗中給我們出示星光。這樣會不會使迷失者更加迷失?是否有這樣的顧慮:小說的偉大、不朽根源于某種不確定后面的無限多義性?我看這樣的“多慮”大可不必。這使我想起列夫·托爾斯泰給聶赫留朵夫、卡列寧安排的歸宿,想起賈寶玉隨“空空道人”而去的生命結(jié)局,但誰會懷疑《復(fù)活》、《安娜·卡列寧娜》、《紅樓夢》不是偉大的作品?抑或是壓根兒不知道拿什么來拯救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苦難,尤其在這樣一個一切標(biāo)準(zhǔn)都煙消云散的迷茫時刻?如果真是如此,這就回到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今天我們的文學(xué)究竟拿什么來啟蒙?不管最終能拿出什么,在我看來,面對精神苦難的現(xiàn)實,中國長篇小說、中國文學(xué)只有承擔(dān),才不辱使命,才會有可能偉大和不朽。文學(xué)是詩意地關(guān)注存在、關(guān)注精神、關(guān)注靈魂的藝術(shù)。但,是溫暖的關(guān)注。溫暖源自作家內(nèi)心的星光。
注釋
①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shù)》,第6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