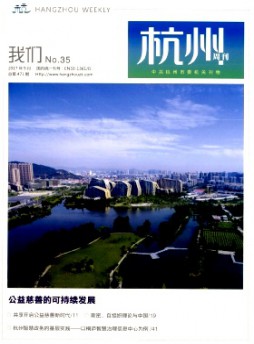我們所面對文化現景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我們所面對文化現景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只要我們不是從主觀愿望出發,不是以書本或外國的模式作為立論的根據,而是以我國現實的國情作為研究的基礎,就會發現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化現實。與整個經濟政治生活一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人民的文化生活也經歷了歷史大轉折形勢大發展的巨大變革。今天的文化已經不再是階級斗爭為綱的、閉關鎖國的、計劃經濟的文化,而是更注重建設與積累的、對外開放與交流的、產業化趨勢愈益明顯的文化。一方面,在大轉折中,文化事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獲得了大發展:文化事業的機構和隊伍、文化產品的數量比十幾年前增加了數倍甚至數十倍,優秀人才和作品獲得了脫穎而出的社會條件,文化界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弘揚主旋律,組織實施精品戰略,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在一定程度上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是當前文化生活的主流。另一方面,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與它的復雜多變、良莠紛呈、撲朔迷離、不可預測、無所適從,也成為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個明顯的潮流。我以為,如果加以概括的話,在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文化現實諸多新的特點、新的發展態勢中,最突出的就是它的多元性、商業性與全球性。
(一)我國面對著一個多元的文化現實
在社會的觀念文化上,人們的理想信仰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生活態度多元化了。這種多元的取向是全方位的,公開化的。十二億人的理想信仰本來就不可能是同一的,即便在“全國一片紅”的時代,宗教徒們也沒有放棄他們的信仰,極左派們也并不信仰馬列主義,更何況在今天。一方面,我國社會主義道路屢經曲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黨內有些人經不起失敗和挫折的考驗,背叛了馬列主義背叛了黨,用他們的政治與經濟行為解構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全社會造成極壞的影響。而在某些文化圈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消失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一些文化人已經不動聲色地完成了他們的“話語轉換”,口號與旗幟已大不相同。前些年是“淡化政治”“躲避崇高”“淡化意識形態”,如今是“告別革命”“消解主流意識”,或直言不諱地談論“中心價值解體”“當代價值解體”“聲勢浩大的主流已經分解,習慣于單一事項的人們從心理上踩不到支撐點”。另一方面,從八十年代以來,我們已經進入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經濟成分共存的混合經濟時代,產生了一些新的社會群體。迄至1996年,私營企業主已超過170萬人,其中注冊資金超過100萬元的為62617戶(《百科知識》1997年第12期)。經濟利益的現實性不僅決定了意識形態的矛盾形式而且構成了文化價值文化理想的現實起點。與“一大二公”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一元文化形態已不可能再存在。一種觀點認為,如今,一元文化已經相互分化和自我確定為三個層面的文化,即體現國家意識形態原則的主流文化、代表人文知識分子價值立場的知識分子文化、反映市民文化精神的大眾文化,并且形成一種自說自話、互不對抗的文化格局。但我認為,并沒有什么統一的知識分子文化,文化的分層實際上是由知識分子的分化而凸現出來。無論是主流文化、大眾文化亦或非主流文化、反主流文化、邊緣文化,其生產制作和傳播者主要都是知識分子。
在文化生產上,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們已不再按照統一指令絞盡腦汁進行創作了。他們從自己的觀念體系出發觀察與思考,并有了自由表達的社會條件。因而我們看到了反映各種世界觀、精神追求與物質追求的文化產品,甚至他們各自所操的方法和語匯也大相徑庭。文化產品的生產方式也發生了看得見的轉變,其過程已經逐漸工業化。電影的生產方式被廣泛地模仿,精神產品的創作者變成了制作者。他們可能是一個生產團體,有一個文章書籍的制造作坊,由一個策劃者擬定內容與章節,然后,在一陣復印機的嗡嗡聲和剪刀和喀嚓聲中,或者電腦的流水作業中,文章書籍被生產出來。同樣,幾十集的電視連續劇可以被幾位“大腕”在茶余飯后娓娓“侃”出。在某種意義上,機械復制時代的文化生產與獨創性為敵。由于文化財富再生產的技術化,復制與盜印盜版成為發財致富的捷徑,它源源不斷地提供產品進入文化市場傾銷。這種文化生產方式與傳播方式初來乍到,管理者適應它、駕馭它尚須時日,在目前這種半自由競爭的狀態下,很難保證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中心價值的凸現。
在文化消費中,人們有了選擇的自由并能夠自由地選擇。各種趣味,各種嗜好,各種欲望——從精神的到物質的,從心理的到生理的,從低級的到高級的,從卑瑣的到高尚的——都被人們寬容地承認并接納,形形色色的消費需求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在文化市場上得到滿足。一方面是人們拒絕引導也怯于引導;另一方面是宣傳媒體尤其電視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火爆,它左右人們的思想,左右人們的日常話題,生成輿論并左右輿論。他們把形形色色的當代英雄、各路明星經過刻意包裝隆重推出,這些人的作派語言服飾被競相效尤,形成聲勢浩大的“追星族”;他們輪番宣傳各種觀念、各種“新潮”,人們一次又一次在不知不覺中被“洗腦”,卻自以為個性已經解放。于是編輯和主持人儼然成了這個社會的精神導師。
在文化市場上,這種多元化的文化現實任何人都可以感覺得到。在書刊音像市場,你幾乎弄不清你是誰,你置身于何時何地,是前現代還是后現代。在這里你比在別處更真切地感到“人文精神失落”“文化殖民主義”“新儒家”“后現代主義”的存在。在娛樂市場,赤橙黃綠青藍紫,五光十色,光怪陸離,令人目眩神迷。在一片異彩紛呈之中主流文化的色彩似乎已經顯得有些暗淡。
(二)我們面對著日益商業化的文化現實
如今我國的文化事業已經開始進入市場經濟軌道,其主要表現是文化市場的蓬勃興起迅猛發展。文化市場的存在是與城市的出現與發展分不開的,封建社會就有所謂“勾欄”“瓦肆”。在舊中國的一些大城市,文化市場也相當發達,比如上海的“大世界”,北京的“琉璃廠”等等。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我們搞的是產品經濟,文化是單純的賣方市場,看書看電影看戲都是受教育是政治任務,文化市場實際上是萎縮的。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市場重新活躍起來,逐漸形成門類齊全的文化市場體系,主要有九大類(一說十三大類):音像制品市場、書報刊市場、演出市場、娛樂市場、工藝美術市場、影視市場、文物市場、文化藝術培訓市場和中外文化交流市場,幾乎涵蓋了文化產品的銷售、文藝演出和文化娛樂活動等方方面面。今天,文化產品的出版發行已經市場化了,文藝演出也部分市場化,創作、著述的商品貨幣交換關系越來越明顯,知識產權意識在萌芽與深化,文化經紀人、文化商人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職業。文化產業吸納了大量經營者(包括國營集體個體私營外資)與從業人員,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據有關部門統計,截止1997年底,全國共有文化產業機構31.3萬個,從業人員167.4萬人;全國文化娛樂業共有機構17.7萬個,從業人員94萬人;全國文化市場其他經營機構共有8萬個,從業人員22萬人。(《中國文化報》1998年4月21日)全國文化市場各類經營單位固定資產原值426.9億元,主業營業收入190.8億元,實現利稅47.9億元。(《人民日報》1998年5月7日)文化產業已成為第三產業中舉足輕重的一個部類,文化市場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結合、相互滲透,一方面,溝通了文化藝術的生產與消費,促進了文化產品的流通與傳播,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發展文化事業的積極性,滿足了人們多方面的文化生活需求,推動了文化體制改革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市場法則”也就制約了文化領域的各種活動,文化產品的商業化勢頭難以遏制。對經濟利益的直接追求成了一種文化現實。文化生產成為一種不斷刺激世俗欲望的消費品的產出,文化消費則變成尋求感觀快樂的具體表達。人們經常莫可奈何地發現,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較量中,在金錢與良心的較量中,后者往往是注定的犧牲品。絕大多數經營者,無論國營集體或個體,為了看得見的利益,總是難免或主動或被動,或興高采烈或極不情愿地俯身屈就低層次的需求。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成為一種“時代病”。文化產品的品位難免被降低,主流文化的傳播與普及難免被忽視。
(三)我們面對著日益信息化全球化的文化現實
早在19世紀中葉,當工業革命的成果剛剛顯露出來時,馬克思恩格斯就曾預言:“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共產黨宣言》)今天,電子技術使訴諸視覺與聽覺的文化藝術率先成為世界性的,電影、電視、錄相、電子游戲和通俗音樂已成為世界性的大眾文化。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使精神產品世界化全球化的進程來得比物質生產領域更加快捷。它將給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娛樂方式帶來巨大的變化,也將導致感性體驗、認識方式、思維方式的變異。有人預言,信息高速公路所帶來的全球趨勢,將引起民族國家的衰落、超空間的團體和超時空的人的出現。
盡管中國尚未進入鋼筋水泥亦即物質的高速公路時代,然而信息高速公路已經以看不見的高速度來到了中國,并已經使部分領域、部分人群現代化與信息化。它可能成為促進我國農業和工業現代化的工具和契機,并為人的自身素質的提高創造新的條件。它給予中國文化的機遇與挑戰是同等的。雖然人類物質財富的全球化仍然遙遙無期,而物質財富的表現物、記錄物、符號、信息、“比特”卻已然全球化了。當然不能認為這是全人類文化的全球化,而只是英語文化的全球化,更確切地說是美國文化的全球化。美國以其雄厚的物質財富和高科技條件為基礎,在不讓全球共享其物質財富的前提下,讓全球共享其精神文明。在新的世界經濟政治格局中,美國已經處于霸主地位,在未來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美國將憑借信息高速公路也處于霸主地位。美國文化、美國意識形態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廣度深度影響全球。有史以來所形成的人類文化的多元化、民族化格局面臨挑戰。中國以其物質科技水平及文化文字條件在這種文化格局中將處于何種地位?在信息高速公路所形成的新文化——電腦空間文化中,能否有中國文化的一席之地?這種新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怎樣交互作用?億萬“網蟲”對網絡上傳播的價值觀和文化能否有所選擇?他們是無條件地拜倒在美國文化足下還是對民族文化仍然心懷摯愛與責任感?這些都還是問題。同時,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現還可能在物質關系和精神關系兩個方面加速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一部分人將優裕地生活于這個知識經濟時代,擁有世界性的精神交往并成為信息百萬富翁;另一部分人將謀生艱難,更加外在于現代社會并成為信息窮人。而這種狀況又會反過來使中國的基礎薄弱與發展不平衡顯得更加觸目驚心,造成領導層抉擇困難,很可能使人力不從心,疲于奔命,顧此失彼。
文化生活的現實,明白無誤地昭示著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多元開放社會和商業時代。它構成活的現實和既定理論的沖突,并直接訴諸人們的直覺,成為我們從未遇見過的一種思想挑戰。同時也對社會領導層的信仰、智慧、毅力和領導能力形成實際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