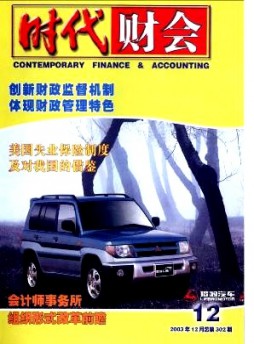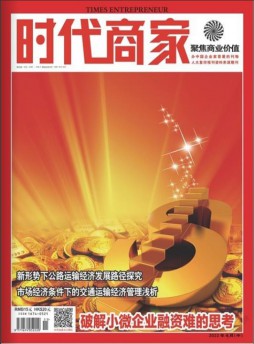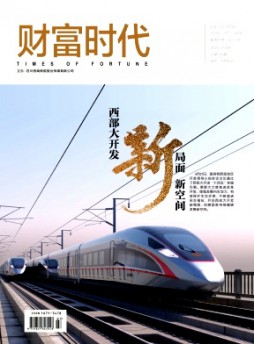微時(shí)代的電影創(chuàng)作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微時(shí)代的電影創(chuàng)作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微電影的“微反思”
微時(shí)代下方興未艾的微電影憑借著豐富的題材,自由的創(chuàng)作、快捷的傳播、低廉的成本優(yōu)勢(shì),以窺斑見(jiàn)豹的態(tài)勢(shì)向人們演繹著自己的影像圖騰,以一種全新的影像敘事風(fēng)格大大地拓展了注意力經(jīng)濟(jì)的疆土,“飛入尋常百姓家”,造就了微時(shí)代的草根盛宴。但也許“從微電影出現(xiàn)的那一刻起,甚至在其概念醞釀之初,其中的大部分領(lǐng)域已然變成媒體新一輪資本游戲的掘金地。”[2]日益成為各業(yè)界關(guān)注的廣告營(yíng)銷新戰(zhàn)場(chǎng)。在《一觸即發(fā)》、《哨聲嘹亮》、《11度青春》、《酸甜苦辣》系列、《奇跡世界》等視頻的背后充斥著的是雪弗蘭品牌、佳能相機(jī)、凱迪拉克汽車、九游網(wǎng)絡(luò)游戲等各種商業(yè)實(shí)體欲言又止的利益訴求。產(chǎn)品廣告的植入和品牌的定制早已經(jīng)成為資本在微電影的創(chuàng)作之中的商業(yè)考量。誠(chéng)然,在微電影的誕生之日就與廣告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但過(guò)度的“曖昧關(guān)系”必將削弱作品本身的藝術(shù)價(jià)值訴求,從而淪為一種淺薄無(wú)營(yíng)養(yǎng)的快餐文化或是披著劇情外衣的高級(jí)廣告。品牌成就微電影的同時(shí),也像一把斯巴達(dá)之劍懸在微電影的創(chuàng)作之中,引發(fā)人們對(duì)微電影創(chuàng)作自由度的疑慮。微電影在藝術(shù)與商業(yè)之間徘徊,但就像徐崢參演的《一部佳作的誕生》所詮釋的:“與其糾結(jié)于文藝片與商業(yè)片之間,不如重視影片細(xì)節(jié)上的藝術(shù)審美追求,只有讓作品走進(jìn)觀眾的心,最終才能贏得商業(yè)上的成功。”與此同時(shí),微電影創(chuàng)作的微門檻喚起眾多“電影游民”的影像沖動(dòng)。他們?cè)谧杂傻木W(wǎng)絡(luò)時(shí)代中爭(zhēng)先恐后地尋找適合自己的“微角色”,沉浸在影像表達(dá)的感性狂歡中,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欣欣向榮的繁華景象。微時(shí)代下的網(wǎng)絡(luò)媒體環(huán)境為非精英式的影像表達(dá)提供了多元化的創(chuàng)作土壤。其中不乏許多優(yōu)秀的作品,以底層敘事的方式切入當(dāng)前社會(huì)發(fā)展的“微現(xiàn)實(shí)”傳遞出發(fā)人深省或感人至深的正能量。如四川大學(xué)的王余亮《山隅》以一種原生態(tài)的攝影方式記錄大山深處爺爺奶奶的生活狀態(tài),詮釋一種對(duì)生活恬靜淡然的態(tài)度。《迷失的家園》通過(guò)物種與環(huán)境反差對(duì)比的手法,以鏡頭語(yǔ)言講述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庭發(fā)生的真實(shí)故事,喚起人們的環(huán)保意識(shí)。當(dāng)然在這些眼花繚亂的作品中,筆者也發(fā)現(xiàn)某些微電影將其淪為他們情感的宣泄工具,甚至無(wú)法掩飾他們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不滿和扭曲的心態(tài)。“這些敘事的方式是以一種自我防御的姿勢(shì)將自身構(gòu)建成與外在世界暫時(shí)隔絕的空間,用‘空間偽裝自身’,無(wú)意識(shí)地維持著一種斗爭(zhēng)和防御的姿勢(shì)。改變的僅僅是猶如海市蜃樓般外部世界的視覺(jué)侵略性。”[3]在《紅領(lǐng)巾》的對(duì)白中曾有“小學(xué)不正常,長(zhǎng)大就流氓”之類近似群體扭曲的價(jià)值觀說(shuō)教;《我要結(jié)婚》中諸如“鄭錢花”、“姜來(lái)有”的未來(lái)期許中,也隱藏著對(duì)“富二代”的微妙的“仇富”心態(tài)。雖然它們直面了現(xiàn)實(shí)的生活狀態(tài)與現(xiàn)象,但缺乏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主題呈現(xiàn)或是與審美價(jià)值擦肩而過(guò)或是停留于表象的結(jié)合,無(wú)法展現(xiàn)人性、情感的力度與深度,雖然迎合了受眾的宣泄心理,但亦消解了作品本身的藝術(shù)價(jià)值與吸引力。
二、微電影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的“微情懷”
黑格爾說(shuō)過(guò):“作為藝術(shù)品應(yīng)當(dāng)具有意蘊(yùn),即內(nèi)在的情感、精神和靈魂。”[4]而各類藝術(shù)在本質(zhì)上是相通的,電影藝術(shù)作為第七藝術(shù)因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態(tài)構(gòu)成了別具一格的藝術(shù)意蘊(yùn)。微電影所追求的藝術(shù)情懷就是指微電影中所具有的藝術(shù)意蘊(yùn),可以指向作品影像語(yǔ)言或人物形象所傳遞給受眾的人生感悟、審美情趣、生命體驗(yàn)以及思想、精神、哲理等價(jià)值取向,是一種言盡意無(wú)窮的藝術(shù)境界。美學(xué)家蘇珊•朗格就曾指出:“呈現(xiàn)就是藝術(shù)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而電影從本質(zhì)上看像是以夢(mèng)的方式進(jìn)行表意。”[5]微電影作為電影在新媒體時(shí)代的新模式可以借助這種獨(dú)特的表意方式滿足了大眾在碎片化時(shí)間中對(duì)于電影之夢(mèng)的審美追求。它以獨(dú)具創(chuàng)意的故事主題、樸實(shí)寫意的影像視聽、個(gè)性化的敘事風(fēng)格演繹著自己的藝術(shù)魅力,以一種新型的藝術(shù)樣態(tài)書寫自己的藝術(shù)情懷,詮釋著每個(gè)人的電影夢(mèng),雖微,亦微而足道。
(一)雖辭微,但其意旨深遠(yuǎn)微電影的“微”之義不僅僅在于微小、微型,而其精髓在于精益求精的選題創(chuàng)意,以微知著,其辭雖微,但其志可潔,雖微言亦可大義,一葉而知秋。沒(méi)有復(fù)雜的時(shí)代精神,也沒(méi)有深沉多元的主題架構(gòu),只有單一的主題闡釋,但必另辟蹊徑,懷有“縱橫自有凌云筆,俯仰隨人已可憐”的情懷,僅僅一個(gè)故事,一段情懷,一次追憶,亦或是個(gè)體情感的釋放與審美理念的濃縮,沒(méi)有宏偉的故事篇章,只有小人物、小命運(yùn),但能達(dá)到“四兩撥千斤,杯酒釋兵權(quán)”“微風(fēng)鼓浪、水石相搏”的藝術(shù)效果。將深沉的表達(dá)蘊(yùn)涵于影像符號(hào)之中,不禁讓觀影者內(nèi)心產(chǎn)生情感的共鳴。在(時(shí)長(zhǎng)5分鐘)《看球記》中當(dāng)成年的兒子騎上父親的肩膀看球的瞬間,濃濃的“父愛(ài)親情”便以這種獨(dú)特的風(fēng)格得以詮釋。在2010年的《老男孩》通過(guò)講述一對(duì)不再青春年少的老男孩重登舞臺(tái)追尋青春與夢(mèng)想的故事,以真實(shí)細(xì)膩的姿態(tài)觸動(dòng)到了廣大的“70、80”后內(nèi)心深處,打開了他們記憶的閘門,激起了他們緬懷自己青春與夢(mèng)想的情感共鳴。
(二)雖景微,但可自成天地微影像中的一個(gè)畫面、一句對(duì)白、一個(gè)鏡頭都可以讓微電影成為捕捉時(shí)間消逝與空間跳躍性的美的藝術(shù)。巴拉茲貝拉曾說(shuō)過(guò):“在優(yōu)秀的影視作品中,許多生活中隱蔽細(xì)節(jié)的發(fā)現(xiàn)往往是歸功于特寫,這些特寫并不是單調(diào)乏味的,它們往往既有現(xiàn)實(shí)性又富有抒情味,體現(xiàn)出一種穿透現(xiàn)實(shí)的力度,以獨(dú)特視覺(jué)效果沖擊著人們的心靈。”[6]微電影因自身時(shí)長(zhǎng)的限制,其鏡頭語(yǔ)言的表現(xiàn)方式必然從宏偉敘述和廣闊的圖景轉(zhuǎn)向聚焦視角致微。因此,微電影故事中呈現(xiàn)的畫面、聲音、色彩、光影的細(xì)節(jié)塑造、人物形象的象征性以及語(yǔ)言對(duì)白的隱喻性將成為展現(xiàn)作品藝術(shù)氣息的重要元素,大面積地選取特寫與近景也將在所難免。一部?jī)?yōu)秀的作品常常利用與日常生活貼近或相關(guān)的自然情感資源或帶有普遍性的大眾訴求指向,通過(guò)特定的畫面與畫面之間觸碰,強(qiáng)烈而鮮明的底層敘事色彩繪制,俘獲觀眾的心,滿足平凡大眾的心理訴求。《老男孩》中鮮有廣闊縱深的外景空間鏡頭,卻通過(guò)泛黃懷舊的影調(diào)、校園大喇叭、藍(lán)白校服、游戲機(jī)、教學(xué)樓場(chǎng)景、吉他、校園街頭的青年小團(tuán)體這些特定鏡頭與場(chǎng)景,以簡(jiǎn)練卻不簡(jiǎn)單的方式在影像與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相關(guān)聯(lián)性上刻畫上時(shí)代的痕跡,寥寥幾筆勾勒出了那個(gè)時(shí)期人們的生活圖景仿像,瞬間將“70、80后”觀眾拉回他們自己的校園記憶中,感慨那個(gè)年代我們一同經(jīng)歷過(guò)的心路歷程與社會(huì)變遷。
(三)雖個(gè)性,但不失微美新媒體技術(shù)的革新,特別是DV技術(shù)的普及打破了傳統(tǒng)膠片時(shí)代精英人士才能駕馭影像的神話,讓電影這個(gè)高雅藝術(shù)平民化,讓每個(gè)懷揣電影夢(mèng)的普通人也可以通過(guò)DV機(jī)以自己的敘事風(fēng)格拍攝屬于自己的微電影。多元化的主題、獨(dú)特的敘事環(huán)境、緊湊的敘事節(jié)奏造成了微電影敘事策略上的獨(dú)具一格。微電影主題的取材雖廣,但沒(méi)有采用傳統(tǒng)長(zhǎng)片中的多元主題建構(gòu),常常以貼近現(xiàn)實(shí)又容易被人們忽略“微現(xiàn)象”為切入點(diǎn),向觀眾呈現(xiàn)出一幅鮮活的生活橫切面。移動(dòng)多媒體技術(shù)地出現(xiàn),讓微電影從暗房走向了天空,讓影像在人們的指尖中“流淌”,在互動(dòng)中讓微電影成為人們精神交流的新載體,某種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電影藝術(shù)從單向傳播到雙向互動(dòng)的轉(zhuǎn)向。若奈特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作品的敘述方式常常與它所敘述的故事成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從這層意義上講,微電影的故事風(fēng)格常常決定了它要選擇的敘事方式。與傳統(tǒng)的線性敘事電影不同,在微電影中往往摒棄傳統(tǒng)的敘述方式,進(jìn)一步淡化、凝練故事發(fā)展中的前期鋪墊與次要部分,簡(jiǎn)潔明了地預(yù)設(shè)懸念,設(shè)計(jì)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的情節(jié)與矛盾,靈活地采用倒敘、交叉敘事、插入敘事、時(shí)空交錯(cuò)式等敘事結(jié)構(gòu)以及應(yīng)用色調(diào)、音樂(lè)、象征性影像語(yǔ)言等手法,在短促的時(shí)間內(nèi),營(yíng)造出一種能引起觀眾對(duì)故事深層內(nèi)涵思考的韻味和情緒,讓觀眾感受到微電影與長(zhǎng)片電影別樣的藝術(shù)表達(dá)形態(tài)。在作品《回到過(guò)去說(shuō)愛(ài)你》中就大膽地采用時(shí)空交錯(cuò)式敘事方式,令觀眾在時(shí)空交錯(cuò)中目睹了一場(chǎng)感人的愛(ài)情故事,提醒當(dāng)代的年輕人許多事情過(guò)去了就無(wú)法挽回,要學(xué)會(huì)珍惜現(xiàn)在。影片《調(diào)音師》中采用閃回與倒敘的剪輯手法,向觀眾展現(xiàn)了一個(gè)偽善的調(diào)音師形象,隱喻著人性的選擇的重要性。全片十三分鐘以平靜而略帶悲傷的音樂(lè),古典而富有感染力的鏡頭,鮮明又獨(dú)具特色的剪輯手法,渲染出懸疑驚悚的氛圍。結(jié)尾用音樂(lè)表達(dá)出語(yǔ)言所無(wú)法表達(dá)的內(nèi)心活動(dòng)。在跌宕起伏的電影情節(jié)中以一種開放式的結(jié)尾引發(fā)人們無(wú)盡的聯(lián)想和深刻的反思。
三、結(jié)語(yǔ)
誠(chéng)然,微時(shí)代下的微電影正在以一種個(gè)性化的影像語(yǔ)言和敘事風(fēng)格滿足著時(shí)代的尋喚,承載著人們?cè)谏鐣?huì)生活中的“微”言“碎”語(yǔ)。讓每個(gè)人都可以自由且放恣地演繹著自己的電影之夢(mèng)。互聯(lián)網(wǎng)的廣闊天空可能讓我們誤以為微電影也可以肆無(wú)忌憚進(jìn)行敘事表意,但在這看似“自由”的背后卻隱藏某種“不自由”———互聯(lián)網(wǎng)獨(dú)特的大眾傳播模式和觀看方式對(duì)作品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影響與約束。微電影作為藝術(shù)殿堂的一員應(yīng)探索符合自身的藝術(shù)意蘊(yùn),架構(gòu)獨(dú)特的視覺(jué)藝術(shù)魅力。讓人們審美情感不僅僅用于消費(fèi),而更多地指向心靈的溝通與交流。
作者:鄭心宇單位:福建師范大學(xué)福清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