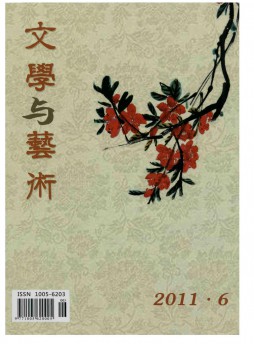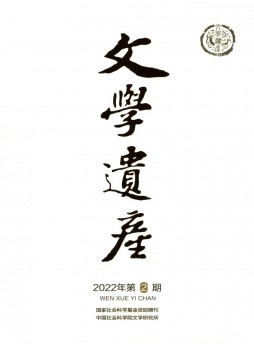文學審美的三種境界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審美的三種境界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文學藝術作為社會精神生活的一種特殊存在,具有復雜的運行過程,大體須經歷三個階段、三種境界的循環往復,方能贏得歷史的認同。本文針對制作者原創性審美標志、閱讀者層次性審美趣味和研究者“非理性”審美覺悟展開論述,試圖從新的角度切入,揭示文學藝術的某些特殊性規律。
關鍵詞:原創性審美標志;層次性審美趣味;非理性
審美覺悟在文學藝術創作過程中,只有那些思想性和藝術性并重的創新作品,才能為文壇或藝苑注入沁人心脾的清新源泉;受眾可以從中汲取營養,娛樂身心;研究者面對名典或新品,運用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思維方式,作出鑒賞批評,以建設性的解構形式,影響創作行為,引導閱讀走向。
一、文學的原創性
審美標志文學審美,是文學作為一門藝術的重要特征。經典名著的審美意義,自然不言而喻;原創性,是文學審美意義之一;名典的原創性標志,是某種陌生性。也就是說,要想贏得文學經典地位,必須具有原創性。美國學術院院士、耶魯大學教授、著名詩歌批評家、理論批評家、宗教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先生,在其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這部著作中,謹慎舉例:“貴族時代”即13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但丁、莎士比亞、喬叟、塞萬提斯、蒙田、莫里哀、彌爾頓、薩繆爾•約翰遜、歌德9位名家。“民主時代”即19世紀的華滋華斯、簡•奧斯汀、沃爾特•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狄更斯、喬治•艾略特、托爾斯泰、易撲生8位名家。“混亂時代”即20世紀以來的弗洛伊德、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夫、卡夫卡、博爾赫斯、聶魯達、佩索阿、貝克9位名家。在26位世界知名文學大師中,哈羅德•布魯姆先生認為,莎士比亞和但丁兩位,是最具有陌生感的原創性作家,他們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所有經典作家的中心。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優美語言和劇情,已經被我們無數次引用,習慣到熟視無睹的程度。而但丁的語言形式,則不大可能被后世讀者完全同化。這是兩種不同的原創性陌生[1]。
之一,何謂“莎氏陌生”?古希臘悲喜劇與莎士比亞悲喜劇,絕不雷同,絕不重復,卻又都擁有無數讀者;巴爾扎克與福克納風格迥異,也同樣為讀者熟知;拜倫與雪萊、艾略特與郭沫若、李白與杜甫,雖各具創作特色,卻并不影響他們的詩歌傳遍千家萬戶。一部中國文學史創造的輝煌,實際上就是以陌生為標志的原創性實績的輝煌。諸子散文、歷史散文、詩、騷、史傳、唐詩、宋詞、元曲、明清以降小說如“蒲氏短制”“馮凌倆人中篇”“曹施羅吳諸公巨著”等,縱觀所列文體,沒有復制品。每一種文體,相對于另一種文體,都絕不重復,絕不蹈襲。每一個大的歷史時期,甚至,哪怕是一個時間只有幾十年的王朝,也會有嶄新文體誕生。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和創新精神。哈羅德•布魯姆先生論述的“原創性陌生”理論,烙印在中國歷代文人每一步創作足跡中。以上文體,幾乎是每一位中國學人甚至是一般讀者都耳熟能詳的“家常小吃”,這便是“莎翁式的原創性陌生”。
之二,何謂“但氏陌生”?《荷馬史詩》《神曲》《浮士德》三大史詩,分別以獨特不二的藝術成就,立于文學之林,因為其對神界、夢幻和魔境的描述,與現實生活產生距離感,如果不借助于現代傳媒,就很難為一般大眾所接受。不熟悉,便陌生,甚至陌生到很難認同的程度。就中國當代文壇來說,80年代蓬勃興起的20世紀最大的一次現代派詩歌創作高峰———朦朧詩的出現,正印證了“但丁式的原創性陌生”。因為讀不明白,是以謂之朦朧;有些詩倘若一直朦朧下去,要想被廣泛認同,似乎不太可能。即便如此,也并不影響朦朧詩,在中國詩學史上的一席地位,尤其是某些經歷三四十年時間過濾而流傳下來,并被學界視為經典的詩。至于先鋒派小說創作中某些文本的某些超現實主義構架和語言形式,也是具有“但丁式原創性陌生”的,不過,能否成為經典,仿佛還有待時間的檢驗。因為,成為經典的思想性要求極高,或具公民意識,或有民主觀念,或備自由啟蒙,或有理性光照,或擁學術深度,或灑悲天憫人情懷,或憂蒼生安寧禍福,或瞻人類未來命運等。只有當語言形式和思想情懷和諧相生,進而構建的出原創性陌生,才有成為經典的可能。此外,具體到古典大賦、駢文、律詩來說,由于一般讀者的難以認同,它們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但丁式的原創性陌生”。二者的區別在于:“莎翁式的原創性陌生”,與后世讀者幾乎沒有距離感,不但可以接近,而且接近之后,還很親切,是那種融入胡同、里弄、坊間、鄉村的親切。“但丁式的原創性陌生”,與后世讀者始終保持著一定距離,似乎永遠也不可能被完全同化,仿佛是俯視蕓蕓眾生不食人間煙火的一尊神。當然,這并不妨礙它們都是經典。新文學30年中創作的經典文本和新時期以來的“傷痕”“反思”“改革”“尋根”“現代派”“先鋒派”“新寫實”等文學思潮中涌現的精品,都擁有自己獨特的思想內涵和藝術形式,彼此之間的陌生感,極為明顯。極為明顯的陌生感,凸顯了文學審美意義之一的原創性準則。哈羅德•布魯姆先生強調文學經典審美意義,強調經典審美原創性陌生感,符合偉大時代精神。科技要創新,文學自然也要創新。至于,戲說歷史、惡搞經典類新媒體行為,從娛樂大眾角度看,似乎也無可厚非;不過,戲說、惡搞,都不能過分,人類對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建設,還是嚴肅或嚴謹些更好。自然對人類的懲罰、經濟危機對人類的威脅,難道還不夠嗎?科技創新,為的是創造人類更加優越的物質生存環境;文學創新,就是要創造出人類精神領域中前所不同審美意義的經典。二者共進,方不辜負盛世中國的燦爛前景和人類的未來。
二、文學的層次性
審美趣味趣味,是客觀外部世界刺激人的感官之后,逐步進入人類個體生命的精神世界,養成的日常行為習慣和對文學藝術品的鑒賞意識。趣味,也是一種美學性情,蔓延在行動者的全部實踐領域。不僅是具有對藝術品的觀點態度,而且還反映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感覺系統和分類格式中。商品流通時代,藝術消費和日常消費的不同,主要表現在:藝術作為精致的文化商品,一方面需要個人天賦作為智力支撐,一方面還存在著社會不同消費層次和不同階級意識的差別。這里,主要根據消費群體,闡述三種不同的審美趣味。
之一,合法性趣味。作為社會主流文化允許的趣味,必須符合信用機制。家庭機制中,孩子趣味,大體要贏得家長認同,閱讀、寫作、繪畫、彈琴等,兩代人之間達成共識,一方愿做想學,一方積極支持,于是,趣味形成良性循環,向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方向發展。教育機制中,學校通過頒發和認證教育的“資格證書”,使得趣味兼具組織化和合法化,并突出了合法趣味的真理性標志。將這種合法趣味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注入常規教育,從而使任何一個試圖接受正規教育和進入合法文化領域的行動者,都身不由己地與教育機制建立起一種信用,最終成為具有合法趣味的美學性情者。當然,個人愛好形成的自由趣味和獲取資格證書爭取的必然趣味之間的對立,有時在所難免。合法趣味的特征,就是強調形式高于功能,注意趨同性,忽略差異性。教師、父母的期待,同行的壓力,導致人們把這一美學性情從合法藝術作品領域延伸到合法日常生活領域。既然合法趣味貫徹在所有領域,那么,通常也只有政府行為,才是合法趣味的真正擁有者。政府機制中,主流社會自然可以享受文化實踐和日常實踐的諸多合法趣味,比如戲劇、歌舞、影視、書畫、琴棋、體育競技、旅游觀光、文化節、藝術節等。《詩經》《楚辭》“四書五經”“唐宋八大家”“二十四史”“明清小說”等,因統治者的點贊與弘揚,必然作為經典永久傳播。
之二,中品性趣味。從整個社會空間位置來說,中產階級的中品趣味,界限含混,處境尷尬。一方面對百姓階層、草根文化的自然趣味,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試圖努力擺脫某些自認為低級庸俗的自然趣味;一方面崇拜并向往上流社會的自由趣味,對他們風格化的生活方式羨慕不已。中產階級中的多數人,本來自鄉村,鄉土情結卻沉淀在心田深處,從不外泄;大庭廣眾之下,對“高粱花子的土氣”,動不動就嘴角一撇,冷嘲熱諷。看影視劇喜歡的是都市小資情調;鍛煉身體最好是高爾夫、網球,最起碼也得是保齡球;日常聊天,必定涉及時尚話題、經濟危機、海盜贖金、股指升降、時髦服飾、熱咖啡、自駕游等,家事、國事、天下事,盡收眼底。《三國》《水滸》《西游記》《紅樓夢》可以經常讀,《當代》《十月》《收獲》《詩刊》《人民文學》《小說月報》也會時常瀏覽。中品趣味者,始終處于患得患失、忐忑不安的焦慮狀態。既沒有上流社會資產雄厚帶來的自信和因為自信產生的隨意性,以及這種隨意性背后隱藏的那份尊嚴,也沒有尋常百姓知天樂命、容易滿足的恒常心境。中品趣味者,以文化客體形式存在,處于社會文化的中間位置,通常缺乏確定性趣味的價值評判標準。他們中的相當一部人,對于文學藝術趣味的美學性情,或表現為錯誤認同,或表現為信念誤置,或依附于上流社會,或游弋于山水稗麥,接受快,遺忘快,波動大,變化大。有時,熱衷于將合法趣味的文化作品淺薄化、邊緣化;有時,熱衷于將非合法趣味的文化作品賦予合法性、政治性。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將迥然不同的兩種文化融為一爐,從而置于自己可以理解、可以親近的審美趣味范圍之內。不久前播放的電視連續劇,亦舒的作品《我的前半生》,寫商海遨游,個人奮斗題材,或許即是其某種特定時刻最佳的精神食糧。
之三,大眾性趣味。作為過慣日常簡單適度生活的大眾群體,自然傾向于接受簡單適度的趣味。對他們來說那些生活藝術中的美學概念不值一提,至于為藝術而藝術的形式主義的東西,更是明確拒絕。大眾的美學趣味,往往就是那種感官的、敘述的、自然的、直接的、實實在在的東西。比如《封神演義》《大明宮詞》《康熙微服私訪記》《還珠格格》《雍正王朝》《鐵嘴銅牙紀曉嵐》《宰相劉羅鍋》《亮劍》等,只要賞心悅目即可,有時不必非得具備崇高和深不可測的美學品位。趙本山師徒、來自黑土地的“二人轉”、陜北信天游、安徽黃梅戲等表演,對于居住在鋼筋水泥森林叢中的現代都市中人來說,既可一解對原始的飽含土腥味的鄉村田野的思念和神往,又可娛樂身心、快意閑暇、釋瀉郁結,于是,和全國人民一道,領略其風采,又何樂而不為呢。老舍、趙樹理、池莉等人的作品,有最廣大的草根族“粉絲”,何愁沒有自己的趣味市場。大眾性趣味,內容非常廣泛。棋弈、淘寶、垂釣、品茗、遠足、逛街、串親、涂鴉、裁剪、刺繡、聽戲、飲酒、追星、習武、健身等,應有盡有,而不是非得形而上的精雅文學藝術,集中表現出隨眾性和比較性特征。他們既隨大流,又與人攀比,力求入流,不至于因為落伍,而為人詬病或哂笑。大眾性趣味中的某些為人捧抬的優秀作品,有時憑借現代傳媒,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躥紅,并被主流文化接受、流傳。比如雪村、范偉、趙本山、高秀敏、潘長江、閆妮等。具備大眾趣味者,對于合法性趣味和中品性趣味的美學性情,能夠持一種非常寬容理解的姿態。鳳凰,雖陽春白雪,卻遠水解不了近渴;野雞,雖難登大雅,卻山林易見。誰也代替不了誰,各安天命,順其自然。20世紀法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布爾迪厄先生,在其代表作《區隔》中,運用“趣味判斷和社會批判”觀念,批評了以康德為代表的“純粹美學理論”,否定了美學經驗的普遍性原則。將人類的美學趣味作了科學區分,為讀者和學者,提供了處理日常生活行為習慣和接觸文學藝術作品時,另外的思維模式和品嘗思路。
三、文學的非理性審美覺悟
古今中外文學創作者及其筆下人物行為,因非理性而乖張癲狂者,不勝枚舉。長期以來,無論現實生活中,還是文學意境中的瘋狂存在或瘋狂描述,都令具有正常理性的人,猶如拒絕麻風病人一樣避之不及。不過,在法國哲學家福柯先生《瘋狂與非理性———古典時代瘋狂史》一書中,卻堅定認為:瘋狂不是一種自然疾病,而是知識文化的另外一種建構。福柯先生的說法,似乎給我們提供了思考問題的另外一個重要途徑。
之一,瘋狂或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理性。中國古代嵇康、阮籍和淘淵明三位著名詩人,或虱多冠斜,或青白眼輪,或醉臥籬下,似乎都是非理性瘋狂行為。他們的瘋狂,表面看與當時的理性相對,其實是人的另外一種存活方式。司馬氏集團迫害,剛烈如嵇康自知難逃一死,慎言如阮籍亦勉為勸進;朝廷腐敗昏聵,喜好酣飲如淵明尚折腰于五斗。看似政見不同,其實是知識背景不同,亦即文化形態選擇的不同。不與陰謀政治和強權統治構隙,只能委曲求全,以他類方式展示人生。既與時人有異,被視為瘋狂,在所難免。為了達到自己堅守的生存境界,必須采取在別人看來是非常態非理性的行為方式,以文飾自己的真實思想。當瘋狂轉換成理性的另一種形式時,外在瘋狂就是內在理性。孫臏、屈原、張旭、懷素、米芾之癲狂和賈寶玉、范進、孔乙己、祥林嫂、蘩漪、曹七巧、隋不召(張煒《古船》)、鹿三(陳忠實《白鹿原》)[3]之瘋狂,似乎都是另一種不同知識文化環境下的理性。西方作品中,莎士比亞筆下著名的哈姆雷特王子,是瘋狂的復仇者,也是理性的判決者;是瘋狂的毀滅者,也是智慧的生存者;是瘋狂的理想主義者,也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瘋狂和理性,如此和諧或不和諧地集中于一人身上。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和桑丘主仆倆人,行為瘋狂、荒誕、離奇。作家以現實主義創作態度,描繪了恢復封建騎士制度的主觀幻想與資本主義興起階段的丑惡現實的尖銳對立,實現了小說文本的人文主義思想啟蒙。16世紀的人文主義輝光,渲染了一幅天幕般的文化背景。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主仆形象,正好印證了福柯先生的觀點:文藝復興時期瘋狂和理性可以互為轉化。
之二,瘋狂不再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理性。古代中國,齊國太監豎刁,推薦廚子易牙給齊桓公;易牙將自己三歲的兒子蒸熟了,捧給齊桓公品嘗,以表達自己的忠誠。多么瘋狂的舉動啊!一個連親子都不愛的人,難道還會愛別人?曹操先是殺朋友呂伯奢一家,后來殺名儒孔融與名醫華佗,實踐了他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生哲學,寧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多么瘋狂的行為,多么令人恐怖的言語。《水滸》中的李逵,動輒揮動兩柄板斧,不問青紅皂白,不管男女老幼,便迎頭砍去,死在他斧下的冤魂不知有多少,真是一個嗜血成性的瘋狂魔頭。什么樣的異樣生活環境或文化背景,構建出他們這樣的非理性瘋狂?西方文學里,哈姆雷特王子的情人奧菲莉婭,因為父親被情人誤殺,情人又處于壓抑瘋癲狀態,終于不堪精神重壓,瘋狂致死。這是實實在在的瘋狂,是柔弱性釀造的瘋狂。羅切斯特的妻子,因家族遺傳疾病瘋癲,只有鎖鏈加身,長期囚禁,即便如此,她仍然莫名其妙地伺機縱火、夜游、毆人,以至于焚毀桑菲爾德莊園,這也是真正的瘋狂,是暴戾性孕育的瘋狂。在她們的精神世界中,一定存在著另一種感知世界、認識世界、審讀世界的價值體系,也就是被稱作文化的東西。簡愛瘋狂地愛羅切斯特,甚至遠在他鄉,也能感受到羅切斯特的呼喚,實現心靈感應,最后,在面目全非的莊園里準確找到羅切斯特的位置。愛情,終于燃起瘋狂的火焰。簡愛和羅切斯特,先是表面的平靜和理智,掩蓋了激情燃燒的真實軀體。后是瘋狂的激情沖向理智的堤壩,終究實現和而為一。這里,瘋狂就是瘋狂,已經不再是理性的另外一種形式了。他們的瘋狂是激情飽經煎熬之后的爆發。在文化教養、知識結構和社交環境構成的綜合背景下,他們的瘋狂,應該是有節制的瘋狂[4]。奧菲莉婭和羅切斯特的妻子,以死完成瘋狂的理性;簡愛和羅切斯特,以愛完成理性的瘋狂。前者和后者是處于兩個極端的瘋狂,不可轉移,也難以轉移。福柯先生認為:這里的瘋狂,應該就是單純的非理性,已經被排除在思想領域之外。在17—19世紀,這種排除尤為明顯。
之三,瘋狂為現代精神醫學進一步排斥。福柯先生認為,由法國匹奈和英國突克創立的新型精神病院,并不是“科學”醫療機構,他們只是使用隔離、觀察、監視、審判等技術的道德改造所。他們不可能成為瘋人的解放者。現代精神分析法,一方面消解了初始精神病院的原有功能,一方面使作為精神疾病的瘋狂完全被所謂的現代醫學科學控制和支配。于是,紛紜復雜的非理性“瘋狂”,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上就橫沖直撞起來[5]。某些狂人和瘋子,如果成為社會理性的顛覆者,這個社會是不會接受他們的。此為一類。公元1989年海子在河北山海關臥軌自殺;兩個月后,時人號稱北大三詩人之一的駱一禾自殺;公元1993年顧城在激流島用斧頭砍死朦朧派詩人之一的妻子謝燁后自殺;在此前后,蝌蚪(陳泮)、戈麥、岳冰在疾患中逝去;北島、江河、駱耕野則遠走異國他鄉。死了,永遠走了;遠游,暫時走了。瘋狂的朦朧詩派,幾乎是瞬間土崩瓦解。可不可以說,在詩歌激情掩飾下的瘋狂的詩人,當他們成為社會慣常理性的叛逆者時,推拒常規理性、尋求標新立異、構建新我,自然成為藝術追求的一種必然向往。他們是詩歌藝術的瘋子,是思想領域超越他人、面對現實卻無可奈何的精神落魄者。此為一類。蒲松齡、曹雪芹、梁啟超、周樹人和戈雅、薩特、尼采、梵高、阿爾托、荷爾德林等文學藝術家和哲學思想家,以自己不可衡量的作品衡量自己。因為,自從非理性被剝奪了瘋狂的真理性那一面,非理性的存在,只能以某種個別的情況顯露出來。這種個別情況就如同那些劃破夜空的閃電,比如上述諸人作品,凸顯了瘋狂的狡智和人類的新勝利。他們的瘋狂作品,為瘋狂和這個世界,作了最好的辯解。此為一類。三類瘋狂,都擁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知識文化背景,這也是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差異的瘋狂。他們的瘋狂,都為現代精神醫學排斥。前二者,經歷推拒、排斥之后,毀滅或逃逸遁跡。后者,則迸射出異樣的瘋狂理性,創造出人類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真人類之幸也。不是自然疾病,而是知識文化的另外一種建構。福柯先生說得好啊,在特定的環境背景下,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思想。誰瘋?誰不瘋?誰說得清?瘋也不瘋,不瘋也瘋,才是真理。綜上所述,肯定某種陌生、肯定某種差異、肯定某種懸殊之后,文學藝術審美的原創性,足以吸引不同層次受眾對于經典或新作品產生廣泛興趣,從而推動文學藝術研究步入嶄新境界,發現新思想,開掘新途徑,完善新人格,構成文學與人生、文學與社會的和諧生長。
參考文獻
[1]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M]//趙憲章.20世紀外國美學文藝學名著精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30.
[2]布爾迪厄.區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M]//趙憲章.20世紀外國美學文藝學名著精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310.
[3]陳忠實.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358.[4]夏洛蒂•勃朗特.簡愛[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569.
[5]福柯.古典時代瘋狂史[M]//趙憲章.20世紀外國美學文藝學名著精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99.
作者:曹為 單位:合肥師范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