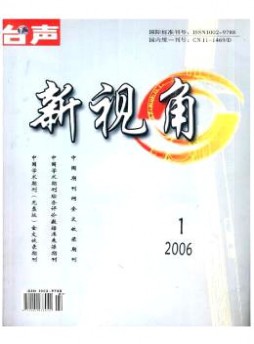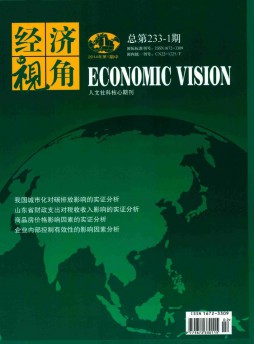“他者”視角下北京形象變遷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他者”視角下北京形象變遷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山花雜志》2015年第二十二期
京味文化固然形成了一些被人們所認(rèn)為的固定特征,如獨特的京味語言(京片兒),以胡同、四合院為標(biāo)志的建筑,但是,也從來沒有停止變化的步伐。于是,“他者”視角成為考察京味文化變遷的一個合理有效的角度。京味文化的形成是在漢文化的基礎(chǔ)上,融合滿、蒙等少數(shù)民族文化,并經(jīng)多年融合、轉(zhuǎn)化形成一樣,京味文化一直以來,都是在與其他地域、民族、國家文化相互磨合、碰撞的過程中,不斷更新著自己的內(nèi)容與表現(xiàn)形態(tài)的。因而,從城市移發(fā)的“他者”視角對京味文化的變遷進(jìn)行研究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xiàn)實價值。對京味文化及北京形象變遷的研究,在王一川教授的著作《泛媒介場中的京味文學(xué)第三代》及其相關(guān)論文中已有所涉及。王教授認(rèn)為,隨著媒介從紙媒向影視等電子媒介的快速轉(zhuǎn)換,京味文學(xué)第三代借影視文學(xué)蓬勃發(fā)展,但是在完成了從高雅文化向大眾文化的轉(zhuǎn)變之后,“作為一種以品味故都流興或殘韻為集中標(biāo)志的現(xiàn)代地域文學(xué)現(xiàn)象,京味文學(xué)終結(jié)了。”王教授最后以充滿期待的心情寫道:“不妨預(yù)期,小區(qū)與胡同和大院的并存及小區(qū)與周邊城鎮(zhèn)或鄉(xiāng)村的交錯,多種多樣北京的人交匯,形形色色北京話、普通話或外地方言等的交響,都注定了會成為21世紀(jì)新京味的有力的生長場。當(dāng)故都流興已成絕響,新京味何以發(fā)生不妨拭目以待。”①那么,我們的問題是,新京味到底表現(xiàn)出哪些特點?新京味與傳統(tǒng)“京味文化”有哪些關(guān)系?隨著新京味的出現(xiàn),北京形象發(fā)生了哪些變化?
一、語言:從京片兒到“南腔北調(diào)”
提到“京味文化”,其鮮明特征首推北京的語言,被稱為“京片兒”的北京話。從老舍《茶館》中地道的北京話,到陳建功《鬈毛》里那句“敢情!”再到王朔的小說中主人公帶有幾分油滑的調(diào)侃語言,北京話都是作為京味文化的一個鮮明特征被人們所稱道的。“北京人如珍視其文物古跡、珍視其胡同四合院一樣,珍視北京話。”②《京華煙云》《城南舊事》,老舍作品中的人物都表現(xiàn)出對北京話的迷戀。地道的北京話,不僅是語言內(nèi)容的載體,更是北京人性格、情緒的體現(xiàn)與表達(dá)。作為明清時期的帝國中心,北京城中并非只有北京話一統(tǒng)天下,但與其他方言相比,北京話的優(yōu)越性,卻是十分突出的。“京師人海,各方人士雜處,其間言龐語雜,然亦各有界線,旗下話、土話、官話,久習(xí)者一聞而辨之,亦間摻入滿、蒙語……又有所謂回宗語、切口語者,市井及倡優(yōu)往往用之,以避他人聞覺,更子后則往往摻入一二歐語、日語,資為諧美而已,士大夫弗屑顧也。”③這里雖然寫出了舊京亦有“南腔北調(diào)”甚至外國語的現(xiàn)象,但是更突出強調(diào)的,應(yīng)該是其中的“各有界線”,因“久習(xí)者一聞而辨之”,“士大夫弗屑顧也”。
這種狀況,到了現(xiàn)當(dāng)代有了明顯的變化。帝制的廢除,人民政權(quán)的建立,將人從三六九等的等級制度下解放出來,全都成為社會的主人。在語言方面,也將帶著鮮明等級的官方、貴族語言與普通大眾的語言解放出來。1956年前后,普通話的全國推廣行為,也對北京話起了不小的沖擊作用。老舍的京味文學(xué)那字里行間透露的北京味,演變成只言片語的殘留,再到王朔的調(diào)侃式北京話,普通話的成分更大,而地道的北京話,越來越淡出人們的視線。北京話的變味,首先表現(xiàn)在普通話代替了北京話。近些年來,故事發(fā)生在北京的影視劇,多采用普通話。《新結(jié)婚時代》中,顧小西的爸爸媽媽,一個是大學(xué)教授,一個是醫(yī)生。但是他們的語言中已經(jīng)完全沒有了北京話的痕跡,而是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北京青年》中土生土長的北京四個堂兄弟,何東、何西、何南、何北,甚至他們的父母親一輩,其語言中也難覓一點老北京話的足跡了。其次,各地方言、港臺味與北京話混雜。影視劇中用方言的現(xiàn)象越來越多,如唐山話、河南話、山東話屢屢出現(xiàn)在影視劇中,在馮小剛導(dǎo)演的《甲方乙方》中,雖然主要還是王朔色彩的調(diào)侃味語言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但在李琦表演的山西廚子那個橋段里面,已經(jīng)流露出一些“南腔北調(diào)”的味道了。賈樟柯導(dǎo)演作品《世界》王小帥《十七歲的單車》,展示的是都市外來務(wù)工人員在北京的生活狀態(tài)。其中的山西方言、貴州方言,已經(jīng)滲入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其他如范偉的東北腔、李瀚祥的河南味、黃渤的山東口音,等等,與北京話相互混雜在一起,人們也見怪不怪了。《杜拉拉升職記》中的王大偉操著一口港臺普通話的現(xiàn)象在影視劇中已經(jīng)屢見不鮮了。在一個以北京為背景的故事中,創(chuàng)作者們不僅不避諱各種口音,甚至熱衷于用“南腔北調(diào)”來展示京味文化向現(xiàn)代化的轉(zhuǎn)變。北京的語言經(jīng)歷著從“京片兒”到“南腔北調(diào)”的轉(zhuǎn)變。
二、城市空間:從大雜院到“大褲衩”
北京作為一座國際性都市,吸引著四面八方的“移民”投入其中,他們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形成獨特的“移民”文化。從明清時期的人口大遷移,到近現(xiàn)代文人從四面八方在北京聚集,再到現(xiàn)當(dāng)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因素引發(fā)的外來人口涌入北京。這些城市“移民”在北京尋求他們的發(fā)財夢、明星夢、仕途夢、城市夢等。如同本雅明《發(fā)達(dá)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中的“游蕩者”一樣,他們觀察著城市,發(fā)現(xiàn)著城市。北京,在他們眼中,有著全然不同的面貌,構(gòu)成迥異于“老北京”眼中的城市文化的一道獨特風(fēng)景線。外來務(wù)工人員對城市建設(shè)的貢獻(xiàn)功不可沒,正在建設(shè)的樓群、寫字樓里的搬家工、清潔工、快遞員,都參演著北京故事的講述。《北京愛情故事》開場的“跳樓”場景,就在國貿(mào)附近的大廈頂上,置身城市之中,遠(yuǎn)眺CBD樓群,城市空間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充滿了張力。咖啡館、酒吧、高級商場、取代了老北京天橋的表演、賣東西的吆喝。北京的家庭倫理劇,將人物、情節(jié)限定在單元樓里面,那里面,住著冷冰冰的岳父岳母,歧視外地人的“第一代移民”,住著惡婆婆、兇媳婦。四合院里鄰里間的相互忍讓、爭斗,大雜院里鄰里之間的相互幫忙,變成了北京人與外地人之間的喜樂悲歡。寫字樓里上演著辦公室政治,為了地位、財富的明爭暗斗。“爭職記”、“厚黑學(xué)”是當(dāng)代北京人的處世哲學(xué)。
三、人物形象:從“北京爺們兒”到“鳳凰男”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在北京打拼,純正的“京味文化”正不斷被“移民文化”所沖擊的背景下,北京題材的影視劇中體現(xiàn)得更多的是城鄉(xiāng)矛盾、階層差異。如果說《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京味文學(xué)的絕唱,“京味文學(xué)中的主人公還沉浸在樂觀的自我滿足”中的話。之后的北京題材影視劇,更多地展現(xiàn)伴隨“移民文化”而來的城鄉(xiāng)矛盾、階層差異。從2006年播出的《新結(jié)婚時代》開始,北京題材的影視劇就一改張大民那種在自我調(diào)侃中隱忍地過活的主題,變成“鳳凰男”與北京女的婚姻家庭生活矛盾的大戲,“何建國出身農(nóng)村,不是城市近郊,比如昌平懷柔之類,是典型的農(nóng)村:山東沂蒙山區(qū)。小西媽曾帶醫(yī)療隊下過鄉(xiāng),太知道那種農(nóng)村是怎么回事兒了,因而堅決反對女兒的這樁婚事,”劇中對顧小西嫁給“鳳凰男”,多少帶有一些同情色彩。對農(nóng)村出來的何建國及其家人身上先天具有的農(nóng)村氣質(zhì)與觀念,絲毫不留情分。《岳母的幸福生活》中麻辣岳母趙慧玲的“三不”擇婿標(biāo)準(zhǔn),“第一不”就是“不找外地的”,因為對于北京女孩兒來說,找外地女婿就會帶來“戶口問題”、“房子問題”以及“婚姻問題”。特別是外地男人,受傳統(tǒng)觀念影響,會把父母接來大城市生活,就會產(chǎn)生地域文化差異、生活習(xí)慣差異帶來的婆媳矛盾問題,勢必影響家庭和諧、婚姻穩(wěn)定。《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中小米媽給女兒下死命令,不能找外地人,“非北京男孩不嫁”。《新女婿時代》中丈母娘李桂蘭,想盡一切辦法,試圖阻止丁勝利跟女兒的成親,歸根結(jié)底就是因為丁勝利在北京土著人眼里是“無房無車無錢”的北漂一族。除了外地女婿受歧視之外,外地媳婦也受歧視,《誰來伺候媽》里林母給開出租的兒子找對象,當(dāng)?shù)弥獌鹤訜釕偕蠔|北來京的打工女金巧時,強烈反對,甚至發(fā)誓不參加婚禮,因為在她看來,金巧不過是為了兒子的北京戶口和房子而已。我們看到,北京就是資本,北京人有著作為優(yōu)勢地區(qū)人群的優(yōu)越感,而這種地域歧視的背后,更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平衡、城鄉(xiāng)貧富差距之下的“賤貧”心理的體現(xiàn),因為所謂外地女婿、外地媳婦的背后,就意味著一個落后的家鄉(xiāng)、一個貧窮的家庭。
于是,“地域歧視”中與優(yōu)勢地區(qū)人群的優(yōu)越感相應(yīng),還有劣勢地區(qū)人群的自卑感。《新女婿時代》中丁勝利與向美麗的婚姻,在他自己看來也是癩蛤蟆與白天鵝的搭配,這份愛多少帶著自卑,所以甘愿為牛為馬把媳婦奉為女神,正像片頭曲唱的“我上得廳堂下得廚房,不怕累和臟;我睡得比你晚,我起得比你早;擦地洗衣淘米做飯,菜炒得噴噴香;工作家庭兩頭忙,我對得起孩兒他娘。”更為明顯的還有《金太狼的幸福生活》,來自東北的金亮父子并沒有強調(diào)東北地域的身份認(rèn)同,而通過所謂的皇胄后裔身份,來拉平北京的“地域歧視”,從而獲得象征性的所謂面子和平等。金老頭時刻強調(diào)“咱們家是皇族后裔”,你奶奶是前清格格,而且還要兒子反復(fù)告訴別人細(xì)節(jié),你奶奶每次進(jìn)宮,“走的都是正門”,這一切都要如實地講,因為“人活這一輩子,就是為了個面子”。
在這類家庭倫理劇里面,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主人公從純“北京爺們兒”,變成一個個從農(nóng)村跳龍門一樣跳到北京的“鳳凰男”。于是,劇集的主題也從北京爺們的或傲慢,或隱忍的故事,變成鳳凰男與北京女的城鄉(xiāng)差別。結(jié)合“北漂、蟻族、高富帥、富二代、屌絲”等詞匯的流行,老北京人身上那種潛在的優(yōu)越感正在一點點流失,代之而起的,是新京味文化的主人公們在當(dāng)代社會夾層中尋求生路的辛酸。“多少人走著卻困在原地,多少人活著卻如同死去,多少人愛著卻好似分離,多少人笑著卻滿含淚滴,誰知道我們該去向何處,誰明白生命已變?yōu)楹挝铮欠裾覀€借口繼續(xù)茍活,或是展翅高飛保持憤怒,我該如何存在。”將一系列悖論的詞語組合在一起,展現(xiàn)著當(dāng)代青年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苦苦掙扎的狀態(tài)。如同正在飛速變化的城市一樣,作為城市文化重要標(biāo)志的“京味文化”無異也在發(fā)生著巨大的變遷。我們要做的,并不是阻止、反對北京形象的變化,而是在這種變化中分析其時代特征,厘清其背后的動因,把握其未來發(fā)展方向。
作者:周春霞 田麗艷 單位:北京聯(lián)合大學(xué)應(yīng)用科技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