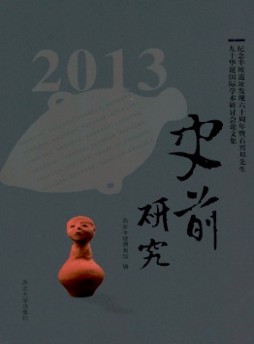史前文化缺首葬俗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史前文化缺首葬俗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青海社會科學雜志》2015年第四期
割肢葬,又名毀尸葬,指人們出于某種信仰對死者實行一定形式的毀壞尸體的安葬方式[1]。由于毀壞部位不同,又有不同的名稱,如割指葬、缺首葬、缺肢葬、斷趾葬等。而缺首葬則是指此類葬俗中對死者的頭骨脫離原身體的埋葬方式,包括單獨埋葬頭骨或無頭尸骨等多種形式。以下僅就青海地區史前時期考古工作中發現的缺首葬葬俗所蘊藏的文化現象進行探討。
一、考古中發現的缺首葬現象
青海史前時期的缺首葬現象多見于墓葬中,少數發現于灰坑中。根據頭骨的有無及與肢體的相對位置的不同,可分為以下三類:A類:僅見頭骨,肢體部分缺失。此類又可分為僅見單個頭骨和多個頭骨兩種情況。僅見單個頭骨:如樂都柳灣墓地馬廠類型早期M505內有三個個體。西側個體為一少年女性,四肢不全;東側個體為一成年男性,仰身直肢。隨葬品較豐富,其中斧、鑿、錛、刀等石器置于西側個體頭骨附近,陶器放在東、西側個體頭上方或腳下方,共45件。另一個體僅是一具頭骨,置于西側個體腳下,其周圍沒有隨葬品,地位當與周圍的其他隨葬品相當。
有多個頭骨:樂都柳灣墓地齊家文化M1179內有四個個體,置于獨木棺內的墓主人為35歲左右的男性,仰身直肢,身首分離,下頜骨放在腿骨上;其余三個個體只有頭骨,放在木棺周圍,東側有兩個個體,為18-22歲的青年男性(A)和10歲的男童(B),西側個體為7歲男性(C)。在墓主腳下放置高領雙耳罐、侈口罐與陶壺等6件;在B個體東側放置陶壺4件;在C個體北邊放置有陶盆、雙耳陶罐、鸮面罐等5件陶器。M979有五個個體,除仰身直置于獨木板內的35歲左右男性墓主外,其余4個個體僅有頭骨,皆放置在棺外,其中3具位于棺外東側,1具置于棺外西側。僅棺外東側頭骨附近放置一枚海貝。[3]B類:墓內頭骨缺失,只見肢體部分。民和陽山半山類型墓葬M24內埋葬兩個個體,均沒有頭骨,只剩下身體部分。兩個個體人骨架擺放有序,俯身直肢,沒有人為擾亂的痕跡,屬一次葬。南側個體為25-30歲男子,北側個體為6-8歲兒童。南側男子頭部隨葬石球、石鑿、石錛、彩陶盆、夾砂陶小罐、斂口罐、陶紡輪等12件;北側兒童頭部隨葬彩陶壺、彩陶盆、夾砂陶小罐、斂口罐等10件。二者腳下方隨葬石鑿、彩陶甕、彩陶壺、夾砂陶小罐等共7件。
柳灣墓地M1337內埋葬兩個個體,北側個體為男性,仰身直肢置于棺中;南側個體為女性,置于棺外,不見頭骨,仰身屈肢側向男性,部分腿骨膝蓋壓在木棺下,在腿骨上還壓有兩塊石頭。男性頭骨處隨葬一粗陶雙耳罐,男性腳下方棺外及女性頭頂處隨葬陶器6件。女性右胳膊處隨葬一高領雙耳陶罐,腰處隨葬一件帶嘴陶器。[5]貴南尕馬臺遺址齊家墓地發現缺首葬6座,分別為M7、M9、M15、M16、M17、M18[6]。M9和M15均為單人葬,墓主人都沒有頭骨,只剩下身體部分。均為男性,俯身直肢,左臂彎曲,右臂直肢或彎曲。隨葬品僅有裝飾品。M9左腿脛骨附近隨葬骨珠,海貝散放于左臂外側。M15僅在雙腿股骨隨葬骨珠。M7和M18墓內均有兩個個體,都沒有頭骨,只剩下身體部分,均為一次葬。M7均為男性,俯身直肢,北側個體左臂彎曲,右臂直肢,脛骨處隨葬一塊豬骨;南側個體雙臂彎曲,手骨被割。除隨葬1件石器外,其余為裝飾品,骨珠主要隨葬于股骨間,少量在其右腳附近。M18南側個體為男性,左臂上伸,右臂向下彎曲,缺肱骨。細石器、骨鏃置于右腿股骨處,骨珠置放于男性股骨周圍;北側個體為女性,雙臂向下壓于盆骨下。頸部放置綠松石珠,左手腕戴有骨腕飾。
M16內有三具個體,南側小孩無頭骨,只剩下身體部分,俯身直肢。成年男性置于墓室之中,俯身直肢,左臂向上彎曲,頭部被砸碎,僅存幾塊碎片,肩胛骨發現于填土中;小孩分置于南、北兩側。北側小孩為二次擾亂葬,頭骨殘存幾塊碎片,左側肢體被擾亂。無隨葬品。M17為兩個個體,北側個體無頭骨,男性,俯身直肢,左臂向上彎曲,右臂下伸手骨壓于盆骨下;南側個體為女性,二次擾亂葬,俯身直肢。男性雙腿股骨間隨葬骨珠、細石葉。C類:身首異處,即死者被割頭,除肢骨外,頭骨放置于填土或墓內的陶罐內。樂都柳灣墓地馬廠類型中期M211為單人墓,墓主人無頭骨,成年男性,仰身直肢。近墓門處隨葬的M52號甕內裝有人頭骨。樂都柳灣墓地像M211將死者的頭骨另置于一粗陶甕的現象,在馬廠中期M542和馬廠早期M506中也有類似情況存在。[7]貴南尕馬臺遺址齊家墓地M38為單人葬,墓主人的頭骨置于填土中,男性,俯身直肢,雙臂下伸直肢。僅頸部隨葬海貝、綠松石珠、骨珠相組合的串飾。此外,在灰坑中亦所見缺首現象,如大通長寧遺址齊家文化H124①層中僅發現一具人頭骨,無隨葬品,屬缺首葬中的A類。[8]由以上可以看出,無頭葬“大體上說,缺頭現象上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只見頭骨,不見肢體;一種是只見肢體不見頭骨;一種是頭骨與肢體都見,但首身分離”[9]。
二、缺首葬的表現形式
這些缺首葬在墓葬中的表現形式不甚一致,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多種多樣,獵首或被獵首。諸墓葬具體屬于哪種類型,還需要從墓葬本身所反映出的信息,如墓主的位置、缺首者所處的方位以及隨葬品的放置位置等多方面加以考察。
(一)獵首柳灣墓地M505中共有3個人類個體,其中兩個個體屬于正常埋葬,隨葬品放在正常埋葬的兩個個體頭骨附近或腳下方,應該是墓主;另一個則僅有一具頭骨,且置于左側墓主的腳下方,且附近無隨葬品,可見其地位較墓主低下,可能是用獵首來的頭骨來埋葬的。M211內有一個個體,墓主人為成年男性,仰身直肢,無頭骨,在頭部置一彩陶體。近墓門處隨葬的陶甕內裝有人頭骨。這種情形在542號墓和506號墓中均出現過。這具頭骨有可能是墓主人的,也有可能是獵首頭骨來埋葬的。柳灣墓地M1179中的4個個體,男性位于棺內,身首分離,為墓主人,而棺外的三個個體位于木棺周圍,且僅有頭骨,頭骨與隨葬品雜陳。M979棺外兩側有四個頭骨。這些頭骨置于棺外,與隨葬品雜陳,有可能是用獵首來的頭骨埋葬的。尕馬臺遺址齊家墓地M38在填土中發現的頭骨與上述M211相似,這具頭骨有可能是墓主人的,也有可能是獵首而來埋葬的,也有可能是獵首其他的首級充作陪葬的。對于灰坑中的頭骨,很可能是獵首來了頭骨后來作為祭祀而直接埋入所致,也有可能是作為垃圾而被丟入灰坑中的。
(二)墓主被獵首尕馬臺遺址齊家墓地M7、M9、M15、M16、M17和M18均屬于無頭埋葬,有隨葬品,但是較少,僅有裝飾品。M9與M15墓內有一個個體無頭埋葬;M7與M18墓內有兩個個體無頭埋葬;M17墓內有2個個體,北側個體無頭埋葬;南側個體為二次擾亂葬;M16中有3個個體,其中有兩個個體屬于正常埋葬(一成年一小孩),成年男性置于墓室之中,僅南側小孩無頭骨,無隨葬品。缺失的這些頭骨可能被獵首,所以只好安葬無頭尸身。從尕馬臺遺址齊家墓地整體情況看,埋葬人骨架完整的墓葬墓主人隨葬品豐富,如M25隨葬品種類多,有陶器、銅器、裝飾品等,頭骨前放置生活用具2件,雙耳彩陶罐放置在粗陶盆內。裝飾品有海貝11枚、骨珠583枚、綠松石珠16枚組合置于頸部;銅泡2件置于左手腕外側;銅鏡置于骨架下的胸部處。而無頭埋葬的墓主人僅隨葬一些佩帶的裝飾品。從墓葬埋葬位置看亦有區別,墓地中的整體葬埋葬在墓地中部,而無頭埋葬的則位于墓地的東北邊緣。缺首墓葬的單獨放置可能與對兇死者的處置有關。兇死者一般實行特殊的葬法,其中包括缺首葬。如海南島有些黎族,正常死亡實行土葬,使用獨木棺,歸葬氏族墓地;兇死者則令人畏懼,不能入墓地,葬具比較簡陋,但送葬時要走彎曲的路,下葬時采取俯身葬,以木錐釘尸,上面壓有巨石,然后才填土。據說這樣死者就翻不了身,永遠不會擾亂活人,即使亡靈回來,也找不到歸途。[10]陽山墓地M24中的2個個體均屬于無頭埋葬,與其他墓葬一起葬入公共墓地,位置并不特殊,葬式都是俯身葬,與其他正常死亡者一樣,而且隨葬品的數量、品種也都與其他墓葬一樣,報告中認為是一種非正常死亡現象。[11]柳灣墓地M1337內埋葬2個個體,其中北側個體屬于正常埋葬,為男子,置于棺內;南側個體不見頭骨,為女性,置于棺外,部分腿骨膝蓋壓在木棺下,在腿骨上還壓有兩塊石頭。其中石斧置于男性的腰部,陶罐放在頭部,綠松石放在頸部,其余陶器放在腳下方。棺外的這具無頭骨女性有可能是被獵首后埋葬的。“因此原始社會墓地中經常發現的無頭葬就是被其他部族獵取了人頭的結果。”
三、相關民族學材料
從上述考古資料可以看出,青海史前時期有著形制多樣的缺首葬現象。這些各自不同的缺首葬所蘊藏的意義是什么?反映了怎樣的社會習俗?只能依托缺首葬本身的考古學信息,結合民族學材料來解釋這種獨特的葬俗現象。僅使用頭骨的缺首葬,無論單個頭骨,還是使用多個頭骨,這些頭骨都是獵取而來的。這些頭骨與隨葬器物一般放置在一起,故推測這些頭骨的地位與隨葬品大體相當,可視作墓主的隨葬品的一部分。這些頭骨的來源是獵取了別的人頭,亦或是砍下死者家內奴隸的人頭來隨葬的,則不得而知。柳灣墓地M1337為成年男子和女子合葬,屬于一次葬,其中女子的頭骨不存,從墓中放置的相對位置可以看出,兩者地位是不平等的,男性仰身直肢,置于墓室中央,女性位于棺外,仰身屈肢側向男性,這一現象與甘肅永靖秦魏家[13]、武威皇娘娘臺[14]發現的男女合葬墓情況相同,所以推測該墓葬為男女合葬墓,但其地位是妻子還是侍妾,頭骨為何缺失,則無從考察。陽山墓地M24兩個無頭埋葬者采取了俯身的葬式。在尕馬臺遺址齊家墓地中,可辨葬式的無頭埋葬者均采用了俯身的葬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尕馬臺遺址齊家墓地中的缺首葬都被放置在墓地邊緣位置,與正常墓葬雖然在同一區域,卻有著明顯的間隔,反映出有意而為之的區別對待。這一現象與古代對惡死者的區別對待較為近似。同時作為一種特殊的葬俗,尕馬臺遺址齊家墓地內的俯身葬與海南島黎族下葬時采取俯身葬相一致。黎族采用的這種俯身葬是一種兇死者的處置方式[15],因此尕馬臺遺址齊家墓地中發現的缺首葬有可能是兇死者。因此,懷疑此墓地內墓主是被獵首后,被自己族人作為兇死者分區埋葬。
在填土或陶甕中發現的頭骨,有可能是墓主人的,也有可能是本氏族成員的頭被別的氏族獵去,又從別的氏族獵來人頭安置于失頭者墓中。目前,我們雖無法確切知道這具人頭骨的具體意義,但根據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墓葬中發現的以陶罐代替墓主失去的頭顱的現象推測,可能是用來代替獻祭過程中不足數的人頭的,用陶器代替頭顱,這在一定意義上蘊含有讓死者“死而復生”之意[17]。對于灰坑中發現的人頭骨現象,在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時期也時有發現。如在河北邯鄲澗溝遺址的龍山文化灰坑中發現有“單一的頭骨(如T16H2)”。這些有可能是在祭祀過程中直接埋入的,用以祭祀田神或祭谷。用獵取的人頭祭祀神靈的行為,這種情況在我國史前遺址是常見的。有學者研究認為,將人埋入圓形窖穴,是“祭祀人格化神或‘地母’等自然崇拜”。這種將人埋入圓形窖穴(廢棄后被稱之為灰坑)的現象,由于無法直接知道其確切意義,故推測灰坑中的頭骨有可能是祭祀類遺存,也有可能是作為垃圾而被丟入灰坑中的。
從民族學材料看,對我們了解這種葬俗有或許一些啟示。云南出土的青銅貯貝器上有殺人祭祀場面,有手持人頭或籃中盛放人頭的造型,這種祭祀是為了祈禱谷物豐收。佤族直到解放前還流行獵頭習俗,用獵獲的人頭來祭祀主宰萬物的神靈“木依吉”[20]。“我國古代生活在云南境內的‘滇族’,每年都要舉行隆重的祖先顱崇拜儀式,目的是為了請求祖先的神靈恢復土地的孕育力”。在云南佤族的獵頭習俗中,人頭的來源有四種,其中一種就是所謂的鬼頭,即掘墓所砍的頭[22]。同時民族學調查發現,佤族信奉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他們最崇拜的鬼神是“木依吉”,他們認為木依吉是創造萬物的神靈,掌管刮風、下雨、打雷,甚至谷子長得好壞、人的生死都歸他管,他們的砍人頭祭谷等較大的宗教活動,都是按照所謂的木依吉的指示和為了祭祀木依吉而舉行的。每個村寨附近都有一個“鬼林”(或稱“神林”)是存放供過的人頭的地方。他們認為只有人頭祭谷,谷子才能長得好,村寨才安全。每年獵頭祭谷的時間,一是在春播前后,一是在秋收之前,其他時間有機會也可以獵頭,獵取人頭后,便開始隆重的宗教儀式,進行祭祀活動。每當播種和收割季節,獵頭活動就特別頻繁。《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南州異物志》載:烏滸人“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貪得之,以祭田神也。”《明史•外國傳•雞籠》載:“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谷種落地則止殺,謂行好事,助天公乞飯食。既收獲即標竹竿于道,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通過民族學資料,可知獵首的習俗更多是為了獵首慶豐收。現在從考古發現看,獵首來的頭骨大多是作為墓主的隨葬品置于墓中。這些頭骨是專門為了陪葬而獵取的,還是如民族學材料那樣是為了豐谷祭祀而獵取的,在這一功能完成后,才作為陪葬品出現在墓內的,由于中間過程的無從考察,而難以確實。考古學材料和民族學材料對缺首葬這一葬俗有著各自的詮釋,反映出兩門學科有著各自的特色和所長。由此,我們不得不意識到作為通過考察古代遺存遺物來復原古代社會的考古學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只有考古材料與民族學材料相結合、相佐證才能合理地理解缺首葬這種現象。其他考古學現象亦然。
作者:王倩倩 單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