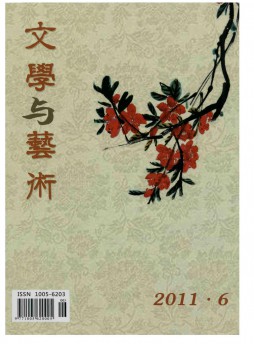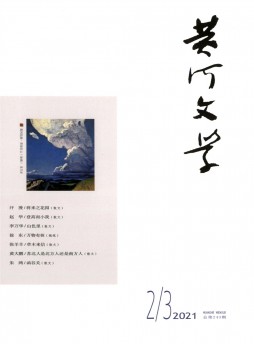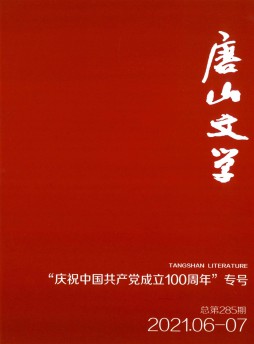文學場中的《小說選刊》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場中的《小說選刊》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在他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中提出了“場”的概念,并主張用場域分析的方法研究文學領域。根據布迪厄的理論,所謂“場”就是一個“可以被定義為由不同的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構成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造”[1]。“文學場”就是一個遵循文學自身的運行和變化規律的空間。布迪厄強調,“文學場”并不是一個自我獨立、封閉的體系,而是與政治場、經濟場等共同處于一個更大的“權力場”之中。“權力場是行動者與機構之間的力量關系空間”,這些場域以及場域內部各成員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獨立靜止的;相反,它們處在一個此消彼長的動態網絡中。“文學(等)場本身在權力場內部占據了一個被統治的位置”,經常受到來自“政治場”和“經濟場”的擠壓。這種“擠壓”,不是通過外部發生,而是通過一種“折射”的方式來影響“文學場”的內部法則,即文學的“自主原則”。文學的自主原則是“文學場”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要素,它是建立在一種“顛倒的”經濟原則———“輸者為贏”的基礎之上的一種類似于“為藝術而藝術”的理想化追求。
這種“擠壓”具體反映到文學上,便表現為代表著“政治場”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審美原則”或代表著“經濟場”的以大眾審美趣味為主導的“市場原則”試圖以自己的標準取代文學的審美原則,重新建立起“文學場”等級秩序的過程。《小說選刊》作為中國作協主辦的刊物之一,兼具大眾傳播媒介、官方意識形態載體和純文學期刊定位的三種文化身份。自1980年創刊以來,它便一直以積極的態度在文學傳播、文學評價和生產引導方面有力地參與著當代文學的發展進程,是當代文學場域中的一個重要“占位”,也是管窺當代文學場的一個重要窗口。事實上,中國當代的“文學場”一直處在與“經濟場”和“政治場”博弈的過程之中。20世紀80年代初期,剛剛擺脫了“工具論”的文學在經歷了“傷痕”“反思”之后開始向文學自我回歸,先鋒小說興起。《小說選刊》也經歷了一個由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依附到漸具開放性、包容性、多樣性的過程。1989年,《小說選刊》停刊,直到1995年才復刊。此時的《小說選刊》面對的是已經翻天覆地的文學環境和廣泛流失的讀者群。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開始加速推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新中國成立以后形成的文學體制產生了強烈的沖擊。文化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而逐漸邊緣化,文學傳媒的生存環境也出現了重大轉變。元氣大傷的《小說選刊》由于1990~1995年這一發展進程的斷裂,相比于其他的文學期刊,似乎錯過了轉型的最佳醞釀期與適應期。1995年,《小說選刊》開始自負盈虧。2005年,《小說選刊》的發行量陷入谷底,臨近破產邊緣。在這樣的背景下,2006年,《小說選刊》大刀闊斧的改版以及對“底層文學”的推動,便具有了尤為重要的意義;同時,“文學場”的觀察視域,也為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觀察的角度與解釋的可能。
二、底層文學:經濟場與政治場的合流
“底層文學”是新世紀初興起于文壇的一股小說創作潮流,主要以城市貧民、農民工,以及其他一些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為寫作對象,反映了他們在貧富分化和社會分層的嚴酷現實中的生存狀態,通常蘊含著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以及人道主義關懷。事實上,至今為止,“底層文學”仍是一個頗為可疑而尚無定論的提法,很大程度上,“底層”只是對當下中國正在形成的一個龐大的無名階層命名的權宜之計,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當下中國的‘底層文學’難以被當作具有相應的藝術成規和美學范疇的文學來討論,人們面對著的,其實是被‘底層文學’所指認、討論者感同身受的社會思想狀況。”[3]大約從2004年開始,文學期刊普遍表現出向底層敘事傾斜的趨勢,特別是《小說選刊》,更是以大刀闊斧的改版方式參與到“底層文學”寫作潮流的倡導與推動之中,尤以2006年和2007年為甚。事實證明,《小說選刊》選擇“底層文學”來作為其改版之后力推的寫作潮流,是經過頗為慎重的考慮的。一方面,“底層”熱的興起與國家話語的誘導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系。2002年3月5日,朱镕基總理在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中首次以官方的名義使用了“弱勢群體”的提法,此后“弱勢群體”的問題便成為“兩會”的焦點話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同時,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也是“底層文學”興起的重要背景。2001年,國家正式將三農問題的提法寫入文件且于2003年正式將其寫入工作報告。“三農問題”自此正式成為理論界和官方決策層引用的術語。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此后又連年1號文件,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這種時間上的巧妙重合昭示了兩者間的必然聯系。事實上,“底層文學”中的一大半,描寫的都是農民———或留守在黃土地上,或掙扎在城市邊緣,或奔波在城鄉之間。在“工業反哺農業”,貧富差距急劇增大的今天,農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底層”的代名詞。因此,《小說選刊》在此時對底層文學的大力提倡,可以說隱含著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有意迎合。
實際上,常常以“國刊”自居的《小說選刊》也毫不避諱自己對主旋律的呼應姿態。副主編馮敏在評論《我們的路》時寫道:“在讀大寶哥這個形象時,我很自然聯想到那些耳熟能詳的關鍵詞:‘三農問題’‘一號文件’‘科學發展觀’‘城鄉協調發展’‘建立和諧社會’等等”[4];小說家徐坤在讀者來信上也直言“改版之后的選刊,順應時勢,在堅持嚴選標準基礎上,貼近當下、替農民和農民工代言的文章多了起來”[5];《小說選刊》改版一周年,主編杜衛東在接受采訪時宣稱:“《小說選刊》去年改版以來所倡導的文學主張,符合總書記對文學界的期待和要求。”[6]另一方面,底層寫作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消費群體。它首先由于其“文壇熱點”的身份成為精英文化圈追捧的“新寵”。同時,底層寫作在歷史上曾經擁有絕對的道義資源,甚至等同于“人民”這一概念。因此,底層文學的描寫對象輕易博取了大眾讀者的同情心,而其創作對現實主義手法的偏愛,也貼合了大眾讀者的審美趣味。《小說選刊》2006年第2期起開設“說話”欄目,從刊登的讀者來信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那青年農民工簡單的飯菜讓我一震,而他臉上那無邪的、燦爛的笑,更令我震驚,那一剎那,我既想哭,又想笑……”(2006年第3期)“現實主義的作品仍然是我的最愛。”(2006年第9期)“封面設計貼近我們農村的生活。”(2006年第11期)現實主義的審美規范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問題小說”開始,再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強力打造”,已經內化為讀者深層的閱讀期待。“尤其對于我們這個務實,實踐理性很強的國度,人們對于現實主義的理解和要求,便傾向于對現實社會和現實人生問題的揭示。讀者希望的是文學能尖銳地提出他們所關心的社會問題,以利于他們的思考和行動,他們對于文學思想的要求,對于問題尖銳性的要求,勝過了對于文學藝術形象的要求。”[7]因此,《小說選刊》對“底層文學”的大力推廣,可以說正好順應了大眾的審美規范。
由此可見,“底層文學”同時滿足了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讀者的審美要求。經過兩年對“底層敘事”的大力倡導,《小說選刊》在全國文學期刊征訂數總體下滑的大背景下,卻在定價上漲的情況下征訂數不降反增,成功實現了對市場的突圍。可以說,《小說選刊》正是充分利用了代表“政治場”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審美原則和代表“經濟場”的以大眾審美趣味為主導的“市場原則”在“底層文學”上“合流”這一特點,才取得了2006年改版的巨大成功。但是,我們也絕不能將《小說選刊》此舉看成是“文學場”中“文學審美原則”對“政治場”和“經濟場”審美原則的全面投降。政治正確與經濟正確并不代表著文學上的注定失敗,有時或許僅僅只是一個權宜之計。事實上,我們也的確看到了《小說選刊》在“利用”“底層”這個概念時,對底層敘事中出現的病象進行努力糾偏,試圖維護“文學場”的審美自主原則,并建立起自己的審美領導權的過程。
三、審美領導權:文學場的自救
“審美領導權”一詞是借用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來說明審美原則上的傾向。在葛蘭西那里,“文化領導權”描述了統治階級不訴諸暴力或強制便能使從屬階級的意識得以構造的過程。具體來說,文化領導權的獲取是以市民社會廣大民眾“自愿的”同意為前提的,并且是以不斷獲取從屬階級的“同意”,進而達成統治階級世界觀指導下的“集體意志”為旨歸的。他對于意識形態斗爭方式的思考給予我們很多的啟發。《小說選刊》自創刊以來,無論是在封面還是在言語之間,一直都有意或無意地強調自己“中國作家協會主管”的官方身份以及在文壇的權威地位,宣稱自己“所選的作品代表了當下中國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和最新成果,全面反映中國小說創作面貌。歷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十有八九都被《小說選刊》選載過,是當代中國影響力最大,最具權威性并擁有廣泛讀者的文學月刊,素有‘文壇風向標’和‘文學濃縮本’之譽,被稱為‘小說國刊’”[8]。同時,它還通過一系列的實際行動來樹立自己的“大刊”姿態,以“整個社會了解和瞭望‘文學’的窗口”自居。例如,每一期開設“全國報刊小說概覽”,給讀者造成“一刊在手,天下我有”的感覺;在年尾的時候不惜騰出多個版面為兄弟報刊刊發征訂廣告,表現出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級大刊應有的氣度和魄力;當社會上發生重大事件時,《小說選刊》也總是積極響應,熱心公益,并號召組織作家進行捐款,以打造自己文壇代表者的形象。《小說選刊》長期以來這樣不遺余力地對自己的宣傳也的確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很多讀者“總在心中給它定位,認為既然是中國作協主辦的,當然應該是同類期刊中最權威的,最好看的”[9]。在以一系列的言行直接標榜自己的權威地位的基礎之上,《小說選刊》還通過對讀者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來建立自己的審美領導權。具體表現在對“底層文學”潮流的推動和引導中,《小說選刊》對“底層文學”進行引導并試圖糾偏的努力。嚴格地說,“底層文學”體現了創作主體對現實生活的密切跟蹤,對弱勢群體的體恤和關懷,尤其是對轉型后的中國社會結構形態及其精神走向給予了自覺的思考。但是,伴隨著“底層無法被真正表述”的焦慮以及大部分作家對底層經驗實際的疏遠與陌生,底層寫作從其創作實績來看,一直“呈現出含混的龐雜和徘徊局面”[10]。特別是2004年以來,隨著“底層寫作”日益成為文壇批評界與創作界追逐的“熱點”,“底層寫作”漸漸由一種“關懷”變為一種“賣點”,并隨之出現了許多病象。《小說選刊》在2006年改版以后就專門設置了“聲音”欄目以“對小說創作中的問題和病象進行善意的,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對小說中帶有普遍意義的傾向和思潮做前瞻性引領”[11]。兩年間,《小說選刊》利用“聲音”欄目,刊發了將近10篇有關底層文學的評論,如邵燕君的《底層如何文學》、李建軍的《重新理解現實主義》、陳福民的《講述“底層文學”需要新語法》、李云雷的《“底層敘事”前進的方向》、賀紹俊的《底層文學的社會性與文學性》、林希的《草根寫作是文學創作的主流》和《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魯太光的《我們為什么寫不好農民》等。這些評論,針對底層寫作出現的將底層妖魔化、苦難化、模式化的傾向以及普遍存在的文學性缺乏等弊病均進行了批評和引導。
除了借批評家之口來表達刊物的導向意圖之外,《小說選刊》還往往直接發聲,甚至為底層敘事開出了“苦難+希望”的藥方,要求“關注生活中的苦難與罪惡,同時又主張在罪惡面前亮出正義的利劍,在苦難旁邊點燃希望的篝火。”[6]除了每一期位于卷首語位置的“閱讀與闡釋”對重點作品的導讀外,選刊還于2006年第3期開始為每一篇沒有配專文評論的小說撰寫“責編稿簽”,以寥寥百余字言簡意賅地對讀者進行閱讀提示。不難設想,每當讀者打開書頁或翻開小說,首先瀏覽到的是置于開頭部分的“閱讀闡釋”或“責編稿簽”,無形之中已經為讀者對小說的理解定下了基調。例如在2006年第3期的“閱讀與闡釋”中,提到敘述人販子靠弄殘兒童以其乞討斂財的《壞爸爸》時,編者認為這篇小說盡管“鋪展了可怕的殘暴與苦難”,但“好在警察來了,好在很多人都在問這是誰的孩子?可以給一個回答:這是‘我們’的孩子,我們能無動于衷嗎?”又如同年第6期在提到馬秋芬的《螞蟻上樹》時,編者直言:“馬秋芬并非一味描寫苦難,底層生活也有自己的形態,一分鐘快樂都沒有的底層生活是不存在的”,直接表明了對此類飽含溫情的作品的肯定與偏愛。又如藍石的《好日子》配以的“責編稿簽”有言:“這篇小說在塑造底層人物時,有別于眾多苦大仇深的面孔。”“下崗工人高健被引車賣漿者流視為窩囊廢,可謂是底層的底層了,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卻整天一副沒心沒肺,樂天派面孔。”津子圍《稻草》的責編評價:“清明已不再善良清明,初月卻依然初守如夢———善比惡更有力量。”諸如此類的評述可謂比比皆是。由于這些欄目長期堅持開設,它們已經逐漸“內化”為了《小說選刊》內容的一部分。此外,《小說選刊》還通過內容編排上對“淚水”與“笑臉”的有意識平衡,封面內容選擇上對希望與溫情的側重甚至直接向作家約稿的方式,來全面滲透和傳遞自己的導向意識。
在葛蘭西看來,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獲得,實際上就是知識分子,特別是無產階級“有機的”知識分子用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社會成員進行教育的過程。就教育的形式而言,他反對強制的“灌輸”方式,而是注重將教育與民眾的自覺結合起來。至于教育的方式,可以采取“陣地戰”的方式,即作文化上的長期滲透與瓦解。《小說選刊》在推廣自己的導向意圖時,采取的即是這樣一種溫和的“教育”方式。那一篇篇有意識選擇的小說與評論,以及“閱讀與闡釋”“責編稿簽”,實際上就是其宣傳思想的一個個“陣地”,在“細無聲”的“潤物”過程中,將自己的價值導向傳遞給了讀者,從而樹立起自己的審美領導權。而廣大讀者(包括許多的小說創作者)也在這種潛移默化的“教育”過程中逐漸接受《小說選刊》的價值導向,甚至將其轉化成自己的審美無意識。例如2006年第8期刊登的一篇讀者來信,該讀者就直接宣稱,盡管《我們的路》《壞爸爸》之類的作品能夠讓人潸然淚下,但若“能選些催人奮發向上的社會感、責任感強烈的激勵人生的小說就更可口了”!在文化領導權獲取的問題上,葛蘭西謹慎地提出要考慮從屬階級的利益,他認為:“毫無疑問,領導權成為事實的前提,就是需要估計將被施加領導權的那些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就是需要通過妥協形成某種平衡。換言之,就是需要領導集團做出某些犧牲。”[12]這種“做出犧牲”,實際上是一種“迂回”的作戰方式。從屬階級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很容易對統治階級的統治持贊賞態度。《小說選刊》自2006年開始,在為讀者做出“犧牲”方面可謂不遺余力:2006年,選刊開始向西南邊防哨所的戰士定期贈送刊物并且推出了“零風險”訂閱,承諾只要讀者對刊物的內在品質不滿意,年末憑郵局的原始訂單和保存完好的12期刊物,就可無條件退款;2007年,《小說選刊》還推出有獎征訂,并隨刊附贈精美的藏書票和年歷,第9、10、11期,為彌補為兄弟刊物發征訂廣告而損失的版面,還貼心地向讀者贈送微型小說讀本,并以充滿感情的口吻告白:盡管“僅此增加的成本已超過20萬元。但取之于讀者,用之于讀者,把錢花在大家的身上我們高興并頗感欣慰”[13]。這一系列的舉動自然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在這種情意濃濃的氛圍中,選刊的價值導向意圖也自然而然地為讀者更好地接受。
綜上所言,《小說選刊》2006年以來對“底層文學”的推舉,不僅是利用“經濟場”與“政治場”的審美趣味在“底層文學”上的重合,實現市場突圍的過程,也是借助底層敘事的新銳勢頭,來確立刊物引領現實主義風潮的權威地位并試圖重新建立起“文學場”的審美領導權的過程。盡管它在扶持、推動底層文學方面有種種不足,但其貼近時代、貼近人民的姿態以及對現實主義的重新呼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凌空高蹈的文學創作重新回到大地,糾正了寫作和審美中出現的病象;同時,也客觀上為文學增加了受眾,顯著地擴大了文學的社會影響。正如一位作者所說,“對走向滑坡的當代文學注入了一針強心劑,這恐怕才是改版的最大意義。”[14]由此可見,《小說選刊》借助“底層敘事”對“經濟場”與“政治場”的“妥協”,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學場”的自救。
但是,我們必須警惕的是,《小說選刊》重新祭起現實主義的大旗,將現實觀照的目光投向為人們所遺忘的底層固然不錯,但它為“底層敘事”開出一味強調溫情與善良的“苦難+希望”的藥方,在矯枉過正的同時,是否陷入了另外一種偽現實主義的困境?另外,自2006年改版以來,《小說選刊》便將“通達好讀,故事性強”作為一條重要的選稿標準,那么,“通達好讀”的“底層故事”是否也暗示著對底層的一種隱性的消費?這些都是《小說選刊》在為一路攀升的訂閱率欣喜不已的同時,需要深思的問題。
作者:趙婷婷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