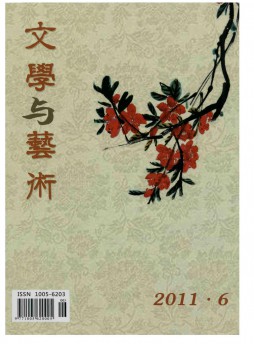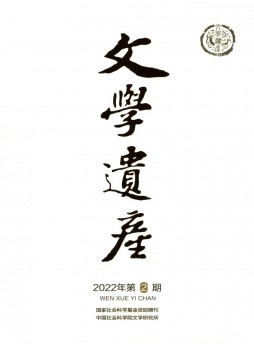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的新拓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的新拓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張以寧論》該書總體架構(gòu)頗為宏大,而論述相當(dāng)精細(xì),追求廣度與深度的統(tǒng)一,重視文本細(xì)讀,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兩種研究方法結(jié)合起來,試圖對張以寧所處的環(huán)境、生平、思想、人格、詩文創(chuàng)作,其與閩文化的關(guān)系等話題作比較全面、深入的探討,注意將原創(chuàng)性置于首位,重視理論性、學(xué)術(shù)性、資料性的某種平衡。該書對于張以寧研究、閩都文學(xué)研究、閩文化研究、元明之際詩文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jià)值。
關(guān)鍵詞:張以寧研究;原創(chuàng)性;學(xué)術(shù)轉(zhuǎn)型
一
《張以寧論》2017年8月由海峽書局出版,該書是福建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游友基繼2012年、2016年分別整理、出版張以寧《翠屏集》簡體橫排版(鷺江出版社)、繁體豎排修訂版(廣陵書社)之后,張以寧研究的又一成果。如果把一本著作比作一座樓房的話,那么,《張以寧論》的總體架構(gòu)則頗為宏大。全書12章,第一章闡述元代社會(huì)的特點(diǎn),勾勒張以寧生存的時(shí)空狀態(tài)及文化語境,從歷史性、時(shí)代性的高度把握住張以寧其人其文。第二章略述張以寧生平與創(chuàng)作道路,先述其家世淵源,后分求學(xué)仕進(jìn)、滯淮十年、居燕廿載、入明三秋四個(gè)時(shí)期,評述其詩文創(chuàng)作。第三章為張以寧的交游錄,共敘述他與近50位文壇各界人士的交往情況,包括與師生、同年進(jìn)士、詩友、同僚、釋道、安南及其他友人,尤著重于其詩文交往,既交代了張以寧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又簡要評述了當(dāng)時(shí)有一定影響的人士的思想、詩文概貌。第四、五章論述張以寧的經(jīng)學(xué)思想、文學(xué)觀。第六章介紹張以寧的人格特點(diǎn)。至此,可視為總論。第七至十一章可視為分論。由于張以寧庚辰歸鄉(xiāng)之旅與入明后出使安南之行,保存的詩較多,較集中,所以,各辟專章闡述。張以寧思鄉(xiāng)詩、題畫詩十分出色,故亦各辟專章論之。對張以寧的散文,該書亦有專章論之。可見,張以寧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該書的重點(diǎn)。第十二章探討張以寧對閩都文化、閩北文化的接受與傳承,把張以寧研究置于他與閩文化的關(guān)系這一理論維度來結(jié)束全書。如此安排結(jié)構(gòu),頗具匠心。當(dāng)我們走進(jìn)這座樓房,發(fā)現(xiàn)它外部的裝飾,內(nèi)部每一個(gè)房間的布置、擺設(shè)都相當(dāng)精致。書中所引用的詩雖只用來說明某一觀點(diǎn),但并不簡單輕易帶過,而予以精煉且生動(dòng)的分析。
一些重要篇章,其闡述則深入透辟,如對早期詩作《奉上御芝隱公》,滯淮時(shí)期《峨眉亭》《舒嘯軒》,庚辰南歸吟詠徐州、蘇杭、武夷等系列的懷古詩,簡直達(dá)到精雕細(xì)刻的地步。對張以寧各階段的創(chuàng)作雖云“略述”,卻分門別類進(jìn)行剖析,并不含糊粗疏,如滯淮十年時(shí)期的詩歌,按寫景詩、贈(zèng)答詩、懷古詩、題詠詩、感懷詩展開論述,洋洋灑灑近萬言。對張以寧的生平一般簡略概述,但關(guān)鍵處也不吝筆墨,如敘張以寧求學(xué)仕進(jìn)時(shí)期的生平,對張以寧老師、老師的老師,下了一番考證的功夫,令人信服地得出張以寧是朱熹五傳弟子的結(jié)論。因此,此書給人以既頗為宏大又相當(dāng)精細(xì)的感覺。游友基追求廣度與深度的統(tǒng)一。他認(rèn)為,作家論,應(yīng)顧及全人,盡量做到全面些,使書具有一定的廣度。為此,該書對張以寧的所有詩文,盡量進(jìn)行全覆蓋,并予解讀,而不僅僅擇取其優(yōu)秀作品或代表作予以評論。他又認(rèn)為,一般的學(xué)術(shù)著作不宜只供極少數(shù)專家學(xué)者參閱,它應(yīng)當(dāng)擁有更多的讀者。因此,讓廣大讀者走進(jìn)張以寧的世界,是著者關(guān)注的中心。它試圖對張以寧所處的環(huán)境、生平、思想、人格、詩文創(chuàng)作,其與閩文化的關(guān)系等話題作比較全面、深入的探討,注意將原創(chuàng)性置于首位,重視理論性、學(xué)術(shù)性、資料性的某種平衡,使普通讀者也能讀得懂,讀得下去,起某種導(dǎo)讀的作用。而同時(shí),該書又具有一定的深度,廣度與深度相結(jié)合。很明顯,該書對于張以寧研究、閩都文學(xué)研究、閩文化研究、元明之際詩文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jià)值。
此書重視文本細(xì)讀,一般不旁及關(guān)系不密切的知識,不輕易做理論上的“提升”,即發(fā)一些并不新鮮的議論,顯得比較扎實(shí)。還重視在“爬梳”的基本功上用力氣,如作品歸屬于哪個(gè)時(shí)期,是需要認(rèn)真考據(jù)、甄別的,該書將張以寧的所有作品幾乎都一一納入了其創(chuàng)作的四個(gè)時(shí)期,只有題畫詩難確定寫作年代,不勉強(qiáng)劃分。該書還重視史料的蒐集。關(guān)于張以寧家世,楊榮《張公墓碑》等只提供一世張睦至三世宗景的材料,四世至十三世空缺,二十一世后又空缺。為理清張以寧的家世延續(xù)情況,該書收錄了吳謹(jǐn)《張以寧宗族脈系考略》、張則建《張以寧家鄉(xiāng)———古田舊城東塔》二文要點(diǎn),以填補(bǔ)這方面的空白。還簡要介紹了張宗昌保存的揚(yáng)州《張氏族譜》自一世張以寧至民國初期張氏的流布情況,盡管其與楊榮記載的張以寧子、孫、曾孫的情況完全不同,存在誤以他人之祖為己祖的質(zhì)疑,但該書還是作為珍貴史料予以保留、評述,說明著者對史料搜集何等重視。張以寧詩中屢屢提及同年進(jìn)士,故著者特意搜集了元泰定四年丁卯(1327)的進(jìn)士名單。一般的史學(xué)著作、文學(xué)史著作都將張以寧列入“明代”加以評說。《張以寧論》不依舊例,根據(jù)張以寧在元朝生活六十七年,在明朝僅生活三年的實(shí)際情況,把論述的重點(diǎn)放在元代,這無疑是正確的。由于將張以寧納入元代文化的大格局中進(jìn)行考察,故凸顯了他的時(shí)代特征,如元代將朱子理學(xu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張以寧浸染其中,積極地宣傳朱子理學(xué);又如元代處于各民族大碰撞、大融合時(shí)期,張以寧結(jié)交了薩都剌、唐兀崇喜等少數(shù)民族朋友。張以寧與元代文學(xué)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其創(chuàng)作是元代文學(xué)的組成部分。如他喜寫題畫詩,這是元代詩壇的共同風(fēng)氣,他的題畫詩充分體現(xiàn)了元代題畫詩的共同特征,當(dāng)然,也葆有其獨(dú)特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著者十分注意張以寧在明初詩壇、文壇所起的作用,尤其是梳理了張對閩派詩的影響。
突出原創(chuàng)性是該書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論張以寧的文學(xué)觀,分五節(jié)論述:第一節(jié)詩的本質(zhì);第二節(jié)詩的創(chuàng)作與詩美追求;第三節(jié)散文理論;第四節(jié)當(dāng)代詩文評論;第五節(jié)淵源與影響。系統(tǒng)性相當(dāng)強(qiáng)。論詩的本質(zhì),張以寧從詩與人的心靈、詩與音樂、詩與畫、詩與問學(xué)的關(guān)系等方面闡述了詩是什么,詩的本質(zhì)是什么的問題。關(guān)于詩與外部世界的關(guān)系,張以寧認(rèn)為:一、詩與“世”,世隆則詩道隆;二、詩與地域文化,詩壇的盛況,與地域文化的悠久歷史、文化傳統(tǒng)、地域山川特點(diǎn)等相聯(lián)系。著者指出:張以寧稱不上詩論及散文理論的名家,但他卻是出色的當(dāng)代詩歌、散文的評論家。他的評論切中肯綮。他認(rèn)為,宋濂是師韓最好的當(dāng)代散文家,他贊揚(yáng)宋濂“先生之文,其進(jìn)于韓氏之為乎!”他概括宋濂散文的特征是非常準(zhǔn)確恰當(dāng)?shù)摹K軓淖髌穼?shí)際出發(fā),根據(jù)不同評論對象的不同特點(diǎn),進(jìn)行剖析,予以歸納,指出其長處,因而具有指導(dǎo)創(chuàng)作的意義。包與直與朱伯良的不同特點(diǎn)鮮明突出,也許他們自己未必清醒地意識到,經(jīng)張以寧“昭然若揭”的指點(diǎn),對其今后創(chuàng)作定有裨益。他能沿波溯源,梳理作者詩文創(chuàng)作的師承、學(xué)習(xí)的源流及變?yōu)橐患业臓顩r。黃清老是嚴(yán)羽的嫡傳弟子,于嚴(yán)氏詩法,可謂深得其精髓。這是黃清老取得詩歌成就的重要原因。黃清老學(xué)詩“由李氏而入,變?yōu)橐患摇保@是獲得成功的又一原因,最重要的是黃清老能“蛻出垢氛,融去渣滓,玲瓏瑩徹,縹緲飛動(dòng)”,融會(huì)貫通,達(dá)到“如水之月、鏡之花,如羚羊之掛角,不可以成象見,不可以定跡求”的藝術(shù)境界,而這正是嚴(yán)羽“妙悟”說的真諦所在。經(jīng)張以寧這一梳理,不僅淵源明晰了,黃清老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也凸顯了。張以寧能牢牢把握其批評標(biāo)準(zhǔn)來進(jìn)行評論。
復(fù)古、師古是他最重要的批評標(biāo)準(zhǔn)之一,其評論的目的性十分明確,即繼承傳統(tǒng)、發(fā)揚(yáng)傳統(tǒng)。張以寧對詩歌群體及其代表詩人作品的評論,引人注目。《桐華新稿序》是對泉州詩人選集的評論。這樣的評論有助于這一群體形成詩歌流派,有利于激勵(lì)地域文學(xué)的發(fā)展,從而有益于創(chuàng)作的繁榮。對于詩歌群體中的代表詩人作出恰當(dāng)評論,不僅是扶持該詩人成長的良方,而且是扶持該詩歌群體生成、發(fā)展的重要途徑。張以寧的評論言簡意明,往往一語中的。既擊中要害,又形象生動(dòng),無套話,無虛言,其評論的文風(fēng)值得肯定。上述皆言人之所未言。應(yīng)當(dāng)說,原創(chuàng)性是流貫于全書的,限于篇幅,就不多例舉了。《張以寧論》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兩種研究方法結(jié)合起來。傳統(tǒng)詩評講究立意、意象、境界等,該書亦靈活運(yùn)用這些傳統(tǒng)方法對張以寧詩展開評述;又注意與現(xiàn)代批評方法相結(jié)合,故能寫出新意。如他用現(xiàn)代詩歌“張力”說分析《嚴(yán)州大浪灘》。詩云:“東來亂石如山高,長江斗瀉湍聲豪。蛟鼉奔走亡其曹,青天白雪揚(yáng)洪濤。舟子撐殺白木篙,長牽百丈嗟爾勞。側(cè)身赤足如猿猱。舟中行子心忉忉,山木巃嵸杜鵑號。”謂:“詩中的意象充滿了‘力’,意象之間處于沖突狀態(tài),具有緊張的‘張力’,展現(xiàn)了舟子與險(xiǎn)灘惡浪搏斗的壯闊畫面,而且這畫面在不斷變動(dòng)中,富有動(dòng)態(tài)感。畫面還伴隨著巨大的聲響,長江洪濤斗瀉的湍聲轟鳴,舟子的吆喝吶喊,岸邊不絕的杜鵑啼聲,匯成了多聲部的交響樂。聲畫疊加,氣勢雄渾,產(chǎn)生了宛若當(dāng)今電影紀(jì)錄片的藝術(shù)效果。”他在闡述張以寧庚辰南歸詩時(shí)概述張以寧詩歌意象的特點(diǎn)曰:“張以寧每首詩都由幾個(gè)意象構(gòu)成,這些意象共同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完整的形象,意象與形象,以及流貫于其中的情感、情緒,共同釀造出某種特定的意境。這是一首詩的創(chuàng)作過程。從總體看,相同、相近、相似的意象,形成了某一意象系列,這些意象系列共同造就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形成了總體的意境。張以寧庚辰南歸的詩由自然風(fēng)光意象系列、思鄉(xiāng)念親意象系列、父子情深意象系列、懷古慨今意象系列等構(gòu)成。”從意象系列的維度來論詩,這是采用了現(xiàn)代的詩歌批評方法。
著者與張以寧相隔八百余年,但畢竟有“同鄉(xiāng)之誼”,著者是懷著崇敬的心情來研究張以寧的。他相當(dāng)全面、深入地發(fā)掘了張以寧思想、人格、詩文中所包含的積極、正面的意義,釋放出正能量,以供今人之借鑒。但作為研究者不能帶有主觀情感,他沒有困于“情”,而是冷靜、客觀地對張以寧作出公允、準(zhǔn)確的定位與評價(jià),顯示出治史所必需的歷史辯證論素養(yǎng)。他肯定張以寧對女性命運(yùn)的同情態(tài)度,又批評其對守節(jié)的苛刻要求;他贊頌張以寧人格的高尚、廉潔,又認(rèn)為:張以寧“奉行中庸之道,修煉所至,性情平和,偶見拘謹(jǐn),而大膽敢為稍遜,此是其長處,亦是其短處。其人格未臻完美。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也。”他高度評價(jià)張以寧的文學(xué)成就,又指出其局限:“翻檢其一生詩文,亦有憾焉。其詩,題贈(zèng)偏多,有時(shí)未免‘客套’,喜化用古人詩句,難避似曾相識之感;其文以論取勝,記敘、抒情稍欠豐贍。”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附錄”收錄了張以寧《春秋春王正月考》整理本,這是游友基以“四庫全書”本為底本整理的簡體橫排本,這樣,張以寧的兩部著作都有了整理本,這給讀者閱讀、研究張以寧提供了便利。
二
據(jù)我所知,游友基的學(xué)術(shù)跋涉之路可分為退休前、退休后兩個(gè)時(shí)期。退休前他從事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與新詩、現(xiàn)代小說的研究,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曾在上海《學(xué)術(shù)月刊》發(fā)表《試論艾青“詩的散文美”的美學(xué)主張及其創(chuàng)作實(shí)踐》,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發(fā)表《女性文學(xué)的嬗變與發(fā)展》等論文,著述并出版《中國現(xiàn)代詩潮與詩派》(1993年)、《中國現(xiàn)代女性文學(xué)審美論》(1995年)《九葉詩派研究》(1997年)、《中國社會(huì)小說通史》(1999年)。當(dāng)時(shí),出現(xiàn)女性文學(xué)研究熱、九葉詩派研究熱,可見,他是跟著學(xué)術(shù)主流走的,參與熱門話題的研究的。但他有點(diǎn)“雜”,亦涉足中國古典文學(xué)的研究,如在《中國古代文學(xué)理論研究叢刊》上發(fā)表《略論李漁戲劇美學(xué)思想的特點(diǎn)》,寫了專著《馮夢龍論》,他認(rèn)同中國文學(xué)從古到今是個(gè)整體的觀念,寫《中國社會(huì)小說通史》,全書50萬字,古代部分約15萬字。退休后,有了更多的學(xué)術(shù)自由,不必再跟學(xué)術(shù)主流走了。經(jīng)過觀察、分析,他覺得地域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起步較慢,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大有可為,于是,選擇了閩都文學(xué)與文化作為研究方向,實(shí)現(xiàn)了學(xué)術(shù)轉(zhuǎn)型。在文學(xué)與文化研究中,確定以文學(xué)研究為重點(diǎn),在文學(xué)研究中,又確定了兩個(gè)研究重點(diǎn):林紓、張以寧。林紓研究,不研究“林譯小說”,而著重研究其創(chuàng)作(含詩歌、筆記、小說、傳奇等),幾年來,寫了約20篇林紓研究的文章。張以寧研究,整理了其詩文集《翠屏集》簡體橫排本(2012),繁體豎排本修訂版(2016),出版了研究專著《張以寧論》(2017)。此外,2013年,還出版了《守望與展望———中國文學(xué)與閩籍作家論集》《閩都文學(xué)與文化漫論》。退休前的研究領(lǐng)域也沒有完全退出,只是大大縮小了陣地,只集中研究艾青,每年至少寫一篇論文,參加全國性的艾青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議;繼續(xù)研究九葉詩人。這樣,有重點(diǎn),才能“力所能及”,才能“老有所為”。實(shí)現(xiàn)學(xué)術(shù)轉(zhuǎn)型,有幾個(gè)問題要解決:第一,要重新學(xué)習(xí)。閩都文學(xué)與文化的輝煌時(shí)期在近代,這一階段,他原先并不熟悉,需重新學(xué)習(xí),由于退休前他已有古代文學(xué)研究的經(jīng)歷,所以重新學(xué)習(xí)并不困難,但受時(shí)間和精力限制,不能全面學(xué)習(xí),只能主要學(xué)習(xí)與所寫論著有關(guān)的文學(xué)與文化知識。第二,要找到別人沒研究或少研究的、自己能駕馭的話題,他選擇了上文所述的林紓創(chuàng)作(而非林譯小說)研究、張以寧研究。《閩都文學(xué)與文化漫論》共有閩都文化特質(zhì)論、閩都文學(xué)論、福州船政文化論、閩都信俗文化論四個(gè)專題。
它以近現(xiàn)代福州籍文化名人推進(jìn)文化思想現(xiàn)代化為例,探討閩都文化勤于學(xué)習(xí)、善于發(fā)現(xiàn),勇于探索、敢為人先,與時(shí)俱進(jìn)、保持先進(jìn),海納百川、無欲則剛等特質(zhì),從而豐富了閩都文化特質(zhì)的內(nèi)涵。閩都文學(xué)論是全書的重點(diǎn),從十邑名家、詩文解讀,吉光羽片、文壇掠影,先賢過境、齒痕處處等視角剖析閩都文學(xué)的獨(dú)特之處,如在“林紓作品新解”中提出《閩中新樂府》是近世最早的白話詩集,《技擊余聞》是閩海武林寫真,《合浦珠傳奇》悉心打造了福州儒商的形象等觀點(diǎn);認(rèn)為現(xiàn)代福州有四大才女,除冰心、廬隱、林徽因外,還應(yīng)補(bǔ)上程俊英,她是廬隱的同學(xué)、好友,把一生獻(xiàn)給文學(xué)教育與研究,是我國第一代的女教授,對故鄉(xiāng)充滿感情,曾詠嘆道:福州,兒時(shí)的故鄉(xiāng),“是我一直憧憬的故鄉(xiāng)”!這些都顯得十分新鮮。它概述了戚繼光入閩平倭的詩文、徐霞客五次入閩之游、郁達(dá)夫在福州的游記和演講等,均可增加讀者的知識,開闊其視野。福州船政文化論從福建海洋文化與福州船政文化的關(guān)系入手,論述福州船政文化是中原文化與海洋文化相融會(huì)的產(chǎn)物,福州船政文化具有獨(dú)特的文化品格,船政文化的主要精神是兼容并包、開拓進(jìn)取、人才為本、務(wù)實(shí)求精、自強(qiáng)愛國等,陳寶楨具有先進(jìn)文化思想,首屆畢業(yè)生嚴(yán)復(fù)占據(jù)了船政文化的理論高峰。閩都信俗文化論專題思考陳靖姑文化的多重內(nèi)涵及其意義,探索圓瑛對中國現(xiàn)代佛教的貢獻(xiàn),指出學(xué)界褒太虛貶圓瑛,是誤認(rèn)為圓瑛保守而太虛主張宗教改革,實(shí)際上,圓瑛與太虛佛教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只不過太虛激進(jìn),圓瑛務(wù)實(shí),兩人曾志同道合,兄弟情深,后因中國佛教會(huì)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問題產(chǎn)生矛盾,但友誼尚存,應(yīng)全面、正確評估圓瑛在中國近現(xiàn)代佛教史上的地位與作用。這些論述都給人以啟示,有利于學(xué)術(shù)上的探求與討論。《守望與展望———中國文學(xué)與閩籍作家論集》是作者多年來的論文選集,共五輯:一、文學(xué)動(dòng)向;二、新詩創(chuàng)作;三、小說天地;四、戲曲理論;五、閩籍作家。其第五輯有三篇論林紓的創(chuàng)作,論其舊體詩真樸寓性情,具有拳拳報(bào)國心,表現(xiàn)了同鄉(xiāng)情誼之深;《<劍腥錄>新論》認(rèn)為林紓塑造了一個(gè)正直、執(zhí)著的近代知識分子形象,開啟了表現(xiàn)重大歷史變革時(shí)期知識分子人生境遇及心路歷程的小說的先河,作品表現(xiàn)出從古典型向現(xiàn)代型轉(zhuǎn)化的特色,具有長篇小說藝術(shù)的某種現(xiàn)代性;介紹了林紓、陳衍的赴臺經(jīng)歷及創(chuàng)作。第五輯有二篇是專論鄭振鐸小說的,探討其對中國小說現(xiàn)代化的貢獻(xiàn)和獨(dú)特價(jià)值,這五篇論文于無人問津處辟出一片天地,論題新穎,論述透辟,言之成理,對于閩都文學(xué)研究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作者:張忠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