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水湖岸植被的分類排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退水湖岸植被的分類排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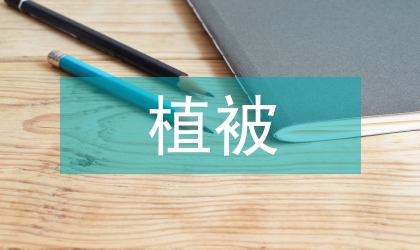
《浙江農業學報》2015年第十期
摘要:
1998—2012年,呼倫湖經歷了連續15年的退水,在南岸形成了一個5km×3km的矩形退水湖岸。于2012年8月中旬對退水湖岸的植被進行調查,并利用空間代替時間的方法探討15年來樣地植被演替的序列。通過雙向指示種法(TWINSPAN),在5級分類水平上將所調查的70個樣方分為6組,利用去趨勢對應分析(DCA)對樣方排序,得到植被的演替序列為:藜科先鋒群落(演替前期)→蘆葦群落(演替中期)→羊草群落(演替后期)。比較各演替階段物種多樣性及組成發現:演替后期物種豐富度、均勻度和多樣性明顯高于演替前期和中期;物種均勻性則表現為演替中期明顯低于演替前期及后期;隨演替進展,多年生植物在群落中比例逐漸增加。
關鍵詞:
空間代替時間;TWINSPAN;DCA;植被演替;呼倫湖
呼倫湖(又名達賚湖),是內蒙古最大的內陸湖,從1998至2012年連續經歷15年退水。研究表明,僅僅2000—2009年,呼倫湖的水位就下降了約4.6m。湖水退卻導致濕地萎縮,湖區生態環境退化。目前對于呼倫湖退水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湖面積、湖水質以及湖岸植被生物量總體的變化[1-3],較少有學者對退水之后新生湖岸植被類型的變化進行觀測和研究,而濕地新生植被的演替序列研究對于了解當地植被的演替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國內外很多研究均是通過對新生濕地演替規律的研究了解研究地演替的動向,繼而對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提出建設性的建議[4-6]。本研究利用空間代替時間的方法,通過TWINSPAN分類[7]和DCA排序[8]研究呼倫湖的退水湖岸植被演替動態,揭示各個演替階段植物種的組成結構和變化,了解退水湖岸植被演替的規律,并結合文獻進行初步分析,以期為呼倫貝爾地區草地的恢復提供理論支持。
1試驗內容與方法
1.1研究區自然地理概況呼倫湖位于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草原西部的新巴爾虎左旗、新巴爾虎右旗(以下簡稱新右旗)和滿洲里市之間。從1998年開始的連續退水導致呼倫湖在南岸新形成了一個東西5km,南北3km的矩形沼澤,位置為48°37'—48°39'N,117°10'—117°14'E,即本試驗所選取的樣地。樣地海拔高度約550m,整個樣地高度差在1m之內。新右旗地處中緯度地區,屬于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冬季嚴寒、漫長、干燥。年平均降水量220~280mm,由北向南遞減。年平均氣溫1.1℃,1月溫度最低,平均氣溫在-21℃左右,夏季短暫、溫涼,7月份溫度最高,平均氣溫21.6℃。日照時間長,年平均日照時數約2800h,無霜期約128d。樣地最西面最早裸露的濕地上的植被為經過多年演替過后的植被,最東面的最新裸露的濕地植被為第1年的植被,自西向東植被類型的更迭為植被演替的各個不同階段。2012年試驗樣地植被自西向東帶狀的變化恰恰驗證了這種假設,使得此地利用空間代替時間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都是可行的。
1.2樣方的選擇和群落調查樣方選取為呼倫湖南岸多年退水形成的矩形地帶,樣地大小約為3km×5km,選取樣方的方法如圖1所示,東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相鄰樣地距離均為500m(即1、2號樣地,1、8號樣地之間距離均為500m,以此類推)。預試驗發現此地均為草本植物,設置樣方大小為1m×1m,樣方總數為70個。每個樣方記錄種類組成,種蓋度、多度、高度、經緯度和海拔高度。
1.3數據分析通過Patrick豐富度指數(Pa)、Simpson多樣性指數(D)、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H)、Pielou均勻度指數(E)來說明研究區的植物多樣性。重要值作為測定物種多樣性的指標,用于草本植物較方便和適用。Ni=(相對密度+相對蓋度+相對頻度)/3樣地分類采用雙向指示種法(two-wayindica-torspeciesanalysis,TWINSPAN)[7],排序用去趨勢對應分析(detrendedcorrespondenceanalysis,DCA)[8]。TWINSPAN和DCA分別在PC-ORD和CANOCO5.0軟件平臺上完成。
2結果與分析
2.1樣方的TWINSPAN分類將70個樣地進行TWINSPAN分類,結果如圖2所示,在D5水平上可以分為6組,分別命名為G1,G2,G3,G4,G5和G6。結合TWINSPAN結果,將樣地分為3個演替階段。分別為:羊草(Leymuschinensis)群落。包含G1和G2。共計8個樣地,G1包含5個樣地,G2包含3個樣地。羊草群落主要伴生種為尖頭葉藜(Che-nopodiumacuminatum)和砂引草(Argusiasibiri-ca),分布于離湖岸的最遠端,是樣地植被演替最終階段的群落。蘆葦(Phragmitesaustralis)群落。包含G3和G4,G3包括18個樣地,G4包括21個樣地。蘆葦群落的主要伴生種為寸草苔(Carexduriuscu-la)。蘆葦群落是樣地植被演替的中級階段。藜科群落包含G5和G6,包含23個樣方,在D3水平上G5和G6被劃分開來。指示種為地膚(Kochiascoparia)、角果堿蓬(Suaedacorniculata)、灰綠藜(Chenopodiumglaucum)。這3種重要植物同屬藜科,經常在濕地之中扮演著先鋒物種的角色,一般為先鋒群落。
2.2樣方的DCA分析對70個樣地進行DCA排序,結果如圖3所示。DCA第一軸提供了大約52%的信息,第二軸提供了16%的信息。藜科先鋒群落,即G5+G6在最右邊,為先鋒物種,蘆葦群落(G3+G4)主要分布在中間,羊草群落(G1+G2)分布于橫坐標最左端。
2.3演替各階段植物種分布本研究在樣地中共發現12科37種植物。利用TWINSPAN將各個樣地分類進行統計,各個群落植物種所在科分布如表1所示。所含植物科的總數表現為:蘆葦群落>羊草群落>藜科先鋒群落。3種群落都是以禾本科、藜科和菊科為主,這3個科植物種類數占各個群落植物種類總數的比例在羊草、蘆葦、藜科先鋒群落中分別為58%,75%和73%。羊草群落中3科植物的種類數大體一致;蘆葦群落中以菊科植物種類最多,占群落植物種類總數的40%;藜科先鋒群落中藜科植物占比最大,占群落植物總種類數的45%。
2.4演替各階段群落的多樣性及生活型變化演替各階段群落的多樣性及生活型的分析如表2所示,據此可知:(1)Patrick豐富度指數(Pa):通過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發現羊草群落Pa顯著(P<0.05)高于蘆葦和藜科先鋒,藜科先鋒和蘆葦Pa無顯著差異(P>0.05)。表明群落演替的前期到中期,物種豐富度變化不明顯,后期的羊草群落與其他群落相比豐富度急劇增加。(2)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H)和Simpson多樣性指數(D)所表示的趨勢相同,羊草群落的H和D顯著(P<0.05)高于蘆葦群落,表明群落演替后期群落多樣性增加。(3)Pielou均勻度指數(E)以蘆葦群落最低,同藜科先鋒差異顯著(P<0.05),同羊草群落差異不顯著(P>0.05)。表明演替前期到演替中期植物種均勻性降低,演替后期恢復。(4)生長型。比較3個種群多年生植物的比例,羊草(68%)>蘆葦(55%)>藜科先鋒(36%)。表明隨著演替的進行,多年生植物在群落組成中比例增加。
3討論
濕地生態系統作為陸地和湖泊兩大生態系統的過渡地帶,在全球物種遷移與演變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9-10]。本文所采用的空間代替時間的方法在國內外有著廣泛的應用[11-12]。傳統的植被演替研究通常需要在同一地點進行連續多年的直接植被觀測[13],這種情況通常比較難以實現,而且演替的研究通常需要樣地盡量保持穩定,少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擾。但在自然狀況下,即使是同樣的位置也很難保持穩定,會不同限度地受到人為因素以及突發的自然因素的干擾而影響研究結果[14]。在本研究中,試驗地位于達賚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極少受到人為活動的干擾,而湖水退卻連續15年無間斷,非常適宜使用空間代替時間的方法來研究當地植被的演替狀況。TWINSPAN是當今數量生態學研究中最主要的分類方法[15],其分類方式比較客觀,個人主觀思維對結果的影響較小[16],與DCA聯用可以很清晰地判別不同的演替階段。DCA和TWINS-PAN聯用結合文獻[17]發現,樣地演替序列為藜科先鋒群落→蘆葦→羊草。此分布模式同實際樣地的演替相同。吳統貴等[9]在杭州灣灘涂對調查的50個樣方進行DCA排序分析,第一排序軸與樣方的空間分布呈顯著的線性相關,與本試驗結果一致,但是文中并未解釋第一軸所對應的環境因子。呼倫湖濕地植被DCA第一軸可能是多個環境因子的作用,而這個環境因子的變化則同演替呈正相關,很可能是水、鹽等的共同影響[10]。第二軸指代了較少的信息量,比較模糊,需要進一步采集各個樣地的土壤水、鹽、溫度和有機質等指標,然后進行典范對應分析(CCA),才能確定哪個因子是主導因子,哪個因子是從屬因子。雖然本研究難以闡釋DCA第一軸的確切含義,但是第一軸明確地反映了群落之間的替代關系和順序,因而達到了研究的目的,結果發現演替趨勢同TWINSPAN圖反映的趨勢一致,因而可以確定演替為藜科先鋒群落→蘆葦→羊草。在演替的初級階段,植被演替起始于零星分布的一年生植物,以藜科植物為主,在藜科先鋒群落所占據的樣方中共發現11種植物,藜科占據了5種,代表植物為堿蓬、地膚、角果堿蓬和灰綠藜。這些一年生C4植物呈斑塊狀分布在由于退水而裸露的濕地上。藜科先鋒群落統治演替前期的可能原因如下:湖水上漲和下降造成植被反復浸入堿性水中,即使短期的浸水也會導致植物的死亡[18],接下來退水又重新裸露植被;而藜科先鋒植物非常適應湖邊高鹽度高濕度的環境,一旦退水,新生的藜科先鋒植物便會重新占據裸露的濕地。一些研究表明,鹽地堿蓬、角果堿蓬等在根系的長度、根的分布以及光合特性(特別是水分利用效率)方面更加適應灘地的環境[19]。藜科植物在演替的早期出現,為后續的演替創造了環境,湖邊高鹽的環境不適宜后續的蘆葦和羊草等群落的生存。有研究表明,地膚、堿蓬、角果堿蓬和灰綠藜具有降低土壤鹽分、改善土質的作用[20]。中期階段的蘆葦和后期階段的羊草群落的繁榮得益于藜科先鋒植物對土壤的改造作用[21]。后期羊草代替蘆葦很可能是由于水分的關系,李永亮等[22]在新疆喀納斯湖北段濕地的研究發現,濕生植物被喜濕中生的植物群落所取代,沿遠離河流方向依次出現草甸化沼澤、沼澤化草甸等植被,原因是土壤水分隨著遠離湖水而降低,濕生植物因此逐漸喪失競爭優勢。呼倫湖濕地植被演替同樣支持這樣的論斷,濕生的蘆葦群落由于遠離湖水而喪失競爭優勢被羊草群落所代替。羊草演替階段的群落Shannon-Wiener指數和Simpson指數均值高于另外兩個階段,表明隨著演替的進行,植物種類豐富性和多樣性增加。范瑋熠等[23]在黃土高原的研究同此結果一致。但這一結果與許多同行的研究結果不同,如Ma等[24]在青藏高原濕地植被演替的研究中發現,隨著演替的進行,多樣性中期增加,后期植物群落趨向于穩定。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使用中度干擾假說來進行解釋,即演替中期的生境經過先鋒植物的改造,趨于適宜,引來眾多其他物種的擴散和競爭。演替末期有幾種優勢種勝出,一些中期演替的植物種被淘汰,所以多樣性下降。呼倫湖植被演替后期多樣性的高低受多方面的影響:呼倫湖樣地發現的植物種遠少于青藏高原樣地植物種數,藜科植物和蘆葦雖然在演替后期不是優勢種,但是也沒有被完全淘汰,演替后期羊草群落的組成是以羊草為主,蘆葦和藜科植物為輔,所以多樣性到演替末期最大。隨著演替的進行,植物群落從一年生植被向多年生植被過渡。這一結果與Parraga-Aguado等[25]和Odland[26]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只是呼倫湖演替最終階段仍為草本植物,Odland[26]的研究中期即已出現多年生灌木,后期則以喬木為主。多年生植物所占比例增加對于群落的穩定具有積極的作用,而且傳統的單元頂級學說也認為一年生植物為多年生植物創造了適合的生境[27]。綜上所述,可得如下結論:空間代替時間的方法在本研究中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利用TWIN-SPAN分類和DCA排序比較客觀地發現,從1998—2013年呼倫湖南岸退水湖岸植被演替共分為3個階段,即藜科先鋒群落→蘆葦→羊草。演替后期植被多樣性、均勻性和豐富度較前期均有所增加;演替前期到演替中期植物種均勻性降低,后期得到恢復;多年生植物在群落中比例遞增。
參考文獻:
[1]趙慧穎,烏力吉,郝文俊.氣候變化對呼倫湖濕地及其周邊地區生態環境演變的影響[J].生態學報,2008,28(3):1064-1071.
[2]楊久春,張樹文.近50年呼倫湖水系草地退化時空過程及成因分析[J].中國草地學報,2009,31(3):13-19.
[3]嚴登華,何巖,鄧偉.呼倫湖流域生態水文過程對水環境系統的影響[J].水土保持通報,2001,21(5):1-5.
[4]Gonzlez-AlcarazMN,ArnegaB,TerceroMC,etal.Irriga-tionwithseawaterasastrategyfortheenvironmentalmanage-mentofabandonedsolarsaltworks:Acase-studyinSESpainbasedonsoil-vegetationrelationships[J].EcologicalEngi-neering,2014,71:677-689.
[5]lvarez-RogelJ,Jiménez-CrcelesFJ,RocaMJ,etal.Chan-gesinsoilsandvegetationinaMediterraneancoastalsaltmarshimpactedbyhumanactivities[J].Estuarine,CoastalandShelfScience,2007,73(3):510-526.
[6]吳統貴.杭州灣濱海濕地植被群落演替及優勢物種生理生態學特征[D].北京: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2009.
[7]HillMO.TWINSPAN-AFORTRANprogramfromarrangingmultivariatedatainanorderedtwowaytablebyclassificationoftheindividualsandattributes[M].HillMO.EcologyandSystematics.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1979.
[8]HillMO.DECORANA-AFORTRANProgramfromdetrendedcorrespondenceanalysisandreciprocalaveraging[M].HillMO.EcologyandSystematics.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1979.
[9]吳統貴,吳明,蕭江華.杭州灣灘涂濕地植被群落演替與物種多樣性動態[J].生態學雜志,2008,27(8):1284-1289.
[10]熊雄,賀強,崔保山.黃河三角洲濕地草本植被的雙變量主坐標排序[J].生態學雜志,2008,27(9):1631-1638.
[11]SunderlinD,TropJM,IdlemanBD,etal.PaleoenvironmentandpaleoecologyofaLatePaleocenehigh-latitudeterrestrialsuccession,ArkoseRidgeFormationatBoxCanyon,southernTalkeetnaMountains,Alaska[J].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2014,401(5):57–80.
[12]劉文治,張全發,李天煜,等.丹江口庫區濕地植被的數量分類和排序[J].武漢植物學研究,2006,24(3):220-224.
[13]CzerepkoJ.Along-termstudyofsuccessionaldynamicsintheforestwetlands[J].ForestEcologyandManagement,2008,255:630-642.
[14]郭月峰,姚云峰,秦富倉,等.敖漢旗小流域不同植被類型區土壤養分狀況分析[J].浙江農業學報,2013,25(5):1062-1067.
[15]李海濤,賀金生,倪志誠,等.西藏拉孜縣草地植物群落的TWINSPAN分類及其物種多樣性研究[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2004,26(1):31-36.
[16]張金屯.植被數量生態學方法[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17]中國植被編輯委員會.中國植被[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18]FraserLH,MulacK,MooreF.Germinationof14freshwaterwetlandplantsasaffectedbyoxygenandlight[J].AquaticBotany,2014,114:29-34.[19]弋良朋,王祖偉.鹽脅迫下3種濱海鹽生植物的根系生長和分布[J].生態學報,2011,31(5):1195-1202.
[20]郗金標,張福鎖,陳陽.鹽生植物根冠區土壤鹽分變化的初步研究[J].應用生態學報,2004,15(1):53-58.
[21]馬超穎,李小六,石洪嶺,等,常見的耐鹽植物及應用[J].北方園藝,2010,(3):191-196.
[22]李永亮,岳明,楊永林.新疆喀納斯湖北端河漫灘濕地植物群落演替[J].生態學雜志,2010,29(8):1519-1525.
[23]范瑋熠,王孝安,郭華.黃土高原子午嶺植物群落演替系列分析[J].生態學報,2006,26(3):706-713.
[24]MaMJ,ZhouXH,MaZ,etal.CompositionofthesoilseedbankandvegetationchangesafterwetlanddryingandsoilsalinizationontheTibetanPlateau[J].EcologicalEngineer-ing,2012,44:18-24.
[25]Parraga-AguadoI,Gonzalez-AlcarazMN,Alvarez-RogelJ,etal.Theimportanceofedaphicnichesandpioneerplantspe-ciessuccessionforthephytomanagementofminetailings[J].EnvironmentalPollution,2014,176:134-143.
[26]OdlandA.PatternsinthesecondarysuccessionofaCarexvesicariaL.wetlandfollowingapermanentdrawdown[J].AquaticBotany,2002,74:233-244.
[27]王陽,王奇贊.種植年限對大棚蔬菜地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多樣性的影響[J].浙江農業學報,2013,25(3):567-576.
作者:馬帥 馮金朝 烏力吉 李昱嫻 馮亞磊 趙慧卿 單位:濰坊工程職業學院 應用化學與生物工程學院 中央民族大學 生命與環境科學學院 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 青州市中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