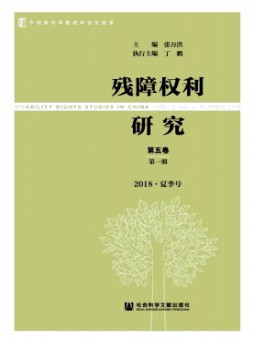墳產權利的限制性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墳產權利的限制性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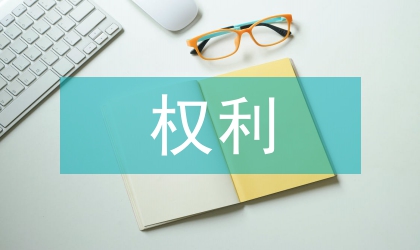
《河南理工大學學報》2015年第六期
摘要:
清代公同共有財產墳產權利,具有區別與西方財產權的獨特屬性。對于墳產權利,中國傳統法律是有限制的,體現在立法中是對墳產各個財產表現形式的限制、體現在司法實踐中是對祖墳再行入葬權利的限制,且此限制與西方法下所有權限制根本不同。西方法強調對權利的利用,中國傳統法律則著重于對權利狀態的持續維護,墳產權利是具備“義務性”的權利。
關鍵詞:
墳產權;民事權利;清代
一、序言
學界認為,公同(共同)共有財產是傳統中國存在的財產形式之一。其中,墳產又是傳統中國公同共有財產的形式之一(墳產是以營葬死者并修建埋葬死者固定場所為目的而設置的財產形式[1])。西方法律體系引入中國后,所有權概念開始在中國流行。關于對墳產權利屬性的認知,有學者直接將其歸入“墓地所有權”[2],實際上這是不嚴謹的。除此之外,學界對于墳產權利的精細研究幾乎為零。關于對所有權觀念的認知,西方法律體系有羅馬法與日耳曼法上的區別。羅馬法中的所有權為完全權利,具有使用、收益、處分等權能,權利為個人享有,不受身份限制。日耳曼法上的所有權觀念可謂系各種利用權之集合,且深具團體與身份色彩,在管理權與處分權上均有相當之限制[3]。對于所有權的屬性,梅仲協指出,完整的所有權包括積極效用(即所有人得自由使用,收益并處分其所有物)和消極效用(排除他人干涉)[4];謝在全認為,所有權者乃于法令限制范圍內,對于所有物永久全面與整體支配之物權[3]。由于墳產的特殊性,自唐至清,國家律例、族譜、合同等都對墳產權利從各方面進行了嚴格限制。
二、立法中對墳產權利的限制
(一)墳山(1)禁止投獻墳山。“子孫將公共祖墳山地,朦朧投獻王府及內外官豪勢要之家,私捏文契典賣者,投獻之人,發邊衛永遠充軍,田地給還應得之人,及各寺觀、墳山地歸同宗親屬各營業。其受投獻家長,并管莊人,參究治罪。”[5]該條例原收錄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刑部尚書白昂等人制定的《問刑條例》中,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問刑條例》沿襲該例,萬歷十三年(1585年)制定的《問刑條例》對上述條例有所修改。清朝規定則與明同[6]。清雍正三年(1725年)、乾隆五年(1740年)對該條例進行了兩次修改。在弘治以及嘉靖時期的《問刑條例》中,沒有“若子孫將公共祖墳山地”“墳山地歸同宗親屬”二句,此為萬歷條例新增,亦為雍正、乾隆時期的修改所沿襲[7]。祖墳山地雖屬于子孫,但法律禁止子孫私自典賣及投獻公共祖墳山地。對于禁止子孫投獻墳山的理由,《唐明律合編(卷十三上)•盜賣田宅》指出:“祖墳山地,非子孫一人可專者,亦猶他人田產也。”[5](2)禁止棄尸賣墳。除了禁止子孫私自典賣與投獻祖墳山地外,子孫棄尸賣墳的行為也是嚴厲禁止的。《大清律例•卷二十五•刑律》記曰:“開棺槨見尸者,斬。監侯。眾棄尸賣墳地者,罪亦如之。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各杖八十,追價入官,地歸同宗親屬。不知者,不坐。”[8]清因襲明律[9]。棄尸賣墳罪與子孫私自典賣祖墳山地罪不同,即使眾子孫均同意棄尸賣墳,也構成本罪。(3)禁止盜葬盜耕。國家對盜耕墓田以及盜葬他人田者的行為都有法律規范。《唐律疏議•卷十三•戶婚》記載,盜耕墓田的,杖一百;傷害到墳墓的,徒一年;盜葬在他人田中的,笞五十[10]。如果盜葬的行為傷害到了他人的墳墓,則與盜耕傷墳者處罰相同。對于盜葬在他人墓田中的,加一等,杖六十,仍令移葬[10]。宋規定與唐相同[11]。明未見有關盜耕傷墳等處罰,但是《大明律•卷十八•刑律》則有規定:于他人有主墳地內盜葬,不令得死,杖八十[9]。清制同明[8]。對于子孫入葬眾存山地的行為,宋《慶元條法事類•卷七十七•服制門》記載:“祖來眾共山地,若眾議不許安葬而盜葬及強者,比之盜葬他人墓田,事體稍輕,即合比附上條(盜葬他人墓田法),各減一等科罪。”[12]《劉氏宗譜•家規》中記曰:“如有不肖私鬻墓地、祭田者,責令贖回,仍以不孝治論。”[13]在墳產合同領域中,申餙護墳合同、禁限護產合同①*都約定了不準盜葬盜賣、保護墳產的事項。例如,“咸豐六年十二月余光紳、光維等保護墳產合同”中,余氏五人共同修造了一大穴,在入葬之前,眾人約定“業內五大房以后不準偷葬及水,如有偷葬侵損砍伐來龍,聽憑宗族理論,將偷葬之墳,五大股相邀實時將骸骨拋毀,無得異言”(咸豐六年十二月余光紳、光維等保護墳產合同。俞江教授藏)。
(二)墳墓(1)墳墓修造步數及高度的限制。國家律令對于墳墓塋地步數以及墳墓高度的限制是從規范與身份的角度入手的,但未有明文規定,只有《唐會要•卷三十八•葬條》記載的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的詔令有對墳墓步數削減的規定,而且還相當嚴格:“墓田一品官塋地先方九十步減至七十步,墳高先一丈八尺減至一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減至六十步,墳高先一丈六尺減至一丈四尺。”依次削減。“其庶人先無步數,請方七步墳四尺。”[14]《唐律疏議•卷二十六•雜律•舍宅車服器物違令條》記曰:“諸營造舍宅車服器物及墳塋石獸之屬,于令有違者杖一百,雖會赦皆令改去之(墳則不改),其物可賣者聽賣,若經赦后百日不改去及不賣者論如律。”[10]薛允升在《讀例存疑•卷十•戶律•田宅》說道:“言墳塋按品建造,不得僭越也。與唐律同。”[15](2)禁止平治墳墓。子孫“并奴仆雇工平治家長墳一塚者,杖一百,徒三年。每一塚加一等,仍照加不至死之例,加至實發云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為止”[15]。因為平治墳墓而獲得了財物的,“均按律計贓,準竊盜論加一等,贓輕者各加平治罪一等”[15]。對于知情謀買的人,“悉與犯人同罪,不知者不坐”[15]。此處對于知情謀買者的處罰與對砍伐盜賣墳樹以及子孫棄尸賣墳中謀買者所作的處罰不相同,如后文將提及的盜賣墳樹中的私買墳樹之人,照盜他人墳園樹木例治罪,杖八十,計贓重加盜一等。而子孫棄尸賣墳中,買地人牙保知情者,則為各杖八十。平治墳墓罪中,知情謀買者與犯人同罪的處罰顯然相較上述二罪要嚴重許多。在族譜中,對墳墓旁行為的限制也很嚴格。如《合肥李氏五修宗譜》中,不僅禁止其他人,也不許親族“謀葬墳塋、起造房屋、牧放牲畜、砍伐樹木、挑塘挖井、挖窖燒窯”等任意作踐的行為[16]。(3)禁止殘害尸體、發掘他人墳墓。《大明律•卷十八•刑律》規定:“諸殘害死尸,謂焚燒、支解之類。及棄尸水中者,杖一百,流三千里。”[9]清規定與明相同。清律規定:“凡發掘他人墳塚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槨見尸者,絞。監侯。”[8]在《讀例存疑•卷三十一•刑律•賊盜》中,薛允升提出,即便是墳墓被他人發掘盜葬,但子孫并未妥善處置發掘者盜葬入墳墓的棺槨(發掘拋棄),也要“照祖父母、父母被殺、子孫不告官司而擅殺行兇人律,杖六十”[15]。發塚行為的目的多在得財,各朝代處罰都較普通竊盜要嚴重許多。薛允升在《讀例存疑》中提出此罰的原因為:“惡其圖財而禍及死尸。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見也。”從歷代的律例處罰程度可看出,法律對于發塚行為的處罰呈愈發嚴厲的態度。
(三)蔭木有清一代,對子孫砍伐買賣行為進行了嚴格的限制,首見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二月內提督衙門議奏:“嗣后如有不孝子孫,將祖父墳園樹木砍伐私賣一株至十株者,杖一百,加枷號二個月;十株以上,即行充發。奴仆盜賣者,買同盜他人墳園樹木者,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其盜賣墳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者,亦照此例治罪。”[6]對于私買之人,內提督衙門議奏:“至于私買之人,若不嚴加懲創,恐市井無賴,貪利引誘,則盜賣弊端仍難杜絕。嗣后有犯,請亦照盜他人墳園樹木例治罪。”[6]此條是根據步軍統領大學士傅恒修改乾隆五年(1740年)原例后所提方案制定的①*。《讀例存疑•卷二十五•刑律•賊盜•子孫盜祖父墳塋墳樹條》分析子孫、他人、奴仆犯案罪重罪輕時說道:“原定之例,子孫罪輕,他人次之,奴仆為重,以墳樹究系子孫己物故也。”[15]墳樹即為子孫之物,為何還要重罰子孫砍伐與盜賣行為呢?“以盜賣墳樹,跡近不孝,故重之也。”[15]不僅在國家律例中禁止砍賣蔭木,在族譜中也有規定。《潤東苦竹王氏支譜》記載:“塋墓樹木所以遮護風水,有偷伐一株者,拿獲以竊盜論,至自己祖墳,敢行伐賣,更以不孝論。”[17]在墳產合同文書中,申餙護墳合同、禁限護產合同、養蔭合同、看墳合同②等常涉及對于蔭木的權利限制與約定保護事項,如同治四年(1861年)正月《學祠支孫人等付養蔭木合同》規定,祠人在祖墳旁植種“杉松雜木以供國課,以護祖墳”。但因為年久荒廢,眾議將山交“詹廣興叔侄等攬去掌養”。在掌養時,對祠人、對掌養人都是“照舊鳴鑼申禁”。另外,在合同中還明確規定了“自今申禁之后,內外人等毋許入山侵害,如有犯者,照禁例議罰。倘悖橫不遵者,報明祠眾,一同辦理,或鄉理,或聞公”(同治四年正月學祠支孫人等付養蔭木合同。俞江教授藏)。
三、司法實踐中的限制
除在立法上對墳山權利進行限制外,在司法實踐中也對墳產權利進行了嚴格的限制。(1)對祖墳再行入葬權利的限制。在《三邑治略》審訊段應貴一案中,段應貴將其媳的棺葬在了祖墳前面,被族人控訴,而段應貴也訴墳碑被他人所毀。地方官吏以祖墳“現有五十余年,無人葬棺,即不應再葬”為由,斷令“段應貴趕緊擇期遷葬,以后此山永遠封禁。被毀墳碑不論何人所毀,責成族人修復”[18]。墳墓之間以及買賣墳地后都應當留足“穿心除界”距離。在《三邑治略》小王鄧氏控大王鄧氏一案中,小王鄧氏買王周氏祖遺田地一處,地內有大王鄧氏祖墳,小王鄧氏與王周氏的契據中并沒有寫明要除留墳界,但是當地官員依舊認為:“如有王姓祖墳,上下左右,穿心除界一丈五尺,其余古冢,有墳無界。”[18]《民事習慣調查報告》就記載了奉省各縣的習慣:“原契中既未注明該墳地一定尺幅,一經涉訟,無從核辦。會員調查各縣習慣,凡塋地界址不明者,均認為廣袤各十八弓,合地一畝三分三。此種習慣按照前清通禮所載,塋地自塋心至四旁僅應十步,降至庶人尤當稍減。”[19](2)嚴格處罰子孫發掘祖先墳墓的行為。在《刑案匯覽》中,有關發塚的嚴重犯罪,司法與立法保持相當一致。在《刑案匯覽•葬父無資盜棺剝衣當錢埋葬》案例中,宇文煥因為葬父無資,就盜棺剝衣當錢埋葬。即使只是抽取死者尸衣,也被依照“子孫盜祖父母、父母未殯埋尸柩,不分首從,未開棺槨者皆絞立決,開棺見尸者皆斬立決”[20]。在《刑案匯覽•賣地造壙誤挖朽棺撿骨另葬(嘉慶二十二年案)》中,姚勝林將墳山賣給陳明光,在遷墳時,姚將鄰界方姓墳墓誤認為廢穴而誤挖。在本案中,姚勝林“于盜發年久穿陷之冢,開棺見尸為首一次擬軍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陳因“聽從雇人誤挖,照為從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20]。在司法判例中,有關蔭木的判例較多,其原因是民眾常由于界址不清而導致砍伐蔭木,繼而引發糾紛。在《三邑治略•吳榮朝案》例中,吳榮朝認為,青龍山是本家留作培植風水的,不準外人砍伐,但李世爵則稱青龍山是己山。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吳榮朝僅有分關而沒有約據,李世爵雖有約據,但約據上并未記載上抵“青龍山”字樣。最后,判決青龍山為官荒,既培陰地,又培陽宅,彼此不準在此砍伐樹木[18]。在沒有明確證據證明為蔭木時,當地官吏的判決往往是雙方均不準砍伐。國家律例對于盜砍盜伐蔭木的處罰十分嚴厲,但在地方審判時,地方官從情理出發,并不會依照律例決斷。在《諸暨諭民紀要•黃金生控周賡燾等暗焚墳蔭案》例中,周賡燾暗焚黃家墳后松木10株。而國家律條規定,砍伐他人墳樹的不論多少即有罪。對于此案例,地方官認為,周氏墳木為開科,風水對于開科的影響是存在的,最后乃令“周備錢繳給黃另買田畝,黃將墳后蔭樹概行拚砍”[21]。在司法過程中,地方官吏追求的是情理平衡、矛盾化解,更注重民間習慣與秩序,而非嚴格遵守國家律例。
四、余論
墳墓,埋葬死者的固定場所,為營葬死者提供容納,是墳產的核心概念[1]。而墳產具有經濟利益,既是身份象征,又是尊祖敬宗及提高宗族、家庭社會評價的要求,還是善待祖先、期盼蔭庇的保證。因此,保證祖先墳墓不被破壞,才是子孫共同的責任。“今夫祖宗之賴有子孫者,養生送死之外。惟此春秋祭掃,保守墳墓為重耳。”[22]回顧法的歷史,中華法系在禮法體系下,權利義務不同于西方法社會,它的權利義務統合于血緣家庭共同體而非原子式個人。國家對于國家法與民間法律秩序權衡與取舍呈現出法律與民間習慣之間的磨合與對沖,這一磨合與對沖之間的角力體現在墳產權利上,即為其權利的限制性。墳產權利雖具備西方所有權理論當中的占有、使用、收益以及部分處分的特征,但其自身獨特的有限性決定了墳產權利并不是西方所有權的權利,其權利的限制也并非西方法意義上的“所有權限制”①*。不論是羅馬法還是日耳曼法,都承認所有權的核心是憑借自己的意志直接對物進行支配,而支配的重要表現即為對物的使用、收益、處分。2007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在第一章第二條即提出:“本法所稱物權,是指合法權利人依法對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權利,包括所有權、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梁慧星在《所有權形式論》中也提出,按照現代民法理論,不自由的或不完全的所有權就不是所有權[23]。因此,墳產權利的屬性并非現今民法意義上的所有權。傳統中國對墳產權利進行限制的目的,并非與西方對所有權的限制一樣(強調對權利的利用),而是著重對權利狀態的持續維護,強調權利的“義務性”。這種對權利進行維護的觀念基礎則來自于中國人觀念中死者仍需供養的信仰,以及禮法體系下的血緣關系。一國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對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的認定,這一認定必須是根植于本民族社會的。對于與民眾關系密切的民法,立法者除了要具備謹慎考慮法律條文以及相關理論修養外,更重要的還需要有透過條文制定尊重和理解傳統中國民眾生活以及本民族、社會的能力與經驗。當今社會承千年傳統而來,中華法系下權利義務統合于血緣家庭共同體的這一典型特征深刻影響著今人,并融入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法律必須尊重傳統、回應傳統,因此,對于墳產權利限制性的思考也許僅僅是某一微小細枝的發端而已。
參考文獻:
[1]余娜如,赫琳.論清代公同共有財產之墳產的權利內容[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0):53-57.
[2]何小平.清代習慣法:墓地所有權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M].5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4]梅仲協.民法要義[M].張谷,點校.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5]薛允升.唐明律合編[M].懷效鋒,李鳴,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6]唐明清三律匯編[M]∥楊一凡,田濤.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8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7]井上徹.中國的宗族與國家禮制:從宗法主意角度所作的分析[M].錢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8]田濤.大清律例[M].鄭秦,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9]懷效鋒,點校.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
[10]長孫無忌.唐律疏議[M].劉俊文,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11]竇儀.宋刑統[M].薛梅卿,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2]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M]∥楊一凡,田濤.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1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13]劉義斌.劉氏宗譜[M]∥張海瀛,武新立,林萬清.中華族譜集成:第5卷.成都:巴蜀書社,1995.
[14]王溥.唐會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5]薛允升.讀例存疑[M].黃靜嘉,點校.臺灣:成文出版社,1970.
[16]李正榮.合肥李氏五修宗譜[M]∥張海瀛,武新立,林萬清.中華族譜集成:第4卷.成都:巴蜀書社,1995.
[17]王振澤.潤東苦竹王氏族譜[M]∥張海瀛,武新立,林萬清.中華族譜集成:第3卷.成都:巴蜀書社,1995.
[18]熊賓.三邑治略[M]∥楊一凡,徐立志.歷代判例判牘:第12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19]前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M].胡旭晟,夏新華,李交發,點校.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20]祝慶祺,鮑書蕓,潘文舫.刑案匯覽三編(三)[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21]倪望重.諸暨諭民紀要[M]∥楊一凡,徐立志.歷代判例判牘:第10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22]劉冰雪.清代喪葬法律與習俗———以《大清律例》的規定為重要依據[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9.
[23]梁慧星.梁慧星文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作者:余娜如 單位:太原工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