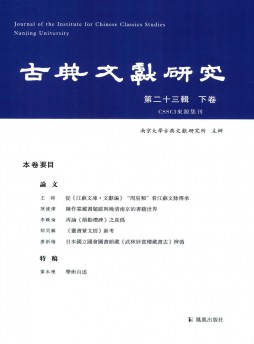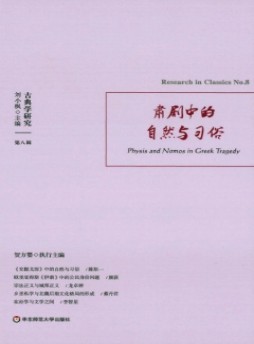新古典經濟學的產業結構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產業結構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時間維度下生產要素產業間的流動導致產業結構變動的文獻綜述
時間維度下的生產要素流動是指生產要素在三次產業之間的流動。W.ArthurLewis(1954)最早發現勞動力報酬是勞動力要素在產業間轉移的源動力,非農產業相對于農業具有較高的工資報酬,吸引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中的工業轉移。劉鶴(1991)發現,勞動力并非必須遵循從農業向工業,再向服務業的流動方向,農業勞動力直接流向服務業,可以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張保法(1997)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分析了勞動力在產業間的流動對三次產業的影響。認為勞動力轉移帶動了要素投入結構的變動,提高了三次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美國學者錢納里研究了同一產業中,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流向高生產率部門所帶來的經濟效應。在其《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中提到,如果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會形成要素流動的產業結構變化,進而促進經濟增長(Peneder,2002)。羅潤東(2006)從技術升級角度分析了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產業間流動受阻的原因。認為技術進步在加快產業升級的同時,還會導致出現短暫性的失業現象,勞動者失業時間的長短取決于技術進步水平和勞動力技能升級水平之間的時滯。技術進步帶動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勞動力技能提高反作用力于技術的提高,經濟增長是技術、勞動力和資本相互作用的結果。呂冰洋(2008)分析了要素中的資本流動和技術升級對產業結構變化的作用。認為資本要素的投入會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技術進步提高了資本要素的產出效率。謝露露(2013)認為,產業聚集效應的發揮必須有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作為基礎,技術進步會提高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但是迄今為止的所有相關的研究都是采用靜態或者靜態比較的研究方法,然而無論是以時間維度,還是以空間維度,生產要素的流動都具有動態特征。為彌補現有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對我國改革開放后生產要素流動驅動產業結構變化的軌跡進行分析,為詮釋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新的視角。
二、空間維度下我國產業結構的動態演變軌跡
區域經濟總量的增長一般是同產業結構的演變相伴在一起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區域經濟增長的速度。一個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將不可避免地對其他區域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國家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由于各地區之間存在著要素稟賦的差異,在封閉條件下,對于當地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而言,并不能形成兩者之間的最佳配比,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分別追尋工資和利息的最大化,形成了驅動其在區域間的流動,影響各區域的產業結構變化。
(一)要素的空間移動推動產業結構變化的理論分析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模型規定,勞動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按照邊際產品價值得到報酬,勞動者追求工資最大化,資本提供者要求利息最大化,經濟主體對收益的最大化要求注定了要素必定會在區域間流動,我們假定區域間生產要素是完全流動的,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可用圖1表示。由圖1可見,假如存在兩個區域(A區域和B區域),起初,A區域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為主導產業,資本的投入量超過B區域,而B區域以第一產業為主,勞動力投入占主導,根據邊際遞減規律,A區域高資本投入使得資本的邊際產量低于B區域,勞動報酬高于B區域,勞動力和資本的收益最大化特點引致生產要素在區間內的轉移,A區域的資本向B區域轉移,B區域的勞動力向A區域轉移,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導致AB兩個區域內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比例發生變化。按照新古典理論,勞動和資本之間存在固定比例的規模收益,且生產要素邊際產量為正,隨著投入的增加其邊際產出會下降。在生產要素初始流動過程中,要素之間的比例尚未達到最佳配比,資本由A區域向第一產業為主導的B區域轉移。同時,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為主導的A區域流動,三個產業的生產要素投入均朝著最佳配比接近,三個產業的產值均有較大提高。待勞動力和資本達到最佳配比之后,要素流動若依然進行,則造成三個產業的產值下降。
(二)我國1978-2012年產業結構變動的空間轉移分析中國東、西部產業結構差異較大,體現在經濟地理學上表現為產業重心轉移的不一致性。本文依據物理學中的重力模型探討產業結構在區域間的差異性。根據物理學常識可知,總力矩最小的點為重心所在點,可以通過(1)式和(2)式的疊代,推算重心的坐標。本文按照地理坐標把中國(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分別進行研究,其中東部包括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和上海,中部包括廣東、海南、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遼寧、吉林和黑龍江,西部包括四川、云南、貴州、廣西、重慶、青海、西藏、寧夏、新疆、陜西、甘肅和內蒙古。1.第一產業動態軌跡特征我國第一產業主要由農業部門構成,目前農業發展整體水平較低,受自然條件影響大,導致農業重心分布的隨機性很大。在我國東部地區,熱、水、土條件配合較好,勞動力充足,我國大部分耕地、農作物和林業、畜牧業、和漁業集中在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氣候比較干旱,自然條件相對較差,且是少數民族聚居區,交通不便,農業發展歷史較晚,人口稀少,農耕地小而分散,大部分地區以放牧業為主。受自然條件的影響,我國第一產業重心移動并不具有規律性。第一產業產值重心變動的動態軌跡,見圖2。根據圖2,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一產業產值重心的移動并無規律可尋,東西方向的差異大于南北方向。總體來看,由于農業的地域性限制和土地要素的非流動性,農業重心的遷移較小,尤其是在南北方向上。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集約農業的出現,農業重心有了較大的轉移,主要表現在東西部的差異較大。2.第二產業動態軌跡特征受資源稟賦的限制,以及國家政策的傾斜,我國第二產業在全國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我國第二產業產值重心在全國區域內的動態移動軌可跡用圖3表示。由圖3可見,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二產業重心基本是向著西南方向轉移。從年份看,1981-1991年總趨勢向西南方向轉移,1991-1994年向東南方向回流,1994年-2000年基本沒有大的變化,2000年之后第二產業重心總體上是向西部移動。2000年之前,第二產業生產總值重心的移動主要是南北方向,第二產業在南北方向上的不均衡布局和我國東北、華北一些老工業基地的衰落有直接關系。改革開放前,東北地區在國家“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重點支持下,憑借能源、礦產資源的優勢,形成全國的重工業基地。到1978年,東北三省的產值占全國的13.5%,工業產值占16.9%,機械、石油、化學、冶金等工業的產值約占全國的60%。1994年,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模式基本確定,東北地區對市場化改革難以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相對緩慢,經濟增長乏力,第二產業增長緩慢。而在此階段,南方沿海和沿江地區利用國外資源發展工業,特別是輕工業發展較快,第二產業重心逐漸向南方移動,我國產業布局形成“南輕北重”的局面。1994年之后,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形成,長時期以資源消耗為代價的重工業發展,加劇了鐵礦、石油等資源緊缺,北方地區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發展輕工業,第二產業重心停止向南部移動。1994-2000年,我國第二產業重心基本保持不變。在此期間,我國南部地區加快發展以加工業為特征的輕工業,北部地區調整重工業和輕工業結構也取得成效,南方和北方第二產業增長勢力處于動態均衡中,經濟重心在全國范圍內保持不變。2000年以來,在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指引下,第二產業重心向西部移動。2000年,西部第二產業產值比全國平均值低4.42個百分點,在工業結構上,西部地區采掘工業和原料工業比重高,高新技術產業比重低,采掘業和原料工業占總產值的36.5%,高出全國平均值7.6個百分點,高出東部地區10.8個百分點,屬于典型的資源性工業結構。經濟總量低于東部地區,為縮小東西部的經濟差距,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帶動了第二產業重心向西部地區移動。3.第三產業動態軌跡特征我國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并且第三產業服務于第二產業的發展,其發展程度依賴于第二產業。圖4描述了我國1978-2012年第三產業產值重心的動態變動軌跡。由圖4可見,改革開放后,我國第三產業重心總體上呈現“Z”形動態轉移軌跡,1978年出現短暫的向西部轉移現象,1979-1988年向東部轉移,1988年-1991年向西南方向移動,1992-2010年向東部和南部移動,2011年和2012年向西北方向移動。其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迅速發展,產業結構日趨完善,第三產業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在國民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第三產業相應發展較慢,在國民經濟構成中所占比重較小,導致第三產業重心向東南移動。
(三)產業結構的區域差異性帶動經濟重心的階段性轉移根據現代區域經濟學理論,區域經濟發展不僅表現為產值或者收入等經濟總量指標的上升,而且必然伴隨產業結構的演變。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區域經濟總體發展水平與區域產業結構是密切相關、相互影響的,而且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區域經濟增長的速度。某個區域的產業結構調整將不可避免地對其他區域產生影響,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區域間產業結構的調整直接影響到經濟總體重心在區域間的轉移,圖5為我國1978-2012年經濟重心在全國范圍內的動態轉移軌跡。由圖5可見,受第三產業重心在全國范圍內的影響,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重心轉移軌跡明顯,具體可分為五個階段:1978-1982年、1982-1987年、1987-1991年、1991-2004年和2004-2012年。其中,1978-1982年、1987-1991年和2004-2012年為我國經濟重心向西部轉移階段,1982-1987年和1991-2004年為我國經濟重心向東部轉移,見表1。由表1可見,1978-1982年、1987-1991年和2004-2012年,我國經濟重心移動與第二產業重心移動方向一致;1978-1982年,第一、第三產業重心移動方向與我國經濟重心移動方向相反;1987-1991年,三次產業重心移動方向均與我國經濟重心移動方向一致,而在2004-2012年,第一、第二產業重心移動與我國經濟重心移動方向一致,而第三產業重心移動與我國經濟重心移動方向相反。比較特殊的是1991-2004年,我國經濟重心移動方向與第二產業重心移動方向相反,而與第一、第三產業重心移動方向一致。可見,改革開放以來,除1991-2004年,第二產業重心與我國經濟重心移動方向相反外,其余年份第二產業重心移動都與我國經濟重心移動方向一致。
(四)基于要素空間流動視角的產業重心和經濟重心動態轉移解釋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經濟增長是各生產要素達成最佳比例組合后所能實現的最大生產規模。對于生產要素的配比未達到最佳比例的區域,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的流入會提高流入地區的生產能力,同時使技術知識得到擴散。對于存在過多勞動力或者過多資本的地區,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受到抑制。通過對我國三次產業和經濟總量在空間維度的移動特征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三次產業在各區域的比重均存在動態演變,下面我們從新古典生產要素流動視角對我國區域產業結構和經濟重心移動進行詮釋。按照發展模式的差異,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年之前,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生產要素由國家統一進行行政性配置,通過國有企業進行要素的組合和生產,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均未進入市場,企業也沒有對國外技術進行模仿和改進,技術進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第二階段是1978-1992年等生產要素的配置方式開始向市場化方向轉變。在這個階段,市場機制處于摸索階段,并沒有達到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要求。對于農村勞動力而言,此階段主要是“離土不離鄉”的轉移模式,以這種方式轉移的勞動力大約占全國勞動力轉移數量的82.4%,戶籍、福利等體制改革滯后,導致農村勞動力并不容易向城市或者其他地區轉移,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并不存在大規模轉移的局面。第三階段是1992年之后,1992年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改革目標和共同富裕理想模式的確定,使勞動力和資本逐漸具有市場化特征(黃家驊,1999),經濟增長驅動要素之間的市場化結合方式基本形成。但是在此階段,市場化進程是漸進性的。具體見圖6、圖7、圖8和圖9。本文以1992年為分界點,考察市場化成分的經濟增長生產要素,對區域經濟總量和產業結構的影響,見表2。由表2可見,在1992-2004年,我國經濟重心與第一、三產業移動方向一致,勞動力和R&D投資與第一、三產業移動方向一致,只有資本要素重心移動方向與第二產業重心移動方向一致;2004-2012年,我國經濟重心與第一、二產業產值重心移動方向一致,且與資本要素移動方向一致。
三、時間維度下我國產業結構的動態演變軌跡
(一)時間維度下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和要素結構的變動度分析我國按照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性強弱將我國1978-2012年的時間跨度,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78-1992年,即開始改革開放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總體目標確定的階段,在此階段,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受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分配方式影響較大,生產要素并不具備受市場化的流動方式;第二階段為1992年-2000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調整和發展階段,在此階段,生產要素的流動具備市場化特征,即生產要素按照市場供求關系在產業間流動的階段;第三階段為2000年-2012年,即我國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在政策引導下生產要素可以自由地在區域間流動,經濟總量增長較快,為調整產業結構并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為目標的階段。干春暉(2009)使用平均結構變動度對中國三次產業結構和生產要素的構成進行分析,我們借鑒其方法,從新古典經濟學視角出發,對我國生產要素結構變動和產業結構變動進行動態分析。由表3可見,我國三次產業在1978-2012年期間,第一產業比重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2年的9%;第二產業比重保持在50%左右,經濟增長長期以工業為主;第三產業比重逐年增加,由1978年的23.9%增加到41%。從生產要素的動態變化角度看,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數量下降較快,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數量逐年增加,且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增長率速度快于第二產業;資本要素在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的比重逐年增大,且增大的幅度較大,而第二產業中的資本要素比重降低,但降低幅度較小。改革開放后,資本要素在三次產業中的總量增大,但增長幅度是不成比例的。從平均結構變動度上看,具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978-1992年、1992-2001年和2001-2012年。1978-1992年,一、二產業產值平均結構變動度均下降,且第一產業下降快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上升速度較快;第一產業勞動力平均結構變動為負值,且以較快的速度下降,第二、三產業上升為正,且第三產業快于第二產業,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流動,且流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力速度快于第二產業;第一、第二產業的資本平均結構變動度為負,第三產業為正,說明在此階段資本要素向第三產業流動,且資本要素從第一產業流向第三產業的速度快于第二產業。即,勞動力主要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流動;資本由農業和工業向服務業流動。結果是,第三產業產值增長較快,由于勞動力和資本要素通過市場化方式自由結合趨向于最佳配比,兩個要素共同驅動了產值的較快增長。1992-2001年,產值平均結構變動度第一產業下降,且第一產業勞動力平均結構變動度下降較快,三次產業的資本平均結構變動度均上升,第三產業平均結構變動最大,同時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均向第三產業流動,勞動力主要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流動,資本要素流向第三產業的速度快于流向第二產業的速度。勞動力向服務業流動,資本要素流向工業和服務業。2001-2012年,第一產業產值平均結構變動度為負,第二、三產業為正,且第二產業大于第三產業,在此階段經濟總產值中以第二產業產值所占的比重為主;勞動力平均結構變動度第一產業為負,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大小相當,且均為正,勞動力要素由農業分別向工業和服務業流動;第三資本要素平均結構變動度產業為負,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為正,第二產業遠大于第一產業,資本要素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總體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一產業產值平均結構變動度為負,第二、三產業為正,且第二產業平均產值結構變動度為0.06,遠小于第三產業的0.49;對于勞動力平均結構變動度,第一產業為負,二、三產業為正,且第三產業為0.68大于第二產業的0.37;資本要素平均結構變動度,三次產業均為正,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值相當。1978-2012年,勞動力要素由第一產業主要流向第三產業,資本要素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但第一產業投資呈現穩步回升的跡象,有利于農業向高級化發展。
(二)時間維度下我國產業結構變動驅動要素的貢獻度分析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經濟增長驅動要素理論,產值增加由是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三個要素共同貢獻的,鑒于技術因素在短期內的不可控性,我們假定技術要素為固定參數,然后對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作對數處理。鑒于數據單位的不統一,為防止回歸結果失真,對數據進行了標準化處理,數據的ADF單位根檢驗發現為非平穩數據,但進行一階差分后趨于平穩,可以進行多遠回歸,結果如下。其中n=1、2、3,分別表示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在(6)、(7)和(8)式中,各產業的勞動力分別用L1、L2和L3表示,使用各產業固定資產投資作為資本要素的替代變量,分別用K1、K2和K3表示,并且假定技術要素為定值,數據來源于CEIC數據庫。括號內為t值,(6)式中L1和K1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0.0156和0.0193,調整后的R2=0.6326,DW=2.6480,F值為11.1912,F值對應的概率值為0.0015;(7)式中L2和K2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0.0091和0.0023,調整后的R2=0.6801,DW=2.3600,F值為16.9465,F值對應的概率值為0.0002;(8)式中L3和K3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0.0345和0.0000,調整后的R2=0.8062,DW=1.9097,F值為27.0344,F值對應的概率值為0.0000。回歸結果表明:就勞動力要素而言,第一和第三產業勞動力要素的彈性系數均為負值,第一產業的勞動力彈性大于第三產業。第一產業中的農業是勞動力密集行業,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超過4600萬,表明我國過剩的勞動力對第一產業造成負擔,而根據時間維度上,勞動力在產業之間的流動方向分析,勞動力主要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流動,對第三產業形成壓力,降低了勞動效率。而對于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1978-1988年,我國工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為5%。其中,1987年和1988年的增速均超過10%,全國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較新中國建國初期來提高了5倍,第二產業勞動者生產效率較高。可見,對于勞動力,第一產業勞動力盡管向第三產業流動,但依然處于勞動力過剩狀態,而第三產業吸納了過多的勞動力,主要原因是第一產業的勞動者并不具有第三產業所需的勞動技能。勞動者勞動技能的提升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不一致,造成第三產業勞動力效率降低。第二產業的勞動力效率明顯高于第一、三產業。但在我國第二產業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要素還未達到最佳配比。就資本要素而言,三次產業中資本要素的效率系數均為正,且第三產業大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資本要素的效率最低。根據時間維度上資本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方向可知,資本要素主要集中于第二、三產業,第二產業資本要素的效率低于第三產業。
四、結論
在空間維度上,受自然條件和土地無法移動的影響,我國第一產業產值重心的轉移沒有明顯的規律;第二產業在1978年之后總體上呈現向西南方向轉移的軌跡,其中,1978-2000年呈現南北方向轉移,2000年之后呈現東西方向轉移,第二產業重心在南北方向的不穩定與東北、華北老工業基地的衰落相關,在東西方向的不穩定發展是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所引起的;1978-2012年,我國第三產業呈現“Z”字形的轉移特征,主要是東部產業結構調整速度較快的結果。從要素流動的視角看,在1992-2004年,我國經濟重心與第一、三產業移動方向一致,勞動力和R&D投資與第一、三產業移動方向一致,而資本要素重心移動方向與第二產業重心移動方向一致;2004-2012年,我國經濟重心與第一、二產業產值重心移動方向一致,且與資本要素移動方向一致。在時間維度上,我們根據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強弱將我國1978-2012年分為三個階段,并使用平均結構變動度對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進行動態分析。研究結果表明,1978-2012年,總體上,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數量下降較快,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勞動力數量逐年增加,且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增長率快于第二產業;資本要素在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的比重逐年增大,且增大的幅度較大,而第二產業中的資本要素比重降低,但降低幅度較小。1978-1992年,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流動,且勞動力流向第三產業的速度快于流向第二產業的速度。而資本要素由農業和工業向服務業流動的結果導致第三產業產值增長較快;1992-2001年,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均向第三產業流動,勞動力主要由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流動,資本要素流向第三產業的速度快于流向第二產業的速度;2001-2012年,勞動力要素由農業分別向工業和服務業流動,資本要素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從生產要素對三次產業的貢獻效率角度看,第一產業勞動力盡管向第三產業流動,但依然處于勞動力過剩狀態,而第三產業吸納了過多的低技能勞動力,勞動者勞動技能的提升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脫節,造成第三產業勞動力效率降低。第二產業的勞動力效率明顯高于第一、三產業,且隨者新勞動力的流入,勞動者效率逐漸提高。此外,在我國第二產業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要素還未達到最佳配比。就資本要素而言,三次產業中資本要素的效率系數均為正,且第三產業大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資本要素的效率最低。
作者:王曉芳于江波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