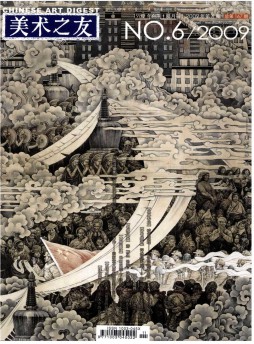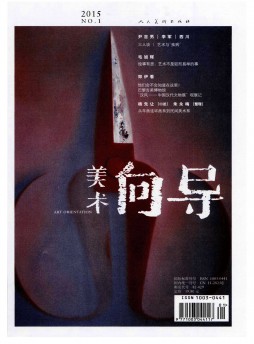犍陀羅美術(shù)研究的現(xiàn)狀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犍陀羅美術(shù)研究的現(xiàn)狀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絲綢之路雜志》2015年第九期
一、考古發(fā)掘與圖錄刊行
犍陀羅佛教美術(shù)衰敗已逾千年,往昔已被掩埋的寺院遺址經(jīng)過發(fā)掘才得以識(shí)其真面貌。19世紀(jì)末以來,英國考古學(xué)家卡尼伽姆、斯坦因、斯普那、哈恩古林維斯等對(duì)白沙瓦盆地周邊的佛教寺院進(jìn)行了考察發(fā)掘。狹義的犍陀羅是指以白沙瓦盆地為中心的遺跡,另外,還包括東部的塔克西拉、北部的斯瓦特、山地的哈扎拉、普奈魯、德意魯、巴就魯?shù)鹊赜颍灿猩⒃诘姆鸾踢z跡說;阿富汗賈拉拉巴德周邊地域(古代稱為南加哈爾,以哈達(dá)寺院遺跡而著名)以及喀布爾近郊、北部的迦畢試地區(qū)的許多佛教遺跡在內(nèi),將這些地域包括在內(nèi)的廣義的犍陀羅,也稱之為“偉大的犍陀羅”。馬歇爾對(duì)塔克西拉都市遺跡和佛教寺院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戰(zhàn)后的考古調(diào)查活動(dòng)中,日本京都大學(xué)調(diào)查隊(duì)對(duì)犍陀羅買哈桑達(dá)、塔來里的佛教寺院進(jìn)行了發(fā)掘,兩處遺跡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雕刻、寺院結(jié)構(gòu)遺跡(考古報(bào)告于1969年、1978年刊行)。另一方面,意大利考古隊(duì)于1956年對(duì)斯瓦特地區(qū)進(jìn)行了發(fā)掘調(diào)查,對(duì)尤德格拉姆、巴里考特都市遺跡之外,還對(duì)布特格拉Ⅰ號(hào)、帕爾、薩伊特•夏利弗Ⅰ號(hào)的佛教寺院遺址進(jìn)行了考察并得以明確其位置,犍陀羅美術(shù)的誕生以及演變的表現(xiàn)樣式逐漸得以明確。特別是法賽奈先生對(duì)布特格拉Ⅰ號(hào)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雕刻、貨幣等遺品。雕刻圖錄于1962~1964年(但是文本篇未出版)、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六冊(cè)于1980~1981年刊布。由考古發(fā)掘報(bào)告得知,布特格拉Ⅰ號(hào)佛寺是從公元前3世紀(jì)至11世紀(jì)經(jīng)歷了由盛到衰的一個(gè)漫長(zhǎng)的存續(xù)歷程。另外,帕爾佛寺發(fā)掘報(bào)告兩冊(cè)于1993年出版,據(jù)此地出土的貨幣為依據(jù)可以得知1~5世紀(jì)佛寺建筑的編年軌跡。此后,薩伊特•夏利弗Ⅰ號(hào)的發(fā)掘報(bào)告以及僧院編與塔院編也相繼刊行(1989、1995年),經(jīng)過對(duì)布特格拉Ⅰ號(hào)、帕爾、薩伊特•夏利弗Ⅰ號(hào)這三處寺院的建筑構(gòu)建的對(duì)比研究得出了編年。關(guān)于佛教雕刻,法賽奈的遺稿對(duì)布特格拉Ⅰ號(hào)、薩伊特•夏利弗Ⅰ號(hào)的建筑物編年為基礎(chǔ),對(duì)出土雕刻地進(jìn)對(duì)比研究,特別論述了犍陀羅雕刻初期表現(xiàn)形式,是繼馬歇爾以來對(duì)犍陀羅佛教美術(shù)編年的重新審視之作。
意大利考古隊(duì)在斯瓦特地區(qū)的考古發(fā)掘持續(xù)數(shù)年,白沙瓦大學(xué)和巴基斯坦考古局對(duì)德以魯、斯瓦特大量的佛教遺跡進(jìn)行了發(fā)掘。在對(duì)斯瓦特河右岸的德魯爾地區(qū)的安達(dá)德里、卡特帕特、達(dá)姆克特等遺跡、布特格拉Ⅲ號(hào)等地的佛教寺址進(jìn)行了發(fā)掘,出土了相當(dāng)數(shù)量的雕刻作品。以上這些發(fā)掘成果雖然包括概報(bào)在內(nèi)出版發(fā)行了相關(guān)報(bào)告,但是,遺憾的是,對(duì)于發(fā)掘的記述、畫面以及圖版等記述并不充分的地方很多。同時(shí),巴基斯坦考古局對(duì)白沙瓦、巴就魯?shù)鹊貐^(qū)進(jìn)行了一般性的考古調(diào)查,在這方面,出版發(fā)行的考古調(diào)查報(bào)告還是很有益的(1996年)。另外,日本京都大學(xué)隊(duì)(以西川幸治為代表)在犍陀羅東端藍(lán)尼伽特遺跡進(jìn)行發(fā)掘,東京國立博物館調(diào)查隊(duì)在哈扎拉地區(qū)的扎魯?shù)吕镞z址進(jìn)行了發(fā)掘。前者對(duì)發(fā)掘成果出版了圖版編和概報(bào),后者研究成果由小泉惠英撰寫了概報(bào)以及石雕像群的復(fù)原考察。諸如上述考察發(fā)掘活動(dòng)一直持續(xù)到1980年以后。另一方面,本地居民以探寶為目的發(fā)掘活動(dòng)也相續(xù)進(jìn)行,一些出土地或出土狀況不明的犍陀羅雕刻品大量出現(xiàn),并流入日本和歐美等國。其中一部分收藏在美術(shù)館、博物館內(nèi),大量藏入私人手中,私人藏品的情況下對(duì)于藏品的收藏地難以追跡。在這種情況下,栗田功先生曾致力于包括私人藏品在內(nèi)的犍陀羅美術(shù)品的調(diào)查,最終結(jié)集圖錄并出版刊行。有關(guān)犍陀羅雕刻圖錄的資料,將巴基斯坦博物館所藏作品進(jìn)行收錄的因福特先生編輯出版的作品享有盛名(1957年),這是此后至今收錄犍陀羅遺品數(shù)量最多的美術(shù)資料集成之作,其中對(duì)斯瓦特、布奈魯、巴休魯?shù)鹊爻鐾恋窨唐钒ㄔ趦?nèi),有助于讀者十分便利地廓清犍陀羅雕刻遺品的全貌。
除了寵大的遺品數(shù)量之外,犍陀羅美術(shù)資料集成對(duì)于美術(shù)史研究至關(guān)重要,這也是將來的必然課題。在此,還要感謝近年來各地的博物館相繼刊行了犍陀羅雕刻遺品的圖錄。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阿克曼恩先生對(duì)維克特里亞和阿魯巴特博物館所藏的故事浮雕作品的研究與圖錄刊行,瑞瓦夫先生對(duì)大英博物館圖錄的研究刊行,切德拉布塔切瑞亞先生對(duì)卡德克魯州立博物館圖錄刊行,本瑞德特先生對(duì)大都會(huì)美術(shù)館藏圖像的刊行等等。在以上例舉的成果中,大英博物館的圖錄最為充實(shí),不僅對(duì)作品解說,還對(duì)犍陀羅的地理、歷史、佛教的狀況以及對(duì)考古學(xué)調(diào)查收集的概要,還有包括窣堵坡、舍利容器及其信仰,雕像、浮雕的主題圖像,建筑裝飾以及年代斷定等方面,對(duì)研究史的概觀進(jìn)行了簡(jiǎn)潔明了的敘述,對(duì)研究者來說極為有益。以上對(duì)近年來考古學(xué)上的發(fā)掘調(diào)查與圖錄刊行情況進(jìn)行了概觀介紹,但是,對(duì)于犍陀羅美術(shù)史更深層次的考慮來說,還有一個(gè)極為重要的基礎(chǔ)資料不容忽視,那就是犍陀羅雕刻遺品究竟是在怎樣的寺院遺址以及在寺院何處出土的問題,還有當(dāng)初是怎樣的配置情況等等。向來對(duì)于犍陀羅美術(shù)史研究來說,諸如上述這樣的問題并沒有涉及到,斷片的出土遺品,如雕像或浮雕當(dāng)初是如何裝飾寺院的,試圖探討這一問題,就有必要了解和明確圖像以及佛教信仰的實(shí)態(tài)、佛教雕刻的功能。但是,且不說近年來的發(fā)掘調(diào)查,特別是20世紀(jì)前半期之前的記載發(fā)掘情況的發(fā)掘報(bào)告內(nèi)容十分簡(jiǎn)略有限,而且忽略了“當(dāng)初雕刻遺品是如何在寺院中配置的”這一問題。近年來,研究者們開始著手重新審視古老的發(fā)拙報(bào)告,對(duì)原始資料、原始照片進(jìn)行追跡,對(duì)遺跡進(jìn)行了更為詳盡的考察檢證。例如蒂索先生對(duì)薩利•巴羅來遺跡,埃林頓先生對(duì)夏瑪爾•嘎利遺跡,達(dá)爾先生對(duì)西克里遺跡,桑山正進(jìn)先生對(duì)夏吉肯德里遺跡。此外,在阿富汗,塔茲先生對(duì)哈達(dá)的特巴克朗遺跡,康邦先生對(duì)迦畢試的佛教寺院遺址進(jìn)行了考察檢證。得益于以上諸學(xué)者的考察檢證,上述各處佛教遺跡的存在情況大致已明確。近年來,犍陀羅研究活動(dòng)相關(guān)展覽會(huì)以及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相繼開展,內(nèi)容豐富充實(shí)的展覽圖錄和論文集相繼刊行。其中,介紹幾本最為值得關(guān)注的展覽圖冊(cè)。
E.ErringtonandJ.Cribbd,ThecrossroadsofAsia:TransformationinImageandSymbolintheArtofAncientAfghanistanandPakistan,Cambridge,1992.這是一本以東西文化交流為視點(diǎn)對(duì)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古代美術(shù)為主的展覽圖錄,收錄作品視野開闊、內(nèi)容豐富、分類多樣,作品解說也極為詳盡,特別是以東西文化交流為背景來看犍陀羅美術(shù)這一視角極其有益。D.E.Klimburg-Salter,BuddhainIndien:DieFruhindis-cheSkulpturvonKonigAsokabiszurGuptazeit,Wien,1995.這本書以犍陀羅和馬圖拉美術(shù)為主線,捕捉兩者的關(guān)聯(lián),進(jìn)而探討印度美術(shù)源流的展覽會(huì)圖冊(cè),其中包括平常難以見到的大量珍貴作品。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巴基斯坦•犍陀羅雕刻展》、《印度•馬圖拉雕刻展》(NH,2002年),這兩個(gè)展覽在東京國立博物館以及其他地方同期展出,出展作品包括了犍陀羅和馬圖拉各種形式的名品以及意趣深遠(yuǎn)的作品,使觀者對(duì)犍陀羅和馬圖拉兩地遺品的迥異一目了然。宮治昭編《犍陀羅美術(shù)與巴米羊遺跡展》(靜岡縣立美術(shù)館,靜岡新聞社,2007~2008年)以日本國內(nèi)所藏、極其珍貴罕見的雕刻遺品為主題圖像的展覽。其中大半作品是作者經(jīng)過近十余年的調(diào)查探訪而獲得的資料。顯示了日本國內(nèi)在世界范圍內(nèi)對(duì)犍陀羅美術(shù)遺品收集收藏的質(zhì)量首屈一指。M.Jansen,C.Luczantitzandothers,Gandhara:TheBud-dhistHeritageofPakistan:Legands,Monasteries,andPar-adise,Maina,2008.本書以巴基斯坦各地博物館收藏品為主,此外,還包括歐洲博物館藏品,犍陀羅美術(shù)大量的代表作品收錄在內(nèi)的展覽圖冊(cè)。展出作品以及展覽目錄內(nèi)容充實(shí)豐富。圖冊(cè)總共由37卷組成,每卷以短文隨筆的形式,內(nèi)容以歷史、貨幣、發(fā)拙史、考古、建筑、出土寫本、碑銘為主,涉及與雕刻相關(guān)的佛傳浮雕,佛像、菩薩像、神像以及與大乘佛教相關(guān)聯(lián)等多方面的問題的解明,可以說這本圖錄彰顯了目前犍陀羅研究的水平與方向。
二、犍陀羅美術(shù)初期表現(xiàn)———佛像的起源及其相關(guān)問題
塔克西拉的達(dá)摩拉吉卡大塔以及斯瓦特的布特卡拉大塔建筑年代的推測(cè),雖然說可以追溯到孔雀王朝時(shí)代(公元前3世紀(jì)),但是,此處沒有發(fā)現(xiàn)雕刻類的遺跡。應(yīng)該說,就在那之后起就有佛教雕刻制作了。中印度最古老的佛教雕刻推測(cè)是公元前100年時(shí)帕爾富特佛塔的塔門和欄楯上的淺浮雕。西印度以及南印度也是在公元前1世紀(jì)以后逐漸盛行制作佛教雕刻的。犍陀羅地區(qū)有雕刻遺跡的古老寺院,例如塔克西拉的西爾卡普的寺院以及達(dá)摩吉卡寺,根據(jù)馬歇爾研究明確記載,最初的淺浮雕是在塔克西拉出土的。印度•希臘人時(shí)代(公元前2世紀(jì)中期至公元前1世紀(jì)中期)的出土遺品數(shù)量有限,大部分在薩珊•帕提亞時(shí)代(公元前1世紀(jì)中期至公元1世紀(jì)中期)。屬于這個(gè)時(shí)代的雕刻遺品,除了有所謂的“化妝盤”,還有佛塔上的花環(huán)裝飾、圓雕的小型女神像、本生故事浮雕以及悉達(dá)多太子像等。可看出這些雕刻具有希臘、西亞以及古印度初期美術(shù)傳統(tǒng)兼融并蓄的風(fēng)格特征。在西爾卡普F區(qū)和G區(qū)有設(shè)有方形基壇的窣堵坡,其建筑裝飾由希臘文化和古印度兩種元素構(gòu)成。另外,在西爾卡普D區(qū)的支提殿堂出土的大量窣堵坡粉飾灰泥像頭部,也包括有薩梯風(fēng)格人物和近似于菩薩像都有很明顯的希臘式的技法。根據(jù)馬歇爾研究,犍陀羅美術(shù)開始于薩珊王朝時(shí)期,希臘文化的復(fù)興是在印度帕提亞時(shí)期,像飲酒圖一樣,在主題和裝飾上,以及技法上都受到了西方雕刻制作的影響,逐漸被佛教化的主題取代。在貴霜王朝初期,以佛傳圖為主,在“祇園布施”圖中出現(xiàn)了自然形態(tài)的佛像。高田修先生根據(jù)馬歇爾的意見,對(duì)年代更加詳細(xì)的探討,推測(cè)迦膩色迦紀(jì)元(馬歇爾采用128年之說),佛像起源于公元1世紀(jì)末期。犍陀羅佛像是如何誕生的呢,對(duì)于明確其形象考古學(xué)發(fā)掘?qū)⑹侵匾木€索。馬歇爾、高田修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對(duì)于塔克西拉的發(fā)掘成果來看,薩珊、帕提亞、貴霜王朝初期的遺址地層并不明確,而且上述遺址的出土品數(shù)量也是有限的,關(guān)于佛像的起源沒有充足的原因根據(jù)。另外,對(duì)于白沙瓦盆地周邊的佛寺遺址來看,是否這就是犍陀羅美術(shù)的初期表現(xiàn)形態(tài)的遺跡,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根據(jù)意大利隊(duì)對(duì)斯瓦特地區(qū)的發(fā)掘,特別是布特卡拉和薩伊特•夏利弗的佛寺遺址的發(fā)掘,成為明確犍陀羅美術(shù)初期表現(xiàn)形式的重要成果之一。
下面,對(duì)法賽奈先生的發(fā)掘報(bào)告進(jìn)行介紹。布特卡拉Ⅰ號(hào)佛寺遺址很大的空間內(nèi)(78×80米)中央建有大塔,在其周圍有很多的小塔、幢柱、祠堂、僧院等227個(gè)建筑物構(gòu)成的大型佛教寺院。根據(jù)發(fā)掘結(jié)果得知,這座寺院是從公元前3世紀(jì)起延續(xù)了1000多年,經(jīng)歷過幾次自然倒塌和再建、改修。以地質(zhì)和出土遺物為基礎(chǔ),發(fā)掘者先后分四期進(jìn)行了編年:中央大塔的創(chuàng)建為第一期,追溯為孔雀王朝時(shí)期;第二期是公元前2世紀(jì)至公元1世紀(jì)初;第三期是公元1世紀(jì)至公元3世紀(jì)末;第四期是3世紀(jì)末至7世紀(jì),在那期間經(jīng)歷了六期增建和改建。推測(cè)最終在11世紀(jì)伽茲尼王朝時(shí)期,隨著伊斯蘭的入侵而消亡了。對(duì)于犍陀羅美術(shù)的考察,布特卡拉Ⅰ號(hào)大塔的第三期改修是至關(guān)重要的。這個(gè)時(shí)期弓形大塔的直徑變?yōu)?5.22米,在圓形基壇的周圍置有欄桿,在四周設(shè)置有臺(tái)階。就在這次第三期的開始,法賽奈以出土貨幣的地質(zhì)年代得知是公元20年時(shí)期左右的。幢柱135號(hào),小塔14、17、22號(hào)等都是相同地質(zhì),推測(cè)都屬于同時(shí)期。135號(hào)幢柱是方形基壇圓柱建成,是克斯林式柱頭,頂部置有法輪。推測(cè)當(dāng)初大塔的四周應(yīng)該是被幢柱包圍,這與達(dá)摩拉吉卡大塔的形式是共通的。
另外,小塔14、17號(hào)都是方形基壇,其壁面有窩形基臺(tái),克林斯式柱頭,裝飾帶狀建筑物頂部突出裝飾圖案。其外觀與西爾卡普F區(qū)雙頭雕窣堵坡以及G區(qū)窣堵坡類似。雙頭雕窣堵坡方形基壇的正面設(shè)有臺(tái)階,壁面也配有克林斯式柱子。在其上面還裝飾有希臘神殿風(fēng)格的建筑屋頂上的裝飾,以及雙頭雕支提、拱門、印度式門,在上端有帶狀建筑物頂部突出裝飾。在方形基壇的上方的窣堵坡四周設(shè)有方形的印度式欄桿。可見,這種雙頭雕窣堵坡是希臘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融合。西爾卡普的窣堵坡(F區(qū))與布特卡拉Ⅰ號(hào)小塔(14、17號(hào)),是具有浮雕裝飾的最古老的犍陀羅窣堵坡的遺跡,希臘風(fēng)格與古代印度的要素表現(xiàn)混合多樣、趣味深遠(yuǎn)。印度的窣堵坡的基壇是覆缽形與圓形的結(jié)合體,幾乎全部都是圓形的,而犍陀羅的窣堵坡的基壇全部都是方形的。對(duì)于這一問題,桑山正進(jìn)先生對(duì)此有論述,他認(rèn)為這可以從羅馬帝國時(shí)代初期的墓室建筑中找到起源。另外,桑山先生認(rèn)為在南印度和西北印度見到的窣堵坡內(nèi)部壁面上車輪狀的構(gòu)造手法來源于奧古斯特靈廟的表現(xiàn)形式,貴霜時(shí)代佛教建筑、美術(shù)表現(xiàn)呈現(xiàn)出大的變化,從中可以看出來自羅馬建筑和美術(shù)的新的巨大影響。賽奈先生認(rèn)為,方形基壇的墓室以及具有方形基壇的圓形建筑物在希臘時(shí)代的希臘、土耳其、安納托利亞以及北非地區(qū)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確實(shí),希臘•羅馬的墓室建筑與犍陀羅的窣堵坡關(guān)系密切,這是應(yīng)該引起人們更多關(guān)注的地方。與此相關(guān)的薩伊特•夏利弗Ⅰ號(hào)的寺院址,根據(jù)考古發(fā)掘得知這里在當(dāng)初就是墓地所在地。特別是在犍陀羅,推測(cè)佛寺以及窣堵坡與葬禮關(guān)系密切,包括對(duì)僧侶的作用以及佛教雕刻的表現(xiàn)方式之上的考慮來看,意味深遠(yuǎn)。此外,布特卡拉Ⅰ號(hào)大塔三期GST3與同時(shí)期的幢柱135號(hào),小塔14、17號(hào)都有浮雕雕刻。幢柱135號(hào)的克林斯柱頭雕有上半身的供養(yǎng)者像、頂部有法輪和蓮花紋的裝飾主題紋樣(與桑奇大塔上紋樣相同)。小塔14、17號(hào)的裝飾有獅子面、睡蓮、鷲、蓮花上的有翼童子等。出土的同時(shí)期的帶狀建筑物頂部突出部分的斷片(B6841、B2587、B3792)上也有上半身人物像。這些浮雕雕刻的人物表現(xiàn)具有寬幅的圓臉、陰刻線的眼球以及半閉合的雙眼、雕刻線很長(zhǎng)的雙眉、小巧而突起的嘴唇,以陰刻手法的平行線來表現(xiàn)的佛像衣紋等上述這些特征,被稱之為“drawingstyle”風(fēng)格。
法賽奈把布特卡拉Ⅰ號(hào)大塔出土的大量雕刻以樣式類型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最古老的是“drawingstyle”風(fēng)格,年代可追溯至公元1世紀(jì)前半的貴霜王朝時(shí)代。法賽奈以犍陀羅最初期的美術(shù)表現(xiàn)風(fēng)格和馬歇爾的塔克西拉發(fā)掘成相結(jié)合,重新審視布特卡拉Ⅰ號(hào)的制作年代為薩珊•帕提亞時(shí)代。另外,將凡•羅哈伊澤•德立芙、法布雷格、福斯曼、卡特等諸位研究者對(duì)上述年代的佛教美術(shù)研究的焦點(diǎn)內(nèi)容來看,在考察犍陀羅美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的誕生、并包含佛像的犍陀羅雕刻應(yīng)是公元1世紀(jì)前半時(shí)期是最具有說服力的。法賽奈先生所謂的以“drawingstyle”進(jìn)行分類的大量作品其風(fēng)格并非一致,需要進(jìn)一步推測(cè)因時(shí)代的不同跨度而產(chǎn)生的異同,因此有必要對(duì)此進(jìn)行更為深入的探討。雖然,向來受希臘風(fēng)格影響頗深的佛教雕刻在犍陀羅雕刻遺品中看上去極為古老,但是,我們認(rèn)為值得關(guān)注的是,最初期的犍陀羅雕刻的樣式是希臘與印度古代初期的兩者美術(shù)傳統(tǒng)相融合之后在此地形成的。筆者曾撰寫《佛像的起源》一書,追溯至公元1世紀(jì)前半———中期,最初期的犍陀羅美術(shù)表現(xiàn)樣式,以裝飾紋樣、菩薩像、佛傳圖、佛陀的象征性表現(xiàn)以及佛陀像等分類考察,并以組像“梵天勸請(qǐng)”的浮雕雕刻為主說明了現(xiàn)存最早的佛像表現(xiàn)的形式。
薩伊特•夏利弗是與斯瓦特的布特卡拉Ⅰ號(hào)同樣重要的佛寺遺址,以法賽奈先生為首的意大利考古隊(duì)對(duì)此進(jìn)行了發(fā)掘,取得了巨大成果。薩伊特•夏利弗遺址位于距離布特卡拉Ⅰ號(hào)佛塔遺址1.5公里的丘陵地帶,它與布特卡拉Ⅰ號(hào)密切相關(guān)。薩伊特•夏利弗遺址是由西側(cè)的低地的主塔為中心的塔院,以及東側(cè)的開闊中庭地帶的方形僧院共同組同,是犍陀羅地區(qū)一般常見的伽藍(lán)配置范式。主塔的北側(cè)正面有階梯,方形基壇約20米,最初在方形基壇的四周有欄楯,方形基壇的四角有獅子形柱頭的圓柱,正面的階梯可供人攀登圓形基壇。最初,在圓形基壇的表面有佛傳浮雕的鑲嵌石板(豎45.5厘米,橫65厘米)總共60~65塊。遺憾的是,這里出土的佛傳浮雕幾乎全部是殘片了,但是,依然能從斷片中看出佛傳故事中比武競(jìng)技的諸場(chǎng)面呈現(xiàn)出的優(yōu)秀的石雕風(fēng)格。在圓形基壇的上部有兩層鼓腹的圓形建筑,底層部分還有帶狀裝飾和欄楯紋樣以及立柱裝飾。上層部分是覆缽形的平頂、傘蓋形式。正如上文所述,這樣宏偉的薩伊特•夏利弗主塔,小塔21、31、32、57號(hào),以及幢柱24、29號(hào)等是同期制作的,法賽奈先生從薩伊特•夏利弗出土的貨幣、碑銘書體等綜合性地判斷來看,將其確定為公元1世紀(jì)前半期或中葉創(chuàng)建的。主塔的圓形基壇以克林斯式柱頭的圓柱將其場(chǎng)面圍合起來,同時(shí),在圓形基壇四周有從誕生到涅槃的“釋尊的生涯”的連續(xù)式佛傳故事浮雕,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連續(xù)式佛傳浮雕的遺例。表現(xiàn)“釋尊的生涯”傳記的連續(xù)式佛傳故事與其說是印度的一個(gè)例外,不如說這是犍陀羅美術(shù)的一大特征,并對(duì)中國以及日本的佛傳美術(shù)表現(xiàn)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諸如這樣的傳記形式的佛傳表現(xiàn)的源流,在帕魯伽姆大祭壇的提萊福斯神話、描繪奧德賽斯故事的艾斯克伊里努斯山丘的繪畫,或者是羅馬紀(jì)念柱、凱旋門等歷史故事浮雕中可尋其蹤,希臘•羅馬的故事傳說表現(xiàn)來看的話,其中在這些故事中,并沒有描繪主人公的全部生涯故事。法賽奈是這樣論述的,唯一例外的是羅馬時(shí)代的鮑魯特安斯街道出土的克里奈葬禮浮雕為例,這里描繪了一個(gè)人從出生到死亡的人生主要事跡。從犍陀羅佛傳美術(shù)中的“釋尊的生涯”為故事表現(xiàn)的特征來看,雖然認(rèn)為這與希臘•羅馬的故事表現(xiàn)密切相關(guān),與其說與之具有直接的影響來說,不得不說這是“歷史化的意識(shí)”所依存的文化土壤的必然結(jié)果。塔德先生在承認(rèn)犍陀羅佛傳美術(shù)受希臘美術(shù)的滲透和影響的同時(shí),以立柱區(qū)隔畫面連續(xù)性地表現(xiàn)釋迦事跡,即所謂釋迦生涯的佛傳故事表現(xiàn),是犍陀羅工匠們將印度和希臘的傳統(tǒng)相結(jié)合的一大創(chuàng)舉。
法賽奈先生以薩伊特•夏利弗出土的佛傳浮雕為例,對(duì)其表現(xiàn)特征進(jìn)行了考察,對(duì)其造型表現(xiàn)力給予了極高的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在薩伊特•夏利弗的工房中應(yīng)有一批技藝高超的匠師。佛像橢圓形的臉寵、眼角微微上挑,陰刻手法表現(xiàn)的雙瞳以及鳥翼形特征的冠飾,具有健壯的身體、明快的肉體感的特征。另一方面,還可以明顯看到佛像的衣裙、天衣等以線條方式表現(xiàn)衣紋褶皺以及衣端規(guī)則性的鋸齒狀衣紋表現(xiàn)。另外,戰(zhàn)士的鎧甲、頭發(fā)、樹葉等也被精致地表現(xiàn)出來。這樣的樣式特征可以說是以布特卡拉Ⅰ號(hào)佛塔的初期樣式,也就是前文提到的“drawingstyle”為基礎(chǔ)發(fā)展而來的、更加具有現(xiàn)實(shí)感表現(xiàn)的造型樣式。基于法賽奈先生的考察成果,說明了薩伊特•夏利弗的佛傳浮雕的重要性。他認(rèn)為薩伊特•夏利弗的制作年代是繼布特卡拉Ⅰ號(hào)“drawingstyle”之后。另外,他根據(jù)考古學(xué)發(fā)掘的地質(zhì)層位、碑銘、出土貨幣等為基礎(chǔ),進(jìn)一步說明了其制作年代應(yīng)在公元1世紀(jì)前期或中期。但是,雖然說此處出土的貨幣數(shù)量極少,卻包含了貴霜王朝時(shí)期的貨幣,而貴霜王朝應(yīng)是1世紀(jì)后半建立的吧。薩伊特•夏利弗的佛傳浮雕的制作年代還有商榷之余地,它與布特卡拉Ⅰ號(hào)的浮雕雕刻共同成為意大利考古隊(duì)在斯瓦特地區(qū)發(fā)拙的關(guān)于犍陀羅雕刻初期表現(xiàn)樣式的閃光點(diǎn),可以說是近年來關(guān)于犍陀羅美術(shù)研究令人矚目的成果之一。正如前文所述,在斯瓦特的布特卡拉Ⅰ號(hào)發(fā)現(xiàn)了貴霜王朝以前的公元1世紀(jì)前半的佛傳圖中出現(xiàn)了佛陀像的有力說明,但是,此地出土的大量雕刻作品不足以成為編年的充分依據(jù)。對(duì)塔克西拉佛寺的變遷進(jìn)行詳細(xì)考察的桑山正進(jìn)先生,對(duì)犍陀羅佛寺的伽藍(lán)配置的變遷進(jìn)行考察研究的本瑞德,還有根據(jù)對(duì)出土貨幣狀況進(jìn)而對(duì)佛寺、佛像制作年代進(jìn)行研究的埃靈頓等諸位研究者認(rèn)為佛像的出現(xiàn)是在貴霜王朝以后。但是,無論誰都沒有對(duì)初期雕刻的表現(xiàn)樣式進(jìn)行詳細(xì)探討。多年以來結(jié)論最多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是在伽膩色伽即位年代,福格對(duì)此提示了紀(jì)元127年是最為有力的說明,眾多的研究者對(duì)此結(jié)論已認(rèn)可,在貨幣上雕刻佛像的唯一帝王———伽膩色伽時(shí)代,不難想象犍陀羅佛教雕刻迎來了極為隆盛的時(shí)期。貴霜王朝王位繼承和佛教信仰狀況的拉巴塔克碑文的解讀還存在不明確之處,公元1世紀(jì)的情況不明確之處存在很多。公元1世紀(jì)時(shí)期的犍陀羅佛寺、雕刻的表現(xiàn)形式的進(jìn)一步確定可以說是今后的學(xué)界課題之一。
三、東西方文化交流和犍陀羅美術(shù)
犍陀羅美術(shù)的一大特征就是由印度、希臘、羅馬、伊朗等美術(shù)傳統(tǒng)兼容并蓄形成的,這是由于它和西北印度的歷史有著很密切的關(guān)系。此地自從印度雅利安人入侵以來不管是從民族的還是語言方面來看印度文化已經(jīng)根深蒂固。一方面,6世紀(jì)前它是波斯阿契美尼德朝的屬地,公元1世紀(jì)前游牧民族塞種從阿富汗西北部起兵,侵入印度•希臘統(tǒng)治的犍陀羅地區(qū),更有貴霜王朝的游牧民族支配給這里帶來伊朗系文化。在美術(shù)表現(xiàn)方面給與犍陀羅很大影響的是希臘文化,也就是希臘精神。公元前4世紀(jì),亞歷山大王的東征之后,繼續(xù)統(tǒng)治東方的希臘塞硫古王朝,建立了希臘•巴克特利亞王國,這樣一系列的歷史關(guān)聯(lián),把希臘文化帶給了犍陀羅。在貴霜朝時(shí)代開始加速和羅馬世界的交流,于是推斷犍陀羅美術(shù)和伊朗、希臘、羅馬等美術(shù)要素兼容并蓄,誕生了全新的美術(shù)風(fēng)格———犍陀羅美術(shù)。在犍陀羅美術(shù)中可以看到印度風(fēng)格的主題圖像,圓形柱礎(chǔ)、欄楯、拱門等建筑主題。藥叉等民間信仰神之外,還有佛傳浮雕中的帝釋天、四天王、魔王等神,或者比丘、婆羅門、國王、居士、仙人、托缽行者等,這些形象表現(xiàn)了印度人的世界觀以及和社會(huì)有關(guān)系的人物。此外,犍陀羅地域還存在特殊信仰的鬼子母神,希臘神話中龍女、金翅鳥、女神等等。另一方面,說起希臘•羅馬風(fēng)格的圖像主體,克林斯式柱頭、葡萄唐草紋以及與狄奧尼索斯信仰有關(guān)聯(lián)的酒宴圖、舞會(huì)圖、男女飲酒圖、扛花環(huán)的童子、游戲的童子、海馬等海獸,雅典娜女神、支撐建筑物的阿特拉斯等枚不勝舉。再有,伊朗作為游牧民族起源的圖像,還有動(dòng)物形柱頭、狩獵圖,游牧民族像、娜娜女神像等。福契爾先生對(duì)犍陀羅美術(shù)中出現(xiàn)諸如上述所提到的各種各樣的美術(shù)圖像進(jìn)行了古典學(xué)研究并對(duì)此作了大致的分析。福契爾把犍陀羅美術(shù)冠之以“希臘式佛教美術(shù)”的稱名,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受希臘影響的結(jié)果。對(duì)此,英美的研究者提出了犍陀羅美術(shù)中看到的西洋古典要素特別是羅馬(帝政初期)美術(shù)的影響,或者是和這個(gè)相呼應(yīng)的東西這樣的見解。苯切斯?fàn)栂壬鷮⒐笠碌姆鹣窈痛┲b的羅馬皇帝像與太子樹下耕作圖像、石棺展現(xiàn)的耕作場(chǎng)面以及太子出城圖像和皇帝勝利后入城、凱旋而歸的圖像等等作了比較,考察了羅馬美術(shù)對(duì)犍陀羅的影響。還有,萊昂德先生認(rèn)為,在比馬蘭出土的黃金制的舍利容器上展示的佛像配置形式是2世紀(jì)的西達(dá)馬羅石棺以前所沒有的形式。或者說,希臘美術(shù)所具有的特征性表現(xiàn),如衣服使身體輪廓清楚地展現(xiàn)的表現(xiàn)力在犍陀羅佛像中并沒有被刻意表現(xiàn),犍陀羅的佛像衣飾透過身體展現(xiàn)出了獨(dú)立的量感,衣紋展示出窗簾狀那樣下垂平行有深度的雕刻,這樣的表現(xiàn)與1世紀(jì)至3世紀(jì)初的羅馬美術(shù)樣式比較接近。此外,還有包括維爾在內(nèi)的羅馬美術(shù)影響的研究者認(rèn)為在犍陀羅美術(shù)中看到的西方影響來自于貴霜王朝時(shí)代的海上貿(mào)易。
相對(duì)于“希臘式佛教美術(shù)”對(duì)“羅馬式佛教美術(shù)”的論考,以犍陀羅美術(shù)的年代論為視角,犍陀羅美術(shù)和羅馬美術(shù)之間的確存在屢屢平衡的關(guān)系,可是,對(duì)兩者進(jìn)行比較后,不得不說決定制作年代相對(duì)困難。還有一個(gè)問題是,無論是“希臘式佛教美術(shù)”還是“羅馬式佛教美術(shù)”這樣的稱呼,就把伊朗、印度等要素等于全部放手了,犍陀羅的人們將多樣的要素進(jìn)行選擇性地接受,更加把它們進(jìn)行融合,形成了稱之為“犍陀羅美術(shù)”這樣的視點(diǎn)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犍陀羅美術(shù)和羅馬美術(shù),還有對(duì)初期的基督教美術(shù)進(jìn)行比較分析,也是很值得研究的課題,可以說應(yīng)該做詳細(xì)的個(gè)別考察課題,遺憾的是,之后這樣的觀點(diǎn)研究活動(dòng)并沒有進(jìn)行下去。犍陀羅美術(shù)是在活躍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基礎(chǔ)上誕生發(fā)展起來的,這樣認(rèn)為的話,那么就要再一次回到原點(diǎn)檢證犍陀羅美術(shù)的多樣性圖像主題的同時(shí),有必要明確對(duì)選擇性接受的做法和其意義的認(rèn)可。“影響”這個(gè)詞使用方便,因?yàn)檫@個(gè)失去對(duì)犍陀羅美術(shù)獨(dú)有的特點(diǎn)的見解是不行的。相對(duì)于“影響”來說使用“吸收”或更為合適吧。以選擇性的吸收和發(fā)展的視點(diǎn)為前提,尤其在考慮犍陀羅美術(shù)問題上是極其重要的。我們?cè)诳紤]犍陀羅美術(shù)之際,對(duì)于探究其早期歷史來說,此地出土的化妝盤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塔克西拉的西爾卡普出土了近60件,還有出土地不明的化妝盤也占多數(shù)(大多在西北印度地區(qū)出土)。現(xiàn)在所被知道的達(dá)到200件以上。化妝盤一般的直徑有10~20厘米的大小,石材選擇凍石或者千枚巖,還有片巖,中心面凹進(jìn)去,四周突出來。內(nèi)面刻有各種題材的圖案的花紋。也有凹面全體施行雕刻的,大概都在上部占3/4部分雕刻著圖案,剩下的部分不是空白的原樣,就是雕刻著蓮花紋和幾何紋樣。自從苯切斯?fàn)栂壬鷮⑦@樣的石制圓形小盤稱之為“化妝盤”以來,這個(gè)名稱被廣泛地普及起來,實(shí)際上怎樣使用它并不明確。只是,那里展示出的主題和圖像幾乎都是神格化的宗教的圖像有關(guān)的這一點(diǎn)來看,化妝盤不是世俗的道具,大概是具有宗教功能的奉納物或者祭祀用的用具等,總之帶有宗教性用途吧。
塔德先生以貝格拉姆出土的表現(xiàn)蓮花化生的三人組的人物像的化妝盤為例,考察說明了化妝盤與地中海地區(qū)宗教世界的關(guān)系。在這個(gè)化妝盤上中心雕刻了從蓮花上出現(xiàn)上半身的三個(gè)人物形象,中央一人雙手合掌,其他二人手舉酒杯。從中央畫面向四方畫面延伸著蓮瓣圖案,四角部位雕刻盛開的花卉紋樣。塔德認(rèn)為,中央畫面表現(xiàn)的是宗教性獻(xiàn)酒場(chǎng)面,其中一個(gè)頭戴帽子的人物表明這與密特拉信仰有關(guān)。福萊克特先生將塔克西拉考古博物館、白沙瓦博物館以及歐洲博物館收藏品為主的96件化妝盤為例,記錄這些作例的基礎(chǔ)數(shù)據(jù),并對(duì)它們的圖像樣式進(jìn)行分類,探討它們的制作由來以及年代排序等問題。關(guān)于化妝盤的斷代問題,馬歇爾根據(jù)希爾卡普的發(fā)掘成果為基礎(chǔ),將化妝盤斷定為三期,分別為印度•古里克、印度•塞種、印度•帕提亞三個(gè)時(shí)期,是屬于公元前2世紀(jì)中期到公元1世紀(jì)中期制作的。結(jié)論是貴霜王朝時(shí)期幾乎沒有再制作。另一方面,達(dá)瑞先生將塔克西拉考古博物館所藏的57件化妝盤,另外還有拉合爾博物館、斯瓦特博物館、白沙瓦博物館、卡拉奇博物館、新德里博物忱、大英博物館、維克特里亞博物館的藏品等,共計(jì)對(duì)123件化妝盤進(jìn)行了圖錄記錄。達(dá)瑞先生研究指出,關(guān)于這些化妝盤的出土地來看,大多來自于都市遺跡所在地,而佛寺出土的件數(shù)卻極為有限,并且認(rèn)為其制作年代,以希爾卡普遺跡的發(fā)掘成果為基礎(chǔ)來看,應(yīng)是在印度•古里特至貴霜王朝時(shí)期。圖像主題來自于祖先崇拜、太陽信仰,更多的是和狄奧尼索斯信仰有關(guān),所以,化妝盤并不是單純的裝飾品或化妝用具,而是宗教儀禮上的使用之物。達(dá)瑞先生認(rèn)為,貴霜王朝時(shí)期佛教的隆盛、同時(shí)急速地衰敗,是因?yàn)榈見W尼索斯信仰取代了佛教信仰,并且是在這種信仰影響下對(duì)“貴霜王朝統(tǒng)治的佛教”的滲透并反映在政治和藝術(shù)上。上述兩位研究者雖然開拓了關(guān)于化妝盤研究的端緒,但對(duì)其宗教意味以及與佛教的關(guān)系并沒有進(jìn)行深入的考察探討。筆者更為重視的是化妝盤的圖像顯示了犍陀羅佛教美術(shù)的成立、發(fā)展的宗教性土壤,并將之與中印度的窣堵坡信仰土壤中的圣樹、藥叉信仰進(jìn)行對(duì)比考察研究。也就是說,窣堵坡是釋迦到達(dá)涅槃、即超越輪回的“永恒世界”的象征,而對(duì)于世俗的佛教信仰者們來說,圣樹信仰所具有的生命力是與之具有同等功能的信仰之物。因此,初期的窣堵坡的欄楯、拱門等部位都雕刻著象征生命力的枝繁葉茂的植物主題圖案紋樣(如蓮花、蓮花蔓草、滿瓶、象、曼陀羅等)、主司豐饒多產(chǎn)的神格等的浮雕圖案。
化妝盤所表現(xiàn)的圖像有“死者的盛宴”、“騎海獸的人物”、“酒醉的狄奧尼索斯”以及“酒宴的男女”等豐富多彩,這些圖像表達(dá)的是人們?yōu)樗篮蟮膬舾F碓福瑸樗勒叩撵`魂往生之旅的再生,接受了這些喚起人們對(duì)往生世界憧憬的主題圖像。特別是與狄奧尼索斯信仰有關(guān)的圖像更為顯著,對(duì)于體現(xiàn)了“永恒的永生”信仰意味,與中印度的圣樹信仰相呼應(yīng)。在犍陀羅也許就會(huì)出現(xiàn)這樣的、表現(xiàn)男女人物騎乘太陽神戰(zhàn)車、飛向天界之旅圖像的化妝盤。筆者在下文中將介紹田邊先生對(duì)化妝盤研究的成果,他對(duì)犍陀羅化妝盤的研究著述頗豐。田邊先生將日本個(gè)人所藏的化妝盤收集起來舉辦了展覽會(huì),并以此為契機(jī)發(fā)表了關(guān)于化妝盤的引人注目的研究論考。文中他積極評(píng)價(jià)了化妝盤所具有的宗教功能,并對(duì)化妝盤的圖像進(jìn)行了系統(tǒng)考察研究。目前為止,僅在一件化妝盤上發(fā)現(xiàn)了“梵天勸請(qǐng)”的圖像,沒有看到其他佛教主題圖像。而向來認(rèn)為化妝盤是與佛教無關(guān)的異宗教、異文化的產(chǎn)物,但是,據(jù)田邊先生研究表明,他認(rèn)為化妝盤是居住在都市里的希臘系俗家佛教徒———也就是希臘人以外的佛教徒廣為使用的一種家庭用禮拜器物,據(jù)說其圖像具有到達(dá)彼岸極樂往生世界的具體意義。到了貴霜王朝時(shí)期,隨著佛像制作的一般化,取而代之了化妝盤,從而引起化妝盤急速衰減。依田邊先生所言,這是因?yàn)榉鹣袷菙y帶信者的靈魂到達(dá)極樂往生世界的引導(dǎo)者,也就是說佛像具有偉大的救世主的功能,佛像從而就取代了化妝盤上的圖像。田邊先生觀點(diǎn)的基礎(chǔ)是將化妝盤以及犍陀羅雕刻中各種各樣的圖像主題納入一個(gè)整體視野中進(jìn)行考察的。他認(rèn)為海獸、海神、冥界中的各種神以及童子、海妖圖像等,表現(xiàn)了希臘人“認(rèn)為海代表死亡的世界”的觀念,以魔物或半人半獸的形象是將海的各種各樣的自然現(xiàn)象進(jìn)行造型化的結(jié)果,他解釋說騎著海神、海馬、海獸前往海上樂園之島的場(chǎng)景象征的是死者到達(dá)往生世界的靈魂之旅。
田邊先生認(rèn)為將狄奧尼索斯、阿里阿德奈、薩狄羅斯、西來努斯、男女飲酒圖、圖等納入雕刻作品中,以圖豐腴的肉體表現(xiàn)來體現(xiàn)對(duì)靈魂的解放,在永恒世界中永存的狄奧尼索斯神的秘儀相關(guān)的圖像,可以看出,相對(duì)于佛教來說,體現(xiàn)了從束縛中解脫、得到自由,所謂涅槃———到達(dá)往生世界的意味。田邊先生認(rèn)為,佛塔圓拱處的佛立像與同樣位于圓拱處的男女圖共同上下表現(xiàn)在浮雕雕刻中,揭示了積善功德的佛教徒在佛陀的助力下、圖暗示了他們可以到達(dá)往生極樂世界的圖像含義。依田邊先生所言,他認(rèn)為犍陀羅雕刻中所見的男女飲酒圖、交歡圖中,因?yàn)閻塾挥兴窒蓿詧D并沒有象印度密特拉像那樣象征著豐饒、吉祥之寓意,而是極樂世界或天國之窗的象征。田邊先生的論考認(rèn)為,化妝盤上的圖像是佛教圖像,以及認(rèn)為它是來自希臘的圖像主題而且向來作為犍陀羅佛教美術(shù)中裝飾功能而被運(yùn)用,具有積極的佛教上的意味之物是其最大的特征。田邊先生的考察非常具有啟示性,對(duì)于化妝盤是否是希臘佛教徒的信仰對(duì)象,筆者認(rèn)為化妝盤應(yīng)是犍陀羅地區(qū)的民眾(包括希臘、塞種、帕提亞、印度)對(duì)希臘精神文化選擇性吸收演變之后的信仰產(chǎn)物,在此,應(yīng)該考慮它是否與佛教有直接的關(guān)系。因此,化妝盤作為考察犍陀羅美術(shù)的前史以及初期樣式將是今后需要探討的重要問題之一。
希臘精神傳來的圖像主題可以確定在貴霜王朝時(shí)期的佛教美術(shù)中就已經(jīng)被運(yùn)用了,根據(jù)卡特先生研究證明,特別是狄奧尼索斯信仰有關(guān)的圖像在貴霜王朝時(shí)期大受歡迎。狄奧尼索斯信仰與佛教具有不同的信仰集團(tuán),男女酒宴圖、交歡圖進(jìn)入佛教圖像中的例子,如桑奇大塔第一塔門浮雕上所那樣,表現(xiàn)了印度豐饒多產(chǎn)和樂園的象征以及人的靈魂進(jìn)入天堂的圖像意味。同時(shí),諸如上述這種異教圖像主題在佛教寺院中究竟被應(yīng)用到什么位置,是我們必需要考慮的。除人物像以外表現(xiàn)最多的應(yīng)是有關(guān)海獸的題材,海馬、下半身作魚尾的海獸,還有長(zhǎng)翼的海獸等主題圖像,都被運(yùn)用于裝飾佛塔臺(tái)階的側(cè)面或下端等位置。狄奧尼索期信仰有關(guān)的男女飲酒圖、歌舞奏樂圖等大多都被用于臺(tái)階表面的裝飾。另外,在獸腳座上也有一些男女飲酒圖和歌舞奏樂圖,這些都被運(yùn)用到佛塔臺(tái)階最下面的左右側(cè)面呈對(duì)配置。連續(xù)的男女交歡圖或者是與佛陀像交互配置在臺(tái)階部位橫長(zhǎng)形狀石板上,被運(yùn)用到祠堂的入口處。由此可見,狄奧尼索斯信仰并不排斥佛教,積極地吸納接了佛教,對(duì)佛教的受容方式是逐層遞進(jìn)的,異教的主題圖像被運(yùn)用到佛塔的邊緣部位,起到引導(dǎo)走向中心佛教世界的這樣一種圖像構(gòu)成和功能作用。正如上文所述,在希臘圖像對(duì)佛教美術(shù)的滲透和影響之下,那么,佛塔、祠堂、僧院等建筑物中浮雕雕刻是如何被配置的呢?以及與佛傳浮雕、菩薩像是如何被組合在一起的呢?以上這些視點(diǎn)都有必要進(jìn)行更深入的探索。同時(shí),對(duì)佛塔整體圖像學(xué)的解讀、佛教寺院整體裝飾方式與佛教主題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以及其意義、功能等諸多問題都有必要進(jìn)行解明,這是犍陀羅美術(shù)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對(duì)此問題的探討,不僅要考慮希臘系圖像,還要將伊朗系、印度系(民間信仰、印度教)圖像納入在內(nèi)一并進(jìn)行研究將是最佳途徑和方法。因?yàn)椋恿_新的尊像樣式以及美術(shù)表現(xiàn)形式的多樣化是因異文化的兼融并蓄而促成的,應(yīng)該說這一點(diǎn)是重要的問題所在。對(duì)此問題的探討,就要包括對(duì)佛傳圖、佛像、菩薩像、佛三尊像以及與大乘佛教的關(guān)聯(lián)等全方面進(jìn)行考慮,就此問題筆者將另稿論述。
作者:宮治昭單位:敦煌研究院文獻(xiàn)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