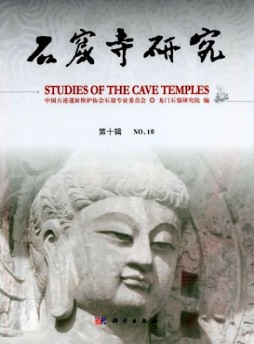石窟藝術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石窟藝術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北魏造像迎漢化
秀骨清像至為上到了北魏孝文帝時期,佛教造像上的漢化體現得更加明顯。孝文帝為了加強對北方的統治,穩定漢族民心,制定了一系列以漢文化為主導的政策,如,規定鮮卑人改穿體現漢族風格的服裝,推廣漢語以統一語言文字,學習漢文化及漢民俗,允許漢人與鮮卑人通婚,等等。這些措施不僅有利于北魏孝文帝的統治,更促進了民族大融合進程,在穩定了政權的同時促進了社會藝術文化的發展。與此同時,佛教造像的世俗性特征更加明顯了。此外,北魏孝文帝還選取了一些漢族人士作為朝廷重臣治理國家,間接地將一些漢文化帶入宮廷,這對其后來的文化統治有著重大影響。在藝術上,北魏漢化的結果是引進了南朝畫家陸探微所創立的“秀骨清像”的圖式。與此同時,麥積山石窟的佛教造像總體特征表現出了一種超凡脫俗的南朝風格之美,北方鮮卑游牧民族所推崇的雄偉大氣、深厚凌然之風逐漸被代替,轉為崇尚和顏悅色、軀體袖長、飄逸灑脫的“秀骨清像”的造像。佛像造型除了開始表現出以瘦為美的氣質,其面部表情特征也發生了變化,“微笑之風”盛行,更注重對人性的表達,東晉顧愷之的“以形寫神”等藝術理論也被應用于佛教造像的表現。創作者開始注重對造像神態的表達,用世俗的形式突顯佛教造像擬人化的神態,一改過去佛教造像的莊嚴肅穆、威武大氣之風,增添了一些瀟灑脫俗的類似文人墨客形象的風格。這種特征在麥積山石窟第121窟和第133窟的佛教造像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在第121窟一尊弟子與菩薩像中,佛弟子與菩薩身體緊靠一起,似在竊竊私語,頗具人間氣息;菩薩的表情慈祥而不失莊重,佛弟子微笑地傾斜著身體,似在向菩薩取經,其崇敬之心溢于言表。而在第133窟的弟子像中,佛弟子頭微低,露出會心的微笑,其身著寬大的袈裟,衣紋簡潔質樸,造像人物的神情表達和衣飾都極為細膩。由此可見,此時麥積山石窟的佛教造像應用了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使其更富有民間世俗氣息,不再是一種佛教程式化的藝術。這種佛教造像的表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國的佛教文化漸漸地有了漢文化的特色,不再完全是外來佛教的特點。
二、清風微笑吹西魏
珠圓玉潤話北周到了西魏時期,除了延續著北魏“秀骨清像”的風格之外,佛像呈現出美麗、善良的母性形象。在麥積山石窟第54窟一尊佛與菩薩的造像中,佛坐在中央,通肩袈裟簡練單純,身體造型完整,兩旁的菩薩同樣造型簡練而面部神情突出。其臉多呈橢圓狀,慈眉秀目,身披具有漢文化風格的袈裟,且繼承了北魏的“微笑之風”,尤顯親切,仿佛不再是威嚴肅穆的佛,而是瀟灑脫俗、富有生活氣息的智者。南朝清新優雅的藝術風格也在西魏時期的麥積山佛教造像上一覽無余。而西魏后期,佛教造像的臉部刻畫不再是南朝的“秀骨清像”之風,取而代之的是豐滿而顯喜態的面相,這與秣陀羅藝術風格不完全相同,是西魏后期獨有的藝術特色——從清瘦淡雅的形象轉變為體態豐潤、面部豐滿的特征。如麥積山石窟第123窟中的男女侍童造像,童男和童女的造型刻畫頗為天真可愛,二者相立而站,面部刻畫憨厚樸實、天真爛漫,既有中國古典審美的含蓄之風,又帶有自然親切的生活氣息,展現了一種從童真稚氣洋溢而出的虔誠與自信。這種珠圓玉潤的造像風格影響了之后北周的造像創作。如麥積山石窟第135窟中的泥塑小佛,其造像風格延續了西魏的“珠圓玉潤”之風,南朝的“秀骨清像”的風格已漸漸淡化;泥塑小佛的造像體態豐滿圓潤,面部為童子面貌,稚氣爛漫,仿佛刻畫的是一位鄰家少童,已看不出是與佛教造像有關的素材。這種創作在北周時期非常之多,其世俗性特征一覽無余。而這種“珠圓玉潤”的風格也影響了唐代的審美傾向與藝術風格。因此,從佛教造像風格的變化上也能表現出當時社會的藝術審美趣味,佛教造像已不僅僅是一種信仰崇拜的表現,更多地展現了人們對于雕塑藝術的審美追求。這種世俗化的佛教造像已成為中國古典藝術審美的有力論證,體現的是一種文化多元性的衍變過程,內容豐富,具有探索性。
作者:潘沛單位:南京藝術學院藝術學研究所
第2篇
安岳石窟造像始鑿于唐,而盛于宋,其藝術風格在借鑒融合的漸變過程中,由最初的質樸的程式化構圖形式逐漸發展,自成體系,藝術表達形式更加多元化,在中國的石窟藝術中被稱為“上承敦煌、云崗、龍門石窟,下啟大足石窟”。
(一)題材多樣安岳的兩萬多軀造像中
觀音造像題材多樣,主為顯教觀音、密宗的千手觀音、華嚴三圣、觀音經變等。唐朝以顯教觀音和密教千手觀音為主,其中臥佛院第45號11面千手觀音最具特色,造像身高135厘米,呈立姿,分三層排列,身前兩臂雙手合十,身后有四陰刻千手掌,掌心各有一眼,在觀音左右手下方有一窮叟手持口袋接錢狀、一夜叉作懼怕狀,此題材與《大正藏》《十一面神咒心經》等經中所言均不相符合,有著地方特色。五代時期的觀音造像較少,題材主為觀音和千手觀音,最具特色的是圓覺洞內的第21號龕的千手觀音經變相和59號龕內西方三圣左側的觀音造像,其中圓覺洞千手觀音有四十只手,跣足善跏趺坐于雙層仰蓮瓣蓮臺之上,左右兩側上方有十方佛坐于祥云中,下有夜叉、窮叟、吉祥仙女、婆藪仙。進入宋代,隨著造像的繁盛,題材逐漸多樣,有毗盧洞的水月觀音(又叫紫竹觀音)、千佛寨的觀音菩薩像,圓覺洞的寶瓶觀音和蓮花手觀音、華嚴洞的辨音觀音等。宋代題材逐漸豐富,雕刻者在佛教題材上進行自我創作發揮,其規模較大,尤其是毗盧洞第19號的觀音經變窟,其“紫竹觀音”坐于鋪有蒲葉之石上,背景為普陀山紫竹林,左右兩側壁刻有八難圖,在四川尚屬首例。
(二)龕形各異唐代造像布局基本以單龕為主
單口略呈弧形,龕內以主尊為中心,兩側對稱構圖,同時匠師又利用兩側的動態、法器等變化打破對稱的板滯構成,追求自然與和諧;五代時期造像規模較小,主為平頂雙重龕;宋代時期造像窟龕形單一,主為方形(或矩形)平頂窟(龕),平面呈方形,三面墻壁基本刻有造像,也有三壁鑿壇,其上設像。
(三)雕刻精湛安岳石窟觀音刀法圓潤
衣紋裝飾追求質感,講究衣紋轉折起伏。雕刻師充分利用造像體、面、線的關系,將細密繁瑣的衣紋和瓔珞與整體構圖協調統一,為造像增添了豐富的層次和色彩感。到了唐代,匠師在單龕造像細部采用線、面結合的雕刻手法,以半圓雕為主,輔之以淺浮雕和線刻,更是借助線條對衣著進行疏密轉折、形體特點的藝術表達。進入宋代,安岳石窟造像在唐、五代對川北石窟的借鑒融合基礎上,逐漸進入自成一脈的成熟期。布局更具代表性,此時期匠師已突破了前期布局,在對稱、均衡、和諧基礎上,追求大小、高低、起伏、疏密等變化,這種融合線條的雕刻體現出了一種韻律之美。
(四)塑造細膩安岳石窟觀音造像造型獨特
形象刻畫細膩,藝術語言簡練、寫實,其形象塑造既符合時代審美特征,又借鑒融合中有了濃厚的地方特色,其神性逐漸減弱,世俗性逐漸增強。唐朝佛教盛行,造像相對較多,造像風格保留了唐代的審美基調。綜觀其安岳唐代觀音造像,其基本是體態圓潤豐盈,高貴端莊,大多身著半臂式天衣,下著羊腸大裙,跣足立于三層仰蓮瓣蓮臺,面頰飽滿,下頜豐圓,兩眼半閉,眉骨、顴骨低平,細眉小口,耳廓下垂,頸部粗短有二道蠶紋。由此可見,唐代觀音造像造型細膩中又透露出唐代的雍容華貴之風姿。此外,唐朝時期觀音造像與以往造像有所區別,不再是印度佛教之像,已具有中國味道的人性美。如華嚴洞高冠觀音依據女皇武則天身形雕刻,體態既有唐人特有的豐滿圓潤,又有女皇的高貴端莊,氣質神態既融入了審美要求又融進了親近和藹的人性,將神性與人性達到了和諧統一。
二、安岳石窟佛教觀音造像藝術風格及審美特點
(一)造型之美所謂造型之美
即指觀音的形體、結構、裝飾的美。安岳石窟佛教造像中的觀音造像符合了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和審美觀念,每一造像傳神逼真、雕刻技藝出神入化,觀音情態讓審美主體心境如水,喚起種種美的意象。首先,安岳石窟觀音造像人物比例勻稱,面部神態刻畫寫實傳神,肌膚豐腴細膩,整體形象逼真傳神、端莊典雅。觀音形體美在于雕刻者動靜結合的藝術表達,憑借優美的曲線、氣質姿態將靜態觀音涌動出內在激情,營造出動態柔靜和諧之美。其次,為了突出形象之美,把裝飾重點轉移到觀音衣飾、寶冠及手印、手中執物等衣飾器上,雕刻之精美復雜,刀法洗煉,有較強的質感且式樣繁多。特別是觀音寶冠,多為鏤空化佛花冠,造型結構簡單中不失精美,花冠中央有形式多樣跏趺坐于蓮花座的化佛,以化佛為中心,卷草紋、寶相紋等蔓形植物呈鏤空狀紋對稱加以裝飾,這是印度佛教雕刻及中國其他石窟藝術中所不能比擬的。最后,采用象征、暗喻藝術表現手法,在濃厚寫實性、人性化基礎上,突出神性特征,使觀音造像更加形象、更富有神性魅力,以此吸引大批信眾,如雕刻者借用服飾、手印、坐式、臺座等帶有一定象征意義的佛教物品與當地特色相融合。
(二)世俗之美世俗之美即為神性與人性相結合
追求現實審美情趣,逐漸走向世俗化,呈現出一種美的特質。觀音造像的流變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且與女性崇拜心理、官方的介入和儒釋文化的融合息息相關。佛教在中國流傳不僅在道義中滲透中國觀念,也在造像上不斷發生變化。安岳石窟觀音造像雕刻者脫離了宗教藝術的特定要求,采用寫實手法來表現這些觀音菩薩形象,雕刻中既融入了“人性”的表達又兼顧到“神性”形象,甚至脫離神的味道,對現實生活審美趣味逐漸加濃,走向世俗化。尤其是毗盧洞的“紫竹觀音”,從造像形象來看,善良慈愛中透露著幾分灑脫和開朗,具有世俗的翹腳側坐更是打破了觀音正襟危坐的定性,儼然像一個灑脫俏皮的四川姑娘,反映出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主觀的具體化和客觀的人文主義化的思想,使紫竹觀音構成了現實人性和理想佛性的的自然融合及神人合一審美追求。
(三)韻律之美安岳石窟佛教觀音造像最大的特點
第3篇
安岳石窟造像始鑿于唐,而盛于宋,其藝術風格在借鑒融合的漸變過程中,由最初的質樸的程式化構圖形式逐漸發展,自成體系,藝術表達形式更加多元化,在中國的石窟藝術中被稱為“上承敦煌、云崗、龍門石窟,下啟大足石窟”。
(一)題材多樣
安岳的兩萬多軀造像中,觀音造像題材多樣,主為顯教觀音、密宗的千手觀音、華嚴三圣、觀音經變等。唐朝以顯教觀音和密教千手觀音為主,其中臥佛院第45號11面千手觀音最具特色,造像身高135厘米,呈立姿,分三層排列,身前兩臂雙手合十,身后有四陰刻千手掌,掌心各有一眼,在觀音左右手下方有一窮叟手持口袋接錢狀、一夜叉作懼怕狀,此題材與《大正藏》《十一面神咒心經》等經中所言均不相符合,有著地方特色。五代時期的觀音造像較少,題材主為觀音和千手觀音,最具特色的是圓覺洞內的第21號龕的千手觀音經變相和59號龕內西方三圣左側的觀音造像,其中圓覺洞千手觀音有四十只手,跣足善跏趺坐于雙層仰蓮瓣蓮臺之上,左右兩側上方有十方佛坐于祥云中,下有夜叉、窮叟、吉祥仙女、婆藪仙。進入宋代,隨著造像的繁盛,題材逐漸多樣,有毗盧洞的水月觀音(又叫紫竹觀音)、千佛寨的觀音菩薩像,圓覺洞的寶瓶觀音和蓮花手觀音、華嚴洞的辨音觀音等。宋代題材逐漸豐富,雕刻者在佛教題材上進行自我創作發揮,其規模較大,尤其是毗盧洞第19號的觀音經變窟,其“紫竹觀音”坐于鋪有蒲葉之石上,背景為普陀山紫竹林,左右兩側壁刻有八難圖,在四川尚屬首例。
(二)龕形各異
唐代造像布局基本以單龕為主,單口略呈弧形,龕內以主尊為中心,兩側對稱構圖,同時匠師又利用兩側的動態、法器等變化打破對稱的板滯構成,追求自然與和諧;五代時期造像規模較小,主為平頂雙重龕;宋代時期造像窟龕形單一,主為方形(或矩形)平頂窟(龕),平面呈方形,三面墻壁基本刻有造像,也有三壁鑿壇,其上設像。
(三)雕刻精湛
安岳石窟觀音刀法圓潤,衣紋裝飾追求質感,講究衣紋轉折起伏。雕刻師充分利用造像體、面、線的關系,將細密繁瑣的衣紋和瓔珞與整體構圖協調統一,為造像增添了豐富的層次和色彩感。到了唐代,匠師在單龕造像細部采用線、面結合的雕刻手法,以半圓雕為主,輔之以淺浮雕和線刻,更是借助線條對衣著進行疏密轉折、形體特點的藝術表達。進入宋代,安岳石窟造像在唐、五代對川北石窟的借鑒融合基礎上,逐漸進入自成一脈的成熟期。布局更具代表性,此時期匠師已突破了前期布局,在對稱、均衡、和諧基礎上,追求大小、高低、起伏、疏密等變化,這種融合線條的雕刻體現出了一種韻律之美。
(四)塑造細膩
安岳石窟觀音造像造型獨特,形象刻畫細膩,藝術語言簡練、寫實,其形象塑造既符合時代審美特征,又借鑒融合中有了濃厚的地方特色,其神性逐漸減弱,世俗性逐漸增強。唐朝佛教盛行,造像相對較多,造像風格保留了唐代的審美基調。綜觀其安岳唐代觀音造像,其基本是體態圓潤豐盈,高貴端莊,大多身著半臂式天衣,下著羊腸大裙,跣足立于三層仰蓮瓣蓮臺,面頰飽滿,下頜豐圓,兩眼半閉,眉骨、顴骨低平,細眉小口,耳廓下垂,頸部粗短有二道蠶紋。由此可見,唐代觀音造像造型細膩中又透露出唐代的雍容華貴之風姿。此外,唐朝時期觀音造像與以往造像有所區別,不再是印度佛教之像,已具有中國味道的人性美。如華嚴洞高冠觀音依據女皇武則天身形雕刻,體態既有唐人特有的豐滿圓潤,又有女皇的高貴端莊,氣質神態既融入了審美要求又融進了親近和藹的人性,將神性與人性達到了和諧統一。
二、安岳石窟佛教觀音造像藝術風格及審美特點
(一)造型之美
所謂造型之美,即指觀音的形體、結構、裝飾的美。安岳石窟佛教造像中的觀音造像符合了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和審美觀念,每一造像傳神逼真、雕刻技藝出神入化,觀音情態讓審美主體心境如水,喚起種種美的意象。首先,安岳石窟觀音造像人物比例勻稱,面部神態刻畫寫實傳神,肌膚豐腴細膩,整體形象逼真傳神、端莊典雅。觀音形體美在于雕刻者動靜結合的藝術表達,憑借優美的曲線、氣質姿態將靜態觀音涌動出內在激情,營造出動態柔靜和諧之美。其次,為了突出形象之美,把裝飾重點轉移到觀音衣飾、寶冠及手印、手中執物等衣飾器上,雕刻之精美復雜,刀法洗煉,有較強的質感且式樣繁多。特別是觀音寶冠,多為鏤空化佛花冠,造型結構簡單中不失精美,花冠中央有形式多樣跏趺坐于蓮花座的化佛,以化佛為中心,卷草紋、寶相紋等蔓形植物呈鏤空狀紋對稱加以裝飾,這是印度佛教雕刻及中國其他石窟藝術中所不能比擬的。最后,采用象征、暗喻藝術表現手法,在濃厚寫實性、人性化基礎上,突出神性特征,使觀音造像更加形象、更富有神性魅力,以此吸引大批信眾,如雕刻者借用服飾、手印、坐式、臺座等帶有一定象征意義的佛教物品與當地特色相融合。
(二)世俗之美
世俗之美即為神性與人性相結合,追求現實審美情趣,逐漸走向世俗化,呈現出一種美的特質。觀音造像的流變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且與女性崇拜心理、官方的介入和儒釋文化的融合息息相關。佛教在中國流傳不僅在道義中滲透中國觀念,也在造像上不斷發生變化。安岳石窟觀音造像雕刻者脫離了宗教藝術的特定要求,采用寫實手法來表現這些觀音菩薩形象,雕刻中既融入了“人性”的表達又兼顧到“神性”形象,甚至脫離神的味道,對現實生活審美趣味逐漸加濃,走向世俗化。尤其是毗盧洞的“紫竹觀音”,從造像形象來看,善良慈愛中透露著幾分灑脫和開朗,具有世俗的翹腳側坐更是打破了觀音正襟危坐的定性,儼然像一個灑脫俏皮的四川姑娘,反映出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主觀的具體化和客觀的人文主義化的思想,使紫竹觀音構成了現實人性和理想佛性的的自然融合及神人合一審美追求。
(三)韻律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