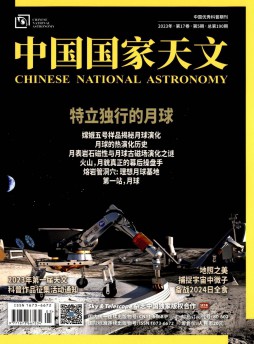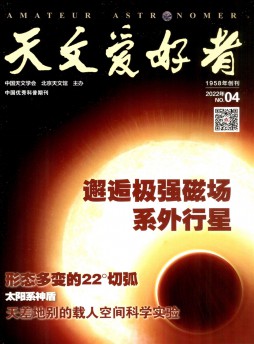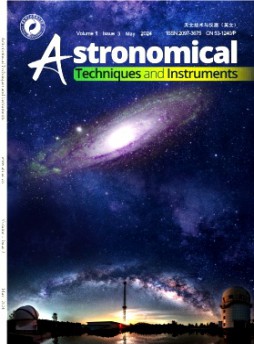天文歷法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天文歷法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王廷相是明代中葉重要儒家學(xué)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為己任,指出:“儒者之論,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則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異學(xué)也,則辨而正之,斯善學(xué)道者也。”[ ]他還根據(jù)孔子所言“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時(shí),他明確主張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問”中說:
諸士積學(xué)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yùn),何以機(jī)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cè)?經(jīng)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為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為鴽,而鴽復(fù)為鼠?何蜣螂化蟬,而蟬不復(fù)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fēng)而自搖?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溫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yīng)也何故?引針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習(xí)矣而不察也。請據(jù)其理之實(shí)論之。[ ]
顯然,王廷相是主張研究各種自然現(xiàn)象、研究科學(xué)的。而且他還認(rèn)為,研究天地之道是學(xué)者“窮理盡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說:
古之圣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內(nèi)外,彌滿于無垠,周匝于六合,茍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悠遠(yuǎn)高深,學(xué)者不可不求其實(shí)矣。[ ]
王廷相不僅主張研究自然,同時(shí)自己也廣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學(xué)。在天文學(xué)上,他進(jìn)行過大量的天文觀測,主張渾蓋合一論,并且通過對渾天說與蓋天說的優(yōu)點(diǎn)加以綜合,以解釋各種天文現(xiàn)象;他還專門研究了古代天文學(xué)上的“歲差”概念的發(fā)展,撰有《歲差考》。[ ]
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講經(jīng)世致用,與此相聯(lián)系,他們也極力推崇科學(xué),主張研究科學(xué),包括研究天文學(xué)。
顧炎武對當(dāng)時(shí)的王學(xué)末流提出批評。他說:“不習(xí)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dāng)代之務(wù),舉夫子論學(xué)、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shí)學(xué)。”[ ]顧炎武認(rèn)為,王學(xué)末流清談“明心見性”之類,實(shí)際上是棄“修己治人之實(shí)學(xué)”,其結(jié)果是“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
顧炎武所謂的“修己治人之實(shí)學(xué)”,就是“博學(xué)于文”、“行己有恥”。關(guān)于“博學(xué)于文”,顧炎武說:
君子博學(xué)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shù),發(fā)之為音容,莫非文也。[ ]
顧炎武講的“博學(xué)于文”,當(dāng)然也包括研究科學(xué)。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十余卷“凡經(jīng)義史學(xué)、官方吏治、財(cái)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證其謬誤”[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識(shí)。《日知錄》第30卷“論天象數(shù)術(shù)”,有《天文》、《日食》、《月食》、《歲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條涉及天文學(xué)。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被認(rèn)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tǒng)地闡發(fā)民主主義思想的著作”[ ]。同時(shí)在該書中,黃宗羲還非常重視“學(xué)校”,認(rèn)為學(xué)校不僅在于養(yǎng)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xué)校”。他認(rèn)為學(xué)校除了有“五經(jīng)”師,“兵法、歷算、醫(yī)、射各有師”。他還說:
學(xué)歷者能算氣朔,即補(bǔ)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額,使禮部考之,官于欽天監(jiān)。學(xué)醫(yī)者送提學(xué)考之,補(bǔ)博士弟子,方許行術(shù)。歲終,稽其生死效否之?dāng)?shù),書之于冊,分為三等:……上等解試禮部,入太醫(yī)院而官之。[ ]
對于取士,黃宗羲提出了8種渠道,有科舉、薦舉、太學(xué)、任子、邑佐、辟召、絕學(xué)和上書。其中所謂“絕學(xué)”,黃宗羲說:
絕學(xué)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郡縣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發(fā)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 ]
顯然,黃宗羲非常強(qiáng)調(diào)天文學(xué)的學(xué)習(xí),注重選拔天文學(xué)人才。
黃宗羲在為學(xué)上有《明儒學(xué)案》、《宋元學(xué)案》等重要著作流傳于世,同時(shí)也撰寫了不少科學(xué)著作,其中天文學(xué)類著作“有《授時(shí)歷故》一卷,《大統(tǒng)歷推法》一卷,《授時(shí)歷法假如》一卷,《西歷假如》、《回歷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潛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對經(jīng)學(xué)、史學(xué)、文學(xué)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對科學(xué)也有較多的關(guān)注。尤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學(xué)與理學(xué)的“格物窮理”聯(lián)系在一起。他曾說:
密翁與其公子為質(zhì)測之學(xué),誠學(xué)思兼致之實(shí)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zhì)測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號(hào)曼公,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科學(xué)家。在學(xué)術(shù)思想上,他主儒、釋、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識(shí)》、《通雅》等科學(xué)著作。他認(rèn)為,學(xué)問有“質(zhì)測”、“宰理”、“通幾”之分,[ ]所謂的“質(zhì)測”就是要研究“物理”;他還明確指出:“物有其故,實(shí)考究之,大而元會(huì),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zhì)測’。”[ ]可見,方以智的“質(zhì)測之學(xué)”就是指自然科學(xué)。王夫之以方以智的“為質(zhì)測之學(xué)”解“格物”,實(shí)際上就是以研究科學(xué)解“格物”。把研究科學(xué)與儒家為學(xué)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聯(lián)系起來,足以表明王夫之對科學(xué)的重視。
王夫之不僅以研究科學(xué)解“格物”,他本人對科學(xué)也進(jìn)行了廣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問錄》以及《張子正蒙注》,其中《思問錄》外篇和《張子正蒙注》的《太和》、《參兩》等篇包含了豐富的科學(xué)方面的論述,涉及天文學(xué)、地學(xué)以及醫(yī)學(xué)等方面的內(nèi)容。
在天文學(xué)上,王夫之反對蓋天說,贊同渾天說。他認(rèn)為,蓋天說“可狀其象而不可狀其動(dòng)也,此渾天之說所以為勝”。他還說:
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畫一之理。[ ]
王夫之還具體分析了歷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zhuǎn)”以及張載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并且說:
張子據(jù)理而論,伸日以抑月,初無象之可據(jù),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為理,非可執(zhí)人之理以強(qiáng)使天從之也。[ ]
顯然,王夫之不贊同張載提出的“日月五星順天左旋”的觀點(diǎn)。與此同時(shí),他也不贊同張載用陰陽五行說解釋日月五星各自運(yùn)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確指出:“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為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 ]關(guān)于日月五星運(yùn)行的速度,王夫之說:
遠(yuǎn)鏡質(zhì)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蓋凡行者必有所憑,憑實(shí)則速,憑虛則遲。氣漸高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 ]
此外,王夫之對月食、月中之影、歲差等天文現(xiàn)象以及歷法的有關(guān)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diǎn)。
明清之際的陸世儀也非常重視天文學(xué)的研究。陸世儀(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號(hào)剛齋,又號(hào)桴亭,太倉(今屬江蘇)人。他贊同朱熹的格物窮理之說,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說:“致良知雖是直截,終不賅括,不如窮理穩(wěn)當(dāng)。……天下事有可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xué)而知者,名物度數(shù)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dāng)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運(yùn)行,必觀書考圖,然后明白,純靠良知,致得去否?”[ ]陸世儀認(rèn)為,科學(xué)方面的知識(shí)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識(shí),其認(rèn)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應(yīng)當(dāng)學(xué)習(xí)科學(xué)知識(shí)、研究科學(xué),而不是靠“致良知”。與此同時(shí),陸世儀還從經(jīng)世致用的角度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習(xí)科學(xué)的重要性。他說:“六藝古法雖不傳,然今人所當(dāng)學(xué)者,正不止六藝。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類,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講。俗儒不知內(nèi)圣外王之學(xué),徒高談性命,無補(bǔ)于世,此當(dāng)世所以來迂拙之誚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對天文學(xué)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晉卿,號(hào)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編《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學(xué),“以子朱子為宗,得道學(xué)正傳。而又多才多藝,旁及天文算數(shù)之事,尤能貫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則觀于天文,窮理之事也,此則儒者所宜盡心也。”[ ]在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學(xué)與儒家的“盡心”、“知性”、“知天”、“窮理”聯(lián)系在一起。
李光地對天文歷算有特殊的愛好,與當(dāng)時(shí)的天文學(xué)家、數(shù)學(xué)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參與修《明史歷志》。當(dāng)時(shí)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歷算才華,與他訂交,并就歷算的研究進(jìn)行了交談。此后,李光地經(jīng)常前去求教,學(xué)問大進(jìn)。期間,梅文鼎還根據(jù)李光地的建議編纂《歷學(xué)疑問》。該書寫成后,李光地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來,李光地又將《歷學(xué)疑問》以及梅文鼎推薦給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獎(jiǎng),于是名聲大震。在與梅文鼎的交往過程中,李光地對天文學(xué)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歷法類著作主要有:《歷象要義》、《歷象合要》、《歷象本要》等,主編《御定星歷考原》、《御定月令輯要》等;還有論文《記太初歷》、《記四分歷》、《記渾儀》、《算法》、《歷法》、《西歷》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漢學(xué)家。他除參與編修《四庫全書》外,還有著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聲類表》、《方言疏證》等,有清代考據(jù)學(xué)大師之譽(yù)。同時(shí),他也非常強(qiáng)調(diào)研究科學(xué)。他說:
誦《堯典》數(shù)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yùn)行,則掩卷不能卒業(y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hào),則比興之意乖。[ ]
顯然,戴震把對科學(xué)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訂古典科技文獻(xiàn)必要的知識(shí)基礎(chǔ)。
戴震不僅強(qiáng)調(diào)研究科學(xué),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學(xué),“凡天文、歷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鎮(zhèn)、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鐘實(shí)、管律之術(shù),靡不悉心討索。”[ ]正是對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寫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歷法類著作:《原象》、《續(xù)天文略》、《迎日推策記》、《九道八行說》、《周禮太史正歲年解》、《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記夏小正星象》、《歷問》、《古歷考》等。
還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黃宗羲、李光地等,他們在研究天文學(xué)時(shí),較多地通過介紹西方的天文學(xué)知識(shí),把中國傳統(tǒng)的天文知識(shí)與西方的天文學(xué)結(jié)合起來。這對于西方天文學(xué)的傳入是有積極意義的。
注釋: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與彭憲長論學(xué)書》。
[2] 《論語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問》。
[5] 參見高令印、樂愛國:《王廷相評傳》,江蘇: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頁。
[6] 《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7] 《日知錄》卷七《博學(xué)于文》
[8] 《日知錄》潘耒“序”。
[9] 馮契:《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邏輯發(fā)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頁。
[10] 《明夷待訪錄學(xué)校》。
[ 1] 《明夷待訪錄取士下》。
[ 2]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續(xù)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冊。
[ 3]《船山全書》第12冊《搔首問》,湖南:岳麓書社1992年版,第637頁。
[ 4] 參見羅熾:《方以智的“質(zhì)測通幾”之學(xué)》,載陳鼓應(yīng)等:《明清實(shí)學(xué)思潮史》(中卷),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識(shí)》“自序”。
[ 7] 王船山:《思問錄》外篇。
[ 8] 《思問錄》外篇。
[ 9] 《思問錄》外篇。
[20] 《思問錄》外篇。
[21] 《思辨錄輯要》卷三《格致類》。
[22] 《思辨錄輯要》卷一《大學(xué)類》。
[23] 阮元:《疇人傳》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55年版。
[24]梅文鼎:《歷學(xué)疑問》“李光地序”。
第2篇
一、舊《大統(tǒng)歷》誤差日顯,徐光啟
奉命修新歷
明朝建立之后,在歷法上開始采用的是《大統(tǒng)歷》。這個(gè)《大統(tǒng)歷》實(shí)際上是元朝天文學(xué)家郭守敬所發(fā)明的《授時(shí)歷》的翻版,只是換了個(gè)名字而已。郭守敬的《授時(shí)歷》發(fā)明之初,在當(dāng)時(shí)國際上處于領(lǐng)先地位,其精度極高。比如他那時(shí)測定的每天的時(shí)間長度,與今天相比才僅差72秒,在當(dāng)時(shí)的科技條件下,能做到如此精度,實(shí)在令人驚訝。
然而從發(fā)明《授時(shí)歷》到明末,已經(jīng)過了三百多年,各種誤差日積月累越來越大。而明朝歷局的官員們只知道依照已有的方法和數(shù)表推算節(jié)氣、天象,甚至用象數(shù)法進(jìn)行臆測,對于誤差怎樣解決大都束手無策,也沒人考慮。此時(shí),日食、月食、節(jié)令、朔望的預(yù)測和安排,已經(jīng)混亂不堪,嚴(yán)重影響國家和社會(huì)管理。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dāng)時(shí)外有滿清叩關(guān),內(nèi)有李自成、張獻(xiàn)忠問鼎,內(nèi)外交困,國家形勢危急。但崇禎皇帝考慮到歷法是一個(gè)王朝實(shí)施其統(tǒng)治的制度象征,歷法的混亂易導(dǎo)致國家的混亂,從社稷江山計(jì),不得不騰出精力來過問這件事關(guān)重大的具體科技問題,便責(zé)成時(shí)任禮部侍郎的大科學(xué)家徐光啟著手修歷。
徐光啟系進(jìn)士出身,他學(xué)識(shí)淵博,學(xué)貫中西,一生致力于科學(xué)事業(yè),著有巨著《農(nóng)政全書》60卷。受到崇禎皇帝重視,被擢進(jìn)入內(nèi)閣,任禮部侍郎。在此期間,他為復(fù)興大明,大力提倡以科學(xué)技術(shù)為“富強(qiáng)之術(shù)”,一方面操持政務(wù),一方面繼續(xù)研究天文、歷算、農(nóng)學(xué)、水利、軍事等科學(xué)。還認(rèn)真汲取當(dāng)時(shí)新傳入的西方自然科學(xué),大量譯介西方科技書籍。這在僵化保守的封建社會(huì)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正因如此,他成了中國歷史上學(xué)貫中西第一人,也是中國科技史上公認(rèn)的泰斗級人物。
徐光啟于崇禎元年(1628年)接受修歷任務(wù),此時(shí)他已是67歲的老人了。他不顧年邁,毅然上陣,立即組成了一個(gè)由中外科學(xué)家組成的龐大的科研班子,其中包括當(dāng)時(shí)著名的意大利科學(xué)家龍華民、羅雅谷,德國科學(xué)家湯若望、鄧玉函。他還制定了這次歷法科研的最高目標(biāo):“上推遠(yuǎn)古,下驗(yàn)將來,必期一一無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并迅速展開了工作。
在修歷的日子里,不管是凄風(fēng)冷雨的秋夜,還是大雪紛飛的隆冬,徐光啟都要登上觀象臺(tái),親臨指揮或親自動(dòng)手觀察天象。那期間,記錄、整理筆記、查找資料,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終于,經(jīng)過他和這些中外科學(xué)家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推出了《日躔歷指》等初步研究成果,接著又開始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歷書》的編纂工作。
二、魏文魁上呈《歷元》《歷測》,
志在否定徐光啟
使人想不到的是,此時(shí)遠(yuǎn)在京師滿城縣的鄉(xiāng)下,竟有一個(gè)叫魏文魁的老百姓,也在為《大統(tǒng)歷》的誤差而苦惱著。他不顧天文歷法歷來是民間研究的,也不顧自己沒有高深的數(shù)學(xué)知識(shí)和先進(jìn)的觀測設(shè)備,更顧不得自己生計(jì)的艱難,經(jīng)年累月一直執(zhí)拗地進(jìn)行著自費(fèi)天文歷法的研究。
此時(shí),魏文魁一定知道,西方的天文歷法技術(shù)已經(jīng)傳入中國。但他的思想不像徐光啟那樣開放,而是有點(diǎn)保守和固執(zhí),對外來的思想和技術(shù)采取了拒絕的態(tài)度,認(rèn)為依靠中國人自己的知識(shí)和文化完全可以解決此類問題。把先進(jìn)的科技知識(shí)拒之門外,這就犯了科研的大忌。
那么他依據(jù)什么來進(jìn)行研究呢?說來很有意思,魏文魁所采納和依據(jù)的重要資料是宋朝人邵雍的那本《皇極經(jīng)世》,而它依據(jù)的數(shù)學(xué)知識(shí)則是“周三徑一,方五斜七”等圓周和勾股之類。作為一個(gè)普通百姓,承擔(dān)如此艱巨的科研課題,依據(jù)的知識(shí)竟是這樣的初級和粗疏,再加上資料和設(shè)備又不具備,又沒有充裕的資金支持,可以想見,他的研究活動(dòng)一定是異常艱難的。
比如,他所依據(jù)的《皇極經(jīng)世》,是宋朝邵雍研究周易而自創(chuàng)的一門預(yù)測學(xué),是不是科學(xué)一直被人大打問號(hào)。該書一個(gè)最基本的概念,便是把人類世界的歷史壽命,根據(jù)易理象數(shù)的法則,規(guī)定出幾個(gè)簡單易記的字,這幾個(gè)字是:“元、會(huì)、運(yùn)、世、分。”他將此作為層級次序,來表示和解釋天文、地理、人事發(fā)展變化,以此進(jìn)行預(yù)測。
比如,從時(shí)間上來說,“元”可以認(rèn)為是年,一“元”就是一年,一年之中有十二個(gè)月,每個(gè)月日月相會(huì)一次,因此便叫做“會(huì)”。所以一“元”之中,便包含了十二“會(huì)”。每個(gè)“會(huì)”之中,地球自轉(zhuǎn)三十次,所以一“會(huì)”又包含三十“運(yùn)”,即三十天。因一天之中又有十二個(gè)時(shí)辰,因此一“運(yùn)”又包含十二“世”,即十二時(shí)辰。每個(gè)時(shí)辰又分三十“分”。
如果廣而擴(kuò)之,把最小的“分”代表年,便構(gòu)成了“三十年為一世,三百六十年為一運(yùn),一萬零八百年為一會(huì),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邵雍認(rèn)為,人類歷史、朝代興亡、世界分合、自然變化,都體現(xiàn)在這“元、會(huì)、運(yùn)、世、分”之中了,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檢測,皆可未卜先知。魏文魁對邵雍這方法頂禮膜拜,深信不疑,把這作為他的整個(gè)研究思路。顯然這對需要十分精細(xì)的歷法來說,太粗糙了。
按著邵雍的思路和理論框架,魏文魁毅然展開了工作。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居然完成了兩部洋洋灑灑的巨著:一部是天文理論著作《歷元》,一部是歷法知識(shí)著作《歷測》。
也就是在這時(shí)候,從北京傳來消息,由徐光啟制定的明顯西化遠(yuǎn)離我中華傳統(tǒng)的新歷法已經(jīng)有了雛形,對此魏文魁怎能接受?他認(rèn)為自己站出來的時(shí)機(jī)到了,便不顧一家老小的安危,當(dāng)即讓兒子魏象乾帶上他剛剛脫稿的兩部巨著,從滿城火速趕到京城,將書送給通政司并轉(zhuǎn)修歷局。他還加了一份上疏,歷數(shù)東方科技的優(yōu)點(diǎn)和西方科技的缺點(diǎn),以及徐光啟引入西方科技做法的謬誤。希望政府引起重視,并檢驗(yàn)和采納他的方法,企圖以此阻止和取代徐光啟的新歷法。
三、徐光啟虛懷若谷,魏文魁據(jù)理力爭
徐光啟聞知大吃一驚,但以多年形成的對不同學(xué)派的廣納博蓄習(xí)慣,以及對科學(xué)的嚴(yán)謹(jǐn)態(tài)度,他馬上冷靜下來。他本著“各家不同看法務(wù)求綜合”的一貫思想,決定對魏文魁的著作進(jìn)行一番公正的研判,以此也希望發(fā)現(xiàn)對手的價(jià)值所在。徐光啟還表示,在沒有通讀完對方著作前,堅(jiān)決不表態(tài)誰對誰錯(cuò),也不發(fā)一句議論。別人問起,他總是說:“文魁之本,臣尚未通讀,不敢言對錯(cuò)。”
可見徐光啟很有風(fēng)度,他對魏文魁的書看得非常認(rèn)真仔細(xì),將書中非常重要的七個(gè)問題一一摘錄,逐個(gè)進(jìn)行研究。通過仔細(xì)翻閱研究,他發(fā)現(xiàn)其中的謬誤很多,推算方法也十分陳舊粗陋。不要說日月食和五星凌犯,就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等二十四節(jié)氣的劃分都不準(zhǔn)確。
但是,徐光啟在研判魏文魁的著作中,也對魏文魁的刻苦研究精神進(jìn)行了肯定,稱他是“苦心力學(xué)之士”。徐光啟對他的謬誤一一進(jìn)行記錄,然后指出魏文魁的錯(cuò)誤都在什么地方。與此同時(shí),徐光啟以寬廣的胸懷傳信給魏文魁,希望他進(jìn)一步努力,爭取在天文學(xué)上真正有所建樹。還告訴他,若有疑義,可以當(dāng)面討論。實(shí)際上,徐光啟對魏文魁的研究成果持了完全否定態(tài)度。
魏文魁當(dāng)然不服輸,決心進(jìn)京與徐光啟論難。他堅(jiān)持認(rèn)為中國傳統(tǒng)方法推算的歷法精度要高于西法,認(rèn)為他的結(jié)果不準(zhǔn)確是因?yàn)橛^測地點(diǎn)不同而造成的。他舉例說,一樣的日月食,京師所觀測到的結(jié)果,與滿城觀測到的絕不會(huì)一樣,與瓊州觀測到的更不一樣,這怎么能說我的方法不準(zhǔn)確呢?至于二十四節(jié)氣的劃分,中國南北差距很大,在北方認(rèn)為準(zhǔn)確的,在南方就不一定準(zhǔn)確,武斷地說哪種方法正確,哪種方法不正確,這是不能服人的。
由于涉及科學(xué)問題,徐光啟沒有讓步,他認(rèn)為魏文魁的做法是“混推”,科學(xué)研究僅靠“混推”是站不住腳的。可是,這時(shí)的徐光啟仍然沒有以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表現(xiàn)出對魏文魁這場爭論的不屑,而是非常重視,每次辯論他都積極參加,還將辯論雙方的觀點(diǎn)都記錄下來,最后形成了《歷局與魏文魁辯論文稿》,保存?zhèn)浒浮?/p>
一個(gè)是國家頂尖級科學(xué)家,還是個(gè)國家的重要官員;另一個(gè)是民間業(yè)余科學(xué)愛好者,還是個(gè)平民百姓。他們竟能夠如此平起平坐地開展激辨,這在明末實(shí)在難能可貴,說明當(dāng)時(shí)明政府有較濃的崇尚科學(xué)的氣氛,以及徐光啟的虛懷若谷。
四、崇禎提出用實(shí)踐檢驗(yàn),
各家觀象臺(tái)上比高低
其實(shí),徐光啟在與魏文魁論戰(zhàn)之前,徐光啟的新歷還受到了其他天文歷法派別的猛烈攻擊。一是以欽天監(jiān)官員為首的一直對徐光啟吸收西方科學(xué)不滿,希望“祖宗之制不可變”的舊《大統(tǒng)歷》派,二是從伊斯蘭傳來的《回回歷》派。這兩派都認(rèn)為自己堅(jiān)持的歷法無可挑剔,而認(rèn)為徐光啟的歷法是不純正、不準(zhǔn)確、不科學(xué)的。現(xiàn)在又增加了一個(gè)魏文魁派,四派混戰(zhàn),轟動(dòng)朝野,震驚中外。
消息傳到皇帝崇禎那兒,鑒于此時(shí)國家形勢不妙,需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已不允許在這件事上這樣久拖不決,需要快點(diǎn)拿出成果。崇禎帝便提出可以“廣集眾長,虛心采聽,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務(wù)求綜合”的思想,希望大家不要再爭。然而,在各家都互不服氣的情況下,他的這一提議是無法實(shí)現(xiàn)的,激烈爭吵仍沒有平息。
事涉國家制度,崇禎帝又提出了另外一個(gè)辦法,既不看理論,不看設(shè)計(jì),也不論“課題組學(xué)術(shù)帶頭人”的身份,只用實(shí)踐檢驗(yàn)。指示尋找一個(gè)特殊天文現(xiàn)象,四家平等預(yù)測,誰家測準(zhǔn)了,誰就正確,國家就采納誰的方案。
崇禎所希望的可以進(jìn)行實(shí)踐檢驗(yàn)的機(jī)會(huì)很快來了:據(jù)預(yù)測,崇禎五年(1632年)九月十五日,將有月食,至于幾時(shí)幾刻還不知道。崇禎帝提出,讓大統(tǒng)、回回、魏文魁、徐光啟四派分別提前提出各自預(yù)測結(jié)果,精確到時(shí)和分,然后等到那一天進(jìn)行實(shí)際檢驗(yàn),看各家預(yù)測的準(zhǔn)確性。
四家受命,遂摩拳擦掌,高速運(yùn)轉(zhuǎn),精心準(zhǔn)備,志在必得。然而各家預(yù)測的結(jié)果大相徑庭,有的竟然相差達(dá)一、二個(gè)時(shí)辰。到底誰的正確呢?只等那一天見分曉。然而非常不巧,好不容易等到十五日夜間,結(jié)果那天天空陰云四合,使整個(gè)檢驗(yàn)計(jì)劃在大家的焦慮心情中落空了。
到崇禎六年(1633年)冬十月,徐光啟因?yàn)榉e勞成疾,已經(jīng)無法再主持修歷工作而辭去歷務(wù)。但是龐大的《崇禎歷書》還沒有徹底完成,四家的爭論仍在膠著狀態(tài),為了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yè),他提議讓既懂天文、又不封閉保守、能夠接受西方科技的山東參政李天經(jīng)接替他的職務(wù)。工作交接后只一個(gè)月徐光啟就病逝了,魏文魁失去了一個(gè)強(qiáng)有力的老對手。
崇禎七年(1634年),魏文魁再次上書,直言徐光啟派歷官所推所有交時(shí)節(jié)氣全然不對,應(yīng)該否掉,并采納他的方案。其他幾家也不示弱,天天爭吵不休。崇禎皇帝還是主張采取老辦法——實(shí)地檢驗(yàn),用事實(shí)說話。而且他此時(shí)變得更加開明,干脆由政府出資成立了四個(gè)天文局,分別為:大統(tǒng)局、回回局、西局和東局。這西局就是徐光啟這一派,而東局則是專為魏文魁所設(shè)。可見崇禎皇帝沒有因?yàn)槲何目且唤椴家掳傩斩鴮λ梢牟恍迹喾匆矠樗O(shè)一個(gè)局,作為封建皇帝這是難能可貴的。
四局成立之后,因?yàn)槎际艿搅嘶实鄣钠降葘ΥF(xiàn)在大家不分高下,爭論更加激烈了。那些天,“言人人殊,紛若聚訟”,欽天監(jiān)里,觀象臺(tái)上,天天吵吵嚷嚷,互相辯論訐難,爭鬧不休。
崇禎聞之,迅速?zèng)Q定,再次用實(shí)踐檢驗(yàn),讓各家在觀象臺(tái)上定高低。恰好這年李天經(jīng)按西洋方法預(yù)測,從閏八月開始將有“五星凌犯”天象出現(xiàn)。崇禎皇帝很快下旨,讓各家預(yù)測金、木、水、火、土五星凌犯準(zhǔn)確時(shí)間,到時(shí)進(jìn)行驗(yàn)證,然后定奪存廢。
各家接旨,迅速行動(dòng),都動(dòng)用了各自當(dāng)時(shí)最具科技含量的高精尖設(shè)備。觀象臺(tái)上,日晷、星晷、壺漏、開隙暗室、測高儀、窺筒、圖板、望遠(yuǎn)鏡、水盆、圭表,遍地都是。試驗(yàn)場地,更是人來人往,忙忙碌碌,緊張異常。很顯然,四家都極度緊張焦慮,因?yàn)榇蠹叶贾溃@是各自理論和方案能否被政府采用的最后一次搏擊。
這次檢驗(yàn)從八月中旬開始,至九月中旬結(jié)束,歷時(shí)一個(gè)月。皇帝所派官員,對照各家的預(yù)測,逐星進(jìn)行檢驗(yàn)。在這些時(shí)日里,四家科研工作者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經(jīng)過了無盡的煎熬和焦慮,最終檢驗(yàn)的結(jié)果是:西局的推算全部正確,其他各家均不準(zhǔn)。至此崇禎無情宣布:大統(tǒng)、回回、魏文魁的方法廢絀。
第3篇
一. 天文學(xué)研究的歷程
朱熹對天文現(xiàn)象的思考很早就已開始。據(jù)朱熹門人黃義剛“癸丑(1193年,朱熹63歲)以后所聞”和林蘷孫“丁巳(1197年,朱熹67歲)以后所聞”,朱熹曾回憶說:“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么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個(gè)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后也須有什么物事。其時(shí)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 ]可見,朱熹從小就關(guān)心天文,直到晚年仍對此難以忘懷,并孜孜以求。
然而,朱熹在其早期的學(xué)術(shù)生涯中,并沒有進(jìn)行天文學(xué)的研究。朱熹早年除讀儒家經(jīng)典外,“無所不學(xué),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xué)”[ ]。紹興三十年(1160年,朱熹30歲),朱熹正式拜二程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開始潛心于儒學(xué),并接受李侗以“默坐澄心”于“分殊”上體認(rèn)“理一”的思想。
據(jù)《朱文公文集》以及當(dāng)今學(xué)者陳來先生所著《朱子書信編年考證》[ ],朱熹最早論及天文學(xué)當(dāng)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歲)的《答林擇之》,其中寫道:“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xì)度其長短。”[ ]
測量日影的長度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觀測活動(dòng)之一。最簡單的方法是在地上直立一根長八尺的表竿,通過測量日影的長短來確定節(jié)氣;其中日影最短時(shí)為夏至,最長時(shí)為冬至,又都稱為“日至”。與此同時(shí),這種方法還用于確定“地中”。《周禮地官》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意思是,在夏至日中午測得日影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地便是“地中”。而且,從“地中”向北,每一千里則影長增一寸;向南,每一千里則影長減一寸。這就是《周髀算經(jīng)》所謂“周髀長八尺,勾之損益寸千里”。這一說法到南朝以后受到懷疑;唐朝的一行和南宮說通過不同地區(qū)日影的測量,進(jìn)一步予以糾正。朱熹要其弟子林擇之協(xié)助測量日影,顯然是要比較不同地區(qū)日影的長短,其科學(xué)精神可見一斑。
在同年的《答蔡季通》中。朱熹寫道:“歷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概規(guī)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yàn)。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
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年);建陽(今屬福建)人,學(xué)者稱西山先生;精于天文、地理、呂律、象數(shù),著作有《律呂新書》、《大衍詳說》等;為朱熹“四大弟子( 蔡元定、黃干、劉爚、陳淳)”之首。蔡元定的年齡僅比朱熹小5歲,并在天文學(xué)等科學(xué)上有所造詣,很受朱熹的器重。從以上所引《答蔡季通》可知,當(dāng)時(shí)朱熹正與蔡元定討論天文歷法,并且認(rèn)為,研究歷法必須用科學(xué)儀器進(jìn)行實(shí)際的天文觀測。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4歲),朱熹在《答呂子約》中寫道:“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shí)亦非光散,但為物掩耳。若論其實(shí),須以終古不易者為體,但其光氣常新耳。”[ ]顯然,朱熹在此前已研讀過北宋著名科學(xué)家沈括的《夢溪筆談》,并對沈括的有關(guān)天文學(xué)的觀點(diǎn)進(jìn)行分析。胡道靜先生認(rèn)為,在整個(gè)宋代,朱熹是最最重視沈括著作的科學(xué)價(jià)值的唯一的學(xué)者,是宋代學(xué)者中最熟悉《夢溪筆談》內(nèi)容并能對其科學(xué)觀點(diǎn)有所闡發(fā)的人。[ ]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6歲),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寫道:“《星經(jīng)》紫垣固所當(dāng)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宿之中,若列于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當(dāng)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昏旦夜半當(dāng)中之星。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曉。……《星經(jīng)》可付三哥畢其事否?甚愿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cuò),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亦初學(xué)之階梯也。”[ ]可見,當(dāng)時(shí)朱熹正與蔡元定一起研究重要的天文學(xué)經(jīng)典著作《星經(jīng)》和以詩歌形式寫成的通俗天文學(xué)著作《步天歌》,并就如何確定天空中恒星的位置問題進(jìn)行討論,其中涉及三垣二十八宿星象體系。
同年,朱熹在《答蔡伯靜》中寫道:“天經(jīng)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形為可低昂反復(fù)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自不看見耳。蓋圖雖古所創(chuàng),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鉆穴為星,而虛其當(dāng)隱之規(guī),以為甕口,乃設(shè)短軸于北極之外,以綴而運(yùn)之,又設(shè)短軸于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shè)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 ]在這里,朱熹設(shè)想了一種可進(jìn)入其中觀看天象的龐大的渾天儀。
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57歲),朱熹在《答廖子晦》中寫道:“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shí),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yuǎn)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yuǎn)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shí),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yuǎn),于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nèi),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zhí)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nèi)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yuǎn),則雖扇在內(nèi),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nèi),而執(zhí)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 ]在這里,朱熹對月亮盈虧變化的原因作了探討。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歲),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寫道:“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tái),卻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zhuǎn),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 ]在這里,朱熹試圖通過比較各地北極星的高度及其與地中岳臺(tái)的關(guān)系,以證明大地的運(yùn)動(dòng)。
朱熹在一生中最后的十年里,在天文學(xué)研究上下了較多的功夫,并取得了重要的科學(xué)成就。南宋黎靖德所編《朱子語類》卷一“理氣上太極天地上”和卷二“理氣下天地下”編入大量朱熹有關(guān)天文學(xué)的言論,其中大都是這一時(shí)期朱熹門人所記錄的。例如:《朱子語類》卷二朱熹門人陳淳“庚戌(1190年,朱熹60歲)、己未(1199年,朱熹69歲)所聞”:“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jìn)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qiáng),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zhì)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 ]
《朱子語類》的其它卷中也有此類記錄。例如:《朱子語類》卷二十三黃義剛“癸丑(1193年,朱熹63歲)以后所聞”: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dòng),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義剛問:“極星動(dòng)不動(dòng)?”曰:“極星也動(dòng)。只是它近那辰后,雖動(dòng)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dòng)來動(dòng)去,只在管里面,不動(dòng)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dòng)。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dòng)。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又曰:“天轉(zhuǎn),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huán)磨轉(zhuǎn),卻是側(cè)轉(zhuǎn)。”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zhuǎn),極卻在中不動(dòng)。”[ ]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熹所著《北辰辨》(大約寫成于1196年,朱熹66歲)以及卷六十五朱熹所注《尚書》之《堯典》、《舜典》(大約寫成于1198年,朱熹68歲)都包含有豐富的天文學(xué)觀點(diǎn)。《北辰辨》是朱熹專門討論天球北極星座的論文;在所注的《堯典》中,朱熹討論了當(dāng)時(shí)天文學(xué)的歲差、置閏法等概念;在所注《舜典》中討論了早期的渾天說、渾天儀的結(jié)構(gòu),并詳細(xì)記錄了當(dāng)時(shí)的渾天儀結(jié)構(gòu)。
這一時(shí)期朱熹所編《楚辭集注》(成書于1195年,朱熹65歲)之《天問》中也有一些注釋反映了他在天文學(xué)方面的研究和造詣。
二. 天文學(xué)的成就
就朱熹研究天文學(xué)的方法而言,其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 ]:
其一,細(xì)心觀察各種天文現(xiàn)象。朱熹是重視親身觀察、善于觀察的人。他經(jīng)常運(yùn)用儀器觀察天文現(xiàn)象;并運(yùn)用觀察所得驗(yàn)證、反駁或提出各種見解。
其二,用“氣”、“陰陽”等抽象概念解釋天文現(xiàn)象。朱熹所采用的這一方法與中國古代科學(xué)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其三,運(yùn)用推類獲取新知。朱熹經(jīng)常運(yùn)用“以類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東西、直觀的東西,對天文現(xiàn)象進(jìn)行類推解釋。
其四,闡發(fā)前人的天文學(xué)研究成果。朱熹研讀過包括沈括《夢溪筆談》在內(nèi)的大量科學(xué)論著,對前人的天文學(xué)觀點(diǎn)均予以評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從現(xiàn)代科學(xué)的角度看,朱熹的天文學(xué)研究方法,固然有其不足之處,這主要是由于古代科學(xué)所處的階段而導(dǎo)致的。在古代科學(xué)的范疇中,朱熹的天文學(xué)研究方法應(yīng)當(dāng)屬于合理。更為重要的是,朱熹運(yùn)用這些方法在天文學(xué)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朱熹在天文學(xué)方面的科學(xué)成就主要反映在他最后十年里有關(guān)的言論中。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gè)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氣”為起點(diǎn)的宇宙演化學(xué)說。朱熹曾經(jīng)說:“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個(gè)氣運(yùn)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里面無處出,便結(jié)成個(gè)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huán)運(yùn)轉(zhuǎn)。地便只在中央不動(dòng)。不是在下。”[ ]這里描繪了一幅宇宙演化途徑的圖景。
在朱熹看來,宇宙的初始是由陰陽之氣構(gòu)成的氣團(tuán)。陰陽之氣的氣團(tuán)作旋轉(zhuǎn)運(yùn)動(dòng);由于內(nèi)部相互磨擦發(fā)生分化;其中“清剛者為天,重濁者為地”[ ],重濁之氣聚合為“渣滓”,為地,清剛之氣則在地的周圍形成天和日月星辰。朱熹還明確說:“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shí),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腳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時(shí)凝了。初間極軟,后來方凝得硬。……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輕便成風(fēng)霆雷電日星之屬。”[ ]他根據(jù)直觀的經(jīng)驗(yàn)推斷認(rèn)為,大地是在水的作用下通過沉積而形成的,日月星辰是由火而形成的。
將宇宙的初始看作是運(yùn)動(dòng)的氣,這一思想與近代天文學(xué)關(guān)于太陽系起源的星云說有某些相似之處。1755年,德國哲學(xué)家康德提出了太陽系起源的星云說;1796年,法國天文學(xué)家拉普拉斯也獨(dú)立地提出星云說。星云說認(rèn)為,太陽系內(nèi)的所有天體都是由同一團(tuán)原始星云形成的。然而,在他們500多年之前,朱熹就提出了類似之說;盡管尚缺乏科學(xué)依據(jù)和定量的推算,但其通過思辯而獲得的結(jié)果則是超前的。
對此,英國科學(xué)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學(xué)史》一書中予以記述:“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他認(rèn)為,在太初,宇宙只是在運(yùn)動(dòng)中的一團(tuán)渾沌的物質(zhì)。這種運(yùn)動(dòng)是漩渦的運(yùn)動(dòng),而由于這種運(yùn)動(dòng),重濁物質(zhì)與清剛物質(zhì)就分離開來,重濁者趨向宇宙大旋渦的中心而成為地,清剛者則居于上而成為天。……”[ ]
第二,提出了地以“氣”懸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結(jié)構(gòu)學(xué)說。朱熹贊同早期的渾天說,但作了重大的修改和發(fā)展。早期的渾天說認(rèn)為:“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天內(nèi),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 ]但是,當(dāng)天半繞地下時(shí),日月星辰如何從水中通過?這是困擾古代天文學(xué)家的一大難題。朱熹不贊同地載水而浮的說法,他說:“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yùn)乎外,故地?fù)n在中間,隤然不動(dòng)。”[ ]這就是說,地以“氣”懸空在宇宙之中。
至于地如何以“氣”懸空在宇宙中央,朱熹說:“天運(yùn)不息,晝夜輾轉(zhuǎn),故地?fù)n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yùn)轉(zhuǎn)之急,故凝結(jié)得許多渣滓在中間。”[ ]又說:“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zhì)者;但以其束于勁風(fēng)旋轉(zhuǎn)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 ]朱熹認(rèn)為,宇宙中“氣”的旋轉(zhuǎn)使得地能夠懸空于宇宙中央。朱熹的解釋克服了以往天文學(xué)家關(guān)于宇宙結(jié)構(gòu)學(xué)說的弱點(diǎn),把傳統(tǒng)的渾天說發(fā)展到了一個(gè)新水平。[ ]
關(guān)于地之外的天,朱熹說:“天之形,……亦無形質(zhì)。……天體,而實(shí)非有體也。”[ ]“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 ]又說:“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 ]這顯然是吸取了傳統(tǒng)宣夜說所謂“天了無質(zhì),……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無止,皆須氣也”[ ]的思想。
第三,提出了天有九重和天體運(yùn)行軌道的思想。朱熹認(rèn)為,屈原《天問》的“圜則九重”就是指“九天”,指天有九重。事實(shí)上,在朱熹之前,關(guān)于“九天”的說法可見《呂氏春秋有始覽》: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后來的《淮南子天文訓(xùn)》等也有類似的說法;直到北宋末年洪興祖撰《楚辭補(bǔ)注》,其中《天文章句》對“九天”的解釋是: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顯然,這些解釋都不包括天有九重的思想。
朱熹則明確地提出天有九重的觀點(diǎn),并且還說“自地之外,氣之旋轉(zhuǎn),益遠(yuǎn)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dāng)?shù),而至于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fù)有涯矣”[ ];同時(shí),朱熹贊同張載所謂“日月五星順天左旋”的說法。他進(jìn)一步解釋說:“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jìn)過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jìn)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jìn)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jìn)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shù);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shù),遂與天會(huì)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jìn)數(shù)為順天而左,退數(shù)為逆天而右。”[ ]《朱子語類》卷二朱熹的門人在闡釋所謂“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時(shí)說:“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nèi),大輪轉(zhuǎn)急,小輪轉(zhuǎn)慢。雖都是左轉(zhuǎn),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zhuǎn)了。”朱熹贊同此說。[ ]
對此,英國著名科學(xué)史家李約瑟說:“這位哲學(xué)家曾談到‘大輪’和‘小輪’,也就是日、月的小‘軌道’以及行星和恒星的大‘軌道’。特別有趣的是,他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逆行’不過是由于天體相對速度不同而產(chǎn)生的一種視現(xiàn)象。”[ ]因此李約瑟認(rèn)為,不能匆忙假定中國天文學(xué)家從未理解行星的運(yùn)動(dòng)軌道。
在天文學(xué)研究中,朱熹除了提出以上新見外,還對沈括有關(guān)天文學(xué)的觀點(diǎn)做過詳細(xì)的闡述。例如:沈括曾說:“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cè),而所見才如鉤;日漸遠(yuǎn),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涂其半,側(cè)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 ]朱熹贊同此說,并接著說:“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 ]他還說:“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
三. 對后世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天文學(xué)大致包括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和歷法兩大主要部分,尤以歷法最為突出。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自漢代形成蓋天說、渾天說和宣夜說之后,也經(jīng)歷了不斷的發(fā)展,主要表現(xiàn)為占主導(dǎo)地位的渾天說不斷吸取各家學(xué)說之長而逐步得到完善。
朱熹的天文學(xué)研究側(cè)重于對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的研究。他通過自己的天文觀測和科學(xué)研究,以渾天說為主干,吸取了蓋天說和宣夜說的某些觀點(diǎn),提出了較以往更加完善的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把古代的渾天說推到一個(gè)新的階段,這應(yīng)當(dāng)是朱熹對于古代天文學(xué)發(fā)展的一大貢獻(xiàn)。
但是,由于朱熹的天文學(xué)研究只是專注于宇宙的結(jié)構(gòu),對于當(dāng)時(shí)在天文觀測和歷法方面的研究進(jìn)展關(guān)注不夠,在這些方面的研究稍顯不足。因此,他的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在某些具體的細(xì)節(jié)方面,尤其是定量方面,尚有一些不足之處,有些見解和解釋是欠妥當(dāng)?shù)摹?/p>
然而,他畢竟對宇宙結(jié)構(gòu)等天文學(xué)問題作了純科學(xué)意義上的研究,代表了宋代以至后來相當(dāng)長一段時(shí)期中國古代天文學(xué)在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研究方面的水平。而且,朱熹的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在后來直至清代一直受到了不少學(xué)者的重視和引述。
朱熹之后宋末的重要學(xué)者王應(yīng)麟(1223~1296年,字伯厚,號(hào)深寧居士)撰《六經(jīng)天文編》六卷,記述了儒家經(jīng)典中大量有關(guān)天文學(xué)方面的重要論述,《四庫全書六經(jīng)天文編》“提要”說:“是編裒六經(jīng)之言天文者,以易、書、詩所載為上卷,周禮、禮記、春秋所載為下卷。”該著作也記述了朱熹的許多有關(guān)天文學(xué)方面的論述。
元代之后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jīng)”為官定教科書。其中《尚書》以蔡沈的《書集傳》為主。蔡沈(1167~1230年,字仲默,號(hào)九峰)曾隨其父蔡元定從學(xué)于朱熹。他的《書集傳》是承朱熹之命而作,其中包含了朱熹所注《尚書》之《堯典》、《舜典》等內(nèi)容,涉及不少有關(guān)天文學(xué)方面的論述。另有元代學(xué)者史伯璿(生卒不詳)著《管窺外篇》;《四庫全書管窺外篇》“提要”說:該書中“于天文、歷學(xué)、地理、田制言之頗詳,多能有所闡發(fā)。”在論及天文學(xué)時(shí),該書對朱熹的言論多有引述,并認(rèn)為“天以極健至勁之氣運(yùn)乎外,而束水與地于其中”。這與朱熹的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是一致的。
明初的胡廣等纂修《性理大全》,其中輯錄了大量朱熹有關(guān)天文學(xué)的論述。明末清初的天文學(xué)家游藝(生卒不詳,字子六,號(hào)岱峰)融中西天文學(xué)于一體,撰天文學(xué)著作《天經(jīng)或問》,后被收入《四庫全書》,并流傳于日本。該書在回答地球何以“能浮空而不墜”時(shí)說:“天虛晝夜運(yùn)旋于外,地實(shí)確然不動(dòng)于中……天裹著地,運(yùn)旋之氣升降不息,四面緊塞不容展側(cè),地不得不凝于中以自守也。”這里吸取了朱熹關(guān)于氣的旋轉(zhuǎn)支撐地球懸于空中的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在解釋地震的原因時(shí),該書又明確運(yùn)用了朱熹的這一觀點(diǎn),說:“地本氣之渣滓聚成形質(zhì)者,束于元?dú)庑D(zhuǎn)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墜為極重亙中心以鎮(zhèn)定也。”在論及日月五星的運(yùn)行方向和速度時(shí),該書說道:“日月之行,宋儒言之甚詳”,并且還直接引述朱熹關(guān)于五星運(yùn)行方向和速度的觀點(diǎn)予以說明。
清代著名學(xué)者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晉卿,號(hào)榕村)曾奉命主編《朱子大全》,其中“卷四十九理氣一”有“總論、太極、天地、陰陽、時(shí)令”,“卷五十理氣二”有“天文、天度、地理、雷電、風(fēng)雨雪雹霜露”,收錄了朱熹有關(guān)天文學(xué)的不少論述。李光地所著的《歷象本要》引述了朱熹所謂“地在中央不動(dòng),不是在下”,“天包乎地”以及“天有九重”等,用以說明朱熹的天文學(xué)思想中包含了西方天文學(xué)有關(guān)宇宙結(jié)構(gòu)的知識(shí)[ ]。他在所撰的《理氣》篇說:“朱子言天,天不宜以恒星為體,當(dāng)立有定之度數(shù)記之。天乃動(dòng)物,仍當(dāng)于天外立一太虛不動(dòng)之天以測之,此說即今西歷之宗動(dòng)天也。其言九層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遠(yuǎn)得一層,運(yùn)轉(zhuǎn)得較緊似一層。至第九層則緊不可言。與今西歷所云九層一 一吻合。”[ ]他的《御定星歷考原》六卷,也引述了朱熹有關(guān)宇宙結(jié)構(gòu)的言論,并且認(rèn)為,朱熹所說的“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就是指“天渾圓地亦渾圓”,而與西方天文學(xué)的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相一致。
李光地與被譽(yù)為清初“歷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號(hào)勿庵)[ ]交往甚密,并且對當(dāng)時(shí)的西方科學(xué)都持“西學(xué)中源”說。梅文鼎在所著《歷學(xué)疑問》中多處引用朱熹有關(guān)宇宙結(jié)構(gòu)的言論。該書認(rèn)為,朱熹已經(jīng)具有西方天文學(xué)所謂“動(dòng)天之外有靜天”、“天有重?cái)?shù)”和“以輪載日月”的觀點(diǎn),并且說:“朱子以輪載日月之喻,兼可施諸黃、赤,與西說之言層次者實(shí)相通貫。”[ ]
除此之外,清代還有黃鼎(生卒不詳)的《天文大成管窺輯要》八十卷,其中也包括朱熹有關(guān)天文學(xué)的不少論述。
朱熹是古代的大哲學(xué)家,代表了中國古代哲學(xué)發(fā)展的一座高峰。也許正是這個(gè)原因,他在天文學(xué)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沒有能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但是,這并不能否認(rèn)他在天文學(xué)上確實(shí)做出過卓越的貢獻(xiàn),他的宇宙結(jié)構(gòu)理論對后世產(chǎn)生過重大的影響。
注釋:
[ ] 李約瑟:《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第四卷《天學(xué)》,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75年版,第2頁。
[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卷第九十四。
[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
[ ]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 《答林擇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以下簡稱《文集》,卷四十三。
[ ] 《答蔡季通》,《文集》續(xù)集卷二。
[ ] 《答呂子約》,《文集》卷四十七。
[ ] 胡道靜:《朱子對沈括科學(xué)學(xué)說的鉆研與發(fā)展》,《朱熹與中國文化》,學(xué)林出版社1989年版。
[ ] 《答蔡季通》,《文集》卷四十四。
[ ] 《答蔡伯靜》,《文集》續(xù)集卷三。
[ ] 《答廖子晦》,《文集》卷四十五。
[ ] 《答蔡季通》,《文集》續(xù)集卷二。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三。
[ ] 樂愛國、高令印《朱熹格物致知論的科學(xué)精神及其歷史作用》,《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7年第1期。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梅森:《自然科學(xué)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頁。
[ ] 《晉書天文志上》。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朱子語類》,卷第一。
[ ] 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頁。
[ ] 杜石然等:《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稿》(下),科學(xué)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頁。
[ ] 朱熹:《楚辭集注》,第51頁。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晉書天文志上》。
[ ] 朱熹:《楚辭集注》,第51頁。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李約瑟:《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第4卷,科學(xué)出版社1975年版,第547頁。
[ ] 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shù)一》。
[ ] 朱熹:《楚辭集注》,第53頁。
[ ] 《朱子語類》,卷第二。
[ ] 樂愛國:《李光地的中西科技觀述評》,載《李光地研究》,廈門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
[ ] 《榕村語錄》卷二十六《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