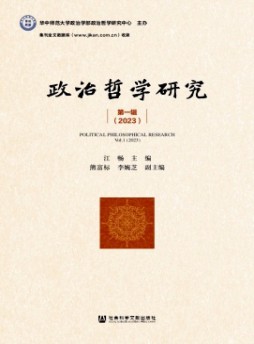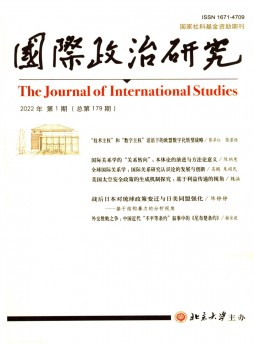例論政治在解放區(qū)文學(xué)的滲透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例論政治在解放區(qū)文學(xué)的滲透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內(nèi)容摘要:解放區(qū)文學(xué)在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因而政治對其起到絕對性的“把控”。無論本土作家群還是外來知識分子作家群都紛紛隱匿原本話語表達(dá)方式,努力用主流意識形態(tài)指導(dǎo)自己的創(chuàng)作。本文主要以《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為例探究政治對解放區(qū)文學(xué)書寫內(nèi)容、模式及語言等方面帶來的影響。
關(guān)鍵詞:《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解放區(qū)文學(xué);政治滲透
“解放區(qū)文學(xué)”是指自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到1949年建國前這段時期的文學(xué)。嚴(yán)格來說,它是以《講話》為界限,以政治為基礎(chǔ)的一種特殊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它使文學(xué)“開始做到真正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結(jié)合,開始做到真正首先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起了極大的變化。”政治幾乎成為解放區(qū)文學(xu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從各個方面對其進(jìn)行滲透。
一.書寫內(nèi)容的政治化大眾化的需求
迫使解放區(qū)作家書寫的主要內(nèi)容必須扎根鄉(xiāng)村,但在政治背景下,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已逐漸被政治解構(gòu)。鄉(xiāng)村的寧靜恬適﹑樸素的人情在政治的滲透下顯出“畸形化”。
1.鄉(xiāng)村風(fēng)景的隱喻功能解放區(qū)文學(xué)作品很少涉及風(fēng)景描寫,即便有所涉及,因?yàn)檎蔚臐B入也早已“變質(zhì)”。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盡管丁玲多次觸及暖水屯的鄉(xiāng)村風(fēng)景描寫但或隱或顯的政治因素使得文本有些“不倫不類”。“路兩旁和洋河北岸一樣,稻穗穗密密的擠著。谷子又肥又高,都齊人肩頭了。高粱遮斷了一切,葉子就和玉茭的葉子一樣寬。泥土又濕又黑。從那些莊稼從里,蒸發(fā)出一種氣味。走過了這片地,又到了菜園地里了,水渠在菜園外邊流著,地里是行列整齊的一畦一畦的深綠淺綠的菜……”莊稼、土地在農(nóng)民眼中(甚至作者的眼中)不再是單純的鄉(xiāng)村風(fēng)景,它是生活希望及社會地位的象征。人們對土地的艷羨都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fā)。在政治的影響下,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風(fēng)景已然可以上述到國家政治層面,它的擁有者亦是特定的政治階層。自然環(huán)境在濃烈的政治氛圍下成了社會環(huán)境的縮影,其文學(xué)審美性也被極度弱化。特別是對鄉(xiāng)村空間中“河流”、“道路”、“大地”等事物的描寫: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多次描寫洋河邊的路及河流,河流是自然形成的它給人的活動形成一種自然阻礙,致使人的行動變得遲緩。于是,作者刻意安排人物借助外力來打破這種天然阻礙:顧老漢駕著胡泰的車子安然地穿過泥濘,車雖多次在河里顛簸最后依舊安然到達(dá)暖水屯。相較于“河流”這種自然化程度較高的外部環(huán)境而言,關(guān)于“道路”的描寫,則有著更為濃厚的政治氣息。道路本身含有快捷、順暢之意,它受人工因素影響較大因此方向(政治方向)明確。小說中,道路是連接暖水屯與外部的主要途徑,一直是屯里上演政治活動的“主舞臺”,是區(qū)上政治方向與暖水屯實(shí)際性實(shí)施之間的連接點(diǎn)。
2.政治化的人情政治因素對解放區(qū)文學(xué)作品的滲透不僅體現(xiàn)在外部環(huán)境更滲入到人情內(nèi)部。(1)人以群分。整個暖水屯村民都嚴(yán)格遵循著“人以群分”的交往規(guī)則。原初的親屬關(guān)系被政治性的隸屬關(guān)系瓦解,沈從文筆下那種溫情的鄉(xiāng)村倫理在這里也早已被解構(gòu)。暖水屯像個等級森嚴(yán)的小社會,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治屬性。地主、富裕中農(nóng)、貧農(nóng)(佃戶)、共產(chǎn)干部……這些既定的政治階層基本在既定的空間內(nèi)活動。這一點(diǎn)從訴苦大會便可看出,訴苦大會作為小空間能量的聚合將鄉(xiāng)村人際的政治分層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劉滿訴苦》一節(jié)通過劉滿與組組員楊亮的對話我們了解到,所謂的訴苦實(shí)則是觀念不滿的濃縮。劉滿作為積極分子本想通過翻身卻適得其反,“干部們可草蛋,他們不敢得罪人。你想嘛,你們來了,鬧了一陣子,你們可是不用怕誰,你們要是走的啦。干部們就不會同你們一樣想法,他們得留在村子上,他們得計算斗不斗得過人,他們總得想想后路啦……。”在過程中,以張?jiān)C駷榇淼拇甯刹俊俺允磷犹糗浀摹睙o非是考慮到群眾本身的政治階層。對待錢文貴這樣的大地主他們總要為自己留后路,并不會毫無保留地去。此時,政治因素成了人情交往的關(guān)鍵。(2)政治性婚戀觀。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顧涌女兒的婚姻、錢文貴女兒的婚姻、李子俊與其老婆的結(jié)合……都是出于對政治利益的權(quán)衡。這里也包括作者著重描寫的人物黑妮,她與程仁互相愛慕但因身份懸殊無法在一起。隨著的進(jìn)行,程仁從窮佃戶變成農(nóng)會主任,他不得不從自己與黑妮的政治階層考慮,這個地主家的女子成了影響自己前程的障礙物。也就是說,程仁是否將黑妮視為結(jié)婚對象考慮的關(guān)鍵因素不是婚戀本身,而是她的出身。“程仁現(xiàn)在既然做了農(nóng)會主任,就該什么事都站在大伙兒一邊,不應(yīng)該去娶他侄女,同她勾勾搭搭就更不好,他很怕因?yàn)檫@種關(guān)系影響了他現(xiàn)在的地位,群眾會說閑話。”單純的男女情感﹑婚戀關(guān)系在政治面前如此地不堪一擊。(3)性別政治化。在解放區(qū)政治環(huán)境下,丁玲早期鮮明而獨(dú)立的女性色彩和性別立場逐漸被政治意識取代。她從女性軀體﹑精神的雙重角度,展現(xiàn)鄉(xiāng)村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直指鄉(xiāng)村政治背后的男權(quán)中心意識。我們可以從大地主錢文貴的家庭結(jié)構(gòu)以窺一二,錢家當(dāng)家的是錢文貴,雖然名義上已經(jīng)和兩個兒子分家了但紅契依舊掌握在自己手中。老婆沒有主見;兒媳懼怕他這只“猛虎”;黑妮在他的權(quán)威下“涂了一層不調(diào)和的憂郁”。丁玲從政治對家庭介入的角度出發(fā)為家庭改造轉(zhuǎn)向社會變革尋求合法性依據(jù)。在政治背景下,女性的性別特征已經(jīng)模糊化,她們甚至放棄了經(jīng)營自己身體的權(quán)利徹底服從和依附男權(quán)。盡管革命的介入以“均貧富”的方式改變了鄉(xiāng)村宗法制社會的倫理體系與價值規(guī)范,女性的權(quán)利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承認(rèn)與默許。但這種改變不過是表象,如婦聯(lián)會主任董桂花盡管領(lǐng)導(dǎo)著婦女工作與其他男性干部看似平等,可她所有的行為都只是在為丈夫服務(wù)。在小說中,我們能夠明顯感受到解放區(qū)政治形勢對丁玲創(chuàng)作帶來的影響。丁玲在延安后期創(chuàng)作中的女性意識明顯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擠壓和異化。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她不再用人物本名命名女性本身,而是以“李子俊老婆”、“趙得祿的女人”這類稱呼命名。這可以說是丁玲對政治化和男權(quán)身份認(rèn)同的一種表現(xiàn)。
二.“大團(tuán)圓”結(jié)局書寫模式
解放區(qū)文學(xué)隨無產(chǎn)階級新政權(quán)而產(chǎn)生,這必然要求文藝要最大限度地參與革命,與民眾產(chǎn)生共鳴,成為革命進(jìn)程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故而解放區(qū)作家們自覺服從革命斗爭的需要,以政治任務(wù)作為創(chuàng)作責(zé)任承諾,表現(xiàn)工農(nóng)兵革命題材內(nèi)容,善意描繪樂觀團(tuán)圓的勝利結(jié)局。于是,傳統(tǒng)的“團(tuán)圓”情節(jié)模式開始備受作者青睞。無論文學(xué)作品中情節(jié)多么曲折,主人公命運(yùn)如何凄慘,矛盾多么復(fù)雜,最終都會迎來圓滿結(jié)局。解放區(qū)主要的文學(xué)作品:《王貴與李香香》、《小二黑結(jié)婚》、《李有才板話》、《白毛女》、《新兒女英雄傳》、《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無一例外地都是大團(tuán)圓模式,對“大團(tuán)圓”結(jié)局模式的追求,儼然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追求的普遍現(xiàn)象。“大團(tuán)圓”的書寫模式雖常為人詬病但在革命現(xiàn)實(shí)面前,這類作品體現(xiàn)了解放區(qū)作家在文藝大眾化﹑民族化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盡管強(qiáng)烈的政治性已消解其內(nèi)在的文學(xué)性審美性,但從文學(xué)史角度出發(fā),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自“五四”開始提倡的文學(xué)大眾化問題在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眸與反撥。三.文本語言的轉(zhuǎn)變解放區(qū)文學(xué)在語言方面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昔日繁復(fù)冗長的抽象化﹑歐化表述已被民族化的短語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傳神的白描甚至是土語方言取代。解放區(qū)文學(xué)作品的語言整體上向政治化﹑大眾化方向發(fā)展。小說中,丁玲在語言的敘述上多使用短句且人物語言較為粗疏。“要是有那些軟骨頭,稀泥泥不上墻的角色,就別叫他當(dāng)干部嘛……窮人當(dāng)家了,窮人都敢說話,別說這幾個尖,還得請他滾蛋呢。”與以丁玲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作家群不同的是,本土作家多是土生土長的農(nóng)民,故而書寫語言絲毫沒有歐化的氣息,本土味兒十分濃郁。一方面,他們注重語言的簡潔緊湊,缺乏雕飾。由于身處解放區(qū)所以寫起反映工農(nóng)兵生活、農(nóng)村斗爭的作品便格外得心應(yīng)手。另一方面,本土作家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模式本身就是扎根民間的,因而在描寫人物事件時擅長運(yùn)用快板、評書、地方戲等民間元素。《小二黑結(jié)婚》里直接引用當(dāng)?shù)厝罕娍谡Z安排人物對話;《王貴與李香香》全部采用陜北方言敘述:“人有精神馬有勁,麻麻亮?xí)r開了槍。”我們應(yīng)當(dāng)明確的是,解放區(qū)作品這種富有流動性、意境明朗的語言結(jié)構(gòu)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對“五四”歐化語言的反撥,對民族風(fēng)格的繼承,但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語言是為解放區(qū)政治策略及相關(guān)活動的傳播開展服務(wù)的。特殊的政治背景為解放區(qū)文學(xué)這種新的文學(xué)形態(tài)的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在民族救亡的緊要關(guān)頭,文學(xué)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影響。也許,政治性書寫會略顯粗疏,但可貴的是,他們?yōu)槲膶W(xué)探索出另類的書寫模式,創(chuàng)造了別樣的書寫可能性。僅從《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中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創(chuàng)作在政治滲透中的改變,政治使文學(xué)的宣講、戰(zhàn)斗功能逐步強(qiáng)化,文學(xué)明顯地縮短了與接受對象的距離。解放區(qū)社會結(jié)構(gòu)的變革決定了解放區(qū)文學(xué)的發(fā)展趨勢,構(gòu)成了這一特定時空下文學(xué)的獨(dú)特個性和色調(diào)。我們要將這種文學(xué)現(xiàn)象放在特殊的文化環(huán)境中加以探討,客觀看待政治對解放區(qū)作家創(chuàng)作滲透這一現(xiàn)象。
參考文獻(xiàn)
[1]郭沫若.為建設(shè)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J].中華全國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代表大會紀(jì)念文集,1949,(7).
[2][3][4][8]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
[5]顏浩.女性立場﹑革命想象與文學(xué)表述———以《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秧歌》為例[J].文藝爭鳴,2015,(2).
[6]陳紅玲,田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女性話語研究[J].邵陽學(xué)院學(xué)報,2017,(1).
[7]施軍.解放區(qū)文學(xué)“大團(tuán)圓”結(jié)局現(xiàn)象分析[J].南京政治學(xué)院學(xué)報,2001,(6).
[9]李季.王貴與李香香[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
[10]劉增杰.解放區(qū)文學(xué)散論[J].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1990,(10).
[11]王玉樹,陳榮毅.略論解放區(qū)文學(xué)對民族形式的探討[J].天津社會科學(xué),1990,(3).
[12]趙朕.關(guān)于解放區(qū)文學(xué)的斷想[J].重慶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1998,(11).
作者:杜歡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