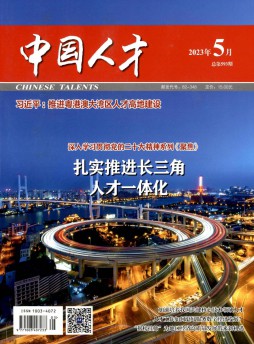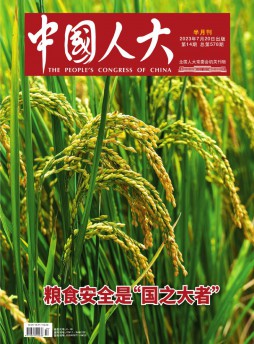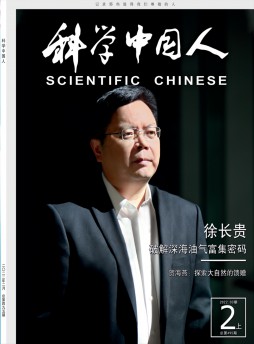國人對屬靈信奉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國人對屬靈信奉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當(dāng)代中國人的物質(zh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這大概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注意自省的人們總能發(fā)現(xiàn)自身的“缺失”,而“缺失”正困擾著我們,讓我們的靈窒息。且心靈上的痛苦對于自省的人們也不斷的證明了這樣的一個事實“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岀的一切話。”(太4:4)〔1〕
物質(zhì)上的滿足不應(yīng)該是也不能是我們有理性的人類的最終目的。因為天堂絕對不應(yīng)該是“豬”的世界。物質(zhì)上的滿足對于自我乃至人類的解放只能是一種最基礎(chǔ)的鋪墊,因此絕非人生目的所在,而神的話語才是我們最終的方向。
當(dāng)代中國對于“神的話語”最大的挑戰(zhàn)莫過于科學(xué)主義。什么是科學(xué)主義?這個問題未免過于龐雜,但了解科學(xué)主義我想得首先知道科學(xué)是什么?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描述科學(xué)的話,可以說科學(xué)是建立在假設(shè)基礎(chǔ)上的通過實證的方法所得岀的一系列知識,其本質(zhì)在于其實證性。由此在科學(xué)的語境中知識之所以“真實”就在于其可以被實證,能夠被實踐檢驗,而除此之外的知識的“真實性”將都會被無情的排除在外。回過頭來看,可以說科學(xué)主義乃就是以站在科學(xué)的“高度”或者自認為站在科學(xué)的“高度”“藐視”一切,“藐視”從一般的人文學(xué)科一直到哲學(xué)一切“非科學(xué)”的一種態(tài)度。科學(xué)主義有時甚至被認為是一種信仰,一種“準(zhǔn)宗教”。從歷史的角度看,科學(xué)主義是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對它的反思則是現(xiàn)代之后的事情。為什么要反思科學(xué)主義?原因是自明的。乃就是歷史的實踐-這個具有科學(xué)性的事實-告訴我們以科學(xué)主義為靈魂的現(xiàn)代并沒有給我們帶來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帶來的只又一次大戰(zhàn)與二次大戰(zhàn)無數(shù)冤魂的吶喊!雖然不可否認科學(xué)的發(fā)展使人們的生活方便了許多,但是現(xiàn)代人在享用科學(xué)所帶來的對物質(zhì)世界的改造的同時,是否也應(yīng)該對自己的處境有所思考,而不要在“欲望”的陷阱當(dāng)中無意識的走入地獄的烈火之中?反思它我想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在于科學(xué)主義能否解決一切?能否拯救我們的靈魂?能否真正解決靈魂的“缺失”?因為科學(xué)主義經(jīng)常會否認靈的存在,而原因只是因為它無法證明祂。歷史已經(jīng)早已在訴說真理,科學(xué)不是萬能的。人類最終完善的計劃,科學(xué)只能做其基礎(chǔ)。而在反思并批判科學(xué)的道路上,我想我們必須豎起屬靈的信仰的大旗。為什么要是屬靈?什么是屬靈的信仰?為什么要信仰?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應(yīng)該自省到“個體的欠然”這個概念。神說:“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chuàng)2:17)但是男人沒有經(jīng)受住女人的誘惑,因為“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創(chuàng)3:6)女人也沒有經(jīng)受住蛇的誘惑,因為“于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cè)说难勰浚沂强上矏鄣模苁谷擞兄腔郏驼鹿觼沓粤恕!保▌?chuàng)3:6)因而我們?nèi)祟愲m然“便如神能知道善惡。”(創(chuàng)3:5)甚至如神一樣能夠創(chuàng)造萬物。但是“他說:‘我在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裸體,我便隱藏了。’”(創(chuàng)3:10)看啊!人在父的面前竟然不能坦然,靈魂在被腐蝕,腐蝕使得人害怕父嚴肅的愛,使得人開始隱藏自己的靈。如上所言,個體的欠然就是因為我們的“原罪”,這是認知的代價,代價就是我們必須承受靈魂的拷問。這樣的靈魂乃就是缺失的。
但缺失的靈魂這樣的理念也許對于西方人不算是一個問題,因為這就像為什么要吃飯一樣早已經(jīng)融入到了他們的生命之中。而對于中國人卻很難明白這樣的“欠然”是怎么一會事情,這樣的問題也讓西方人在看待中國人以及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這個問題時產(chǎn)生了困難。“叔本華已經(jīng)曉得,傳教士們沒有搞懂中國的Glaubenslehren(信仰學(xué)說),因為‘因為他們受的是樂觀主義教育’,無法理解中國人把Daseyn(生存)理解為Uebel(不幸),將世界看作Jammer(受苦),‘最好不要生在這個舞臺上’。”〔2〕中國人在1840年之前,是在一個“倫理天下”生存著。中國遍是天下,天下就是人生目的之所在,之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前由于大一統(tǒng)的定局早已形成,幾千年以來中國人的思想之最高目的乃就在于怎樣使這個狀態(tài)傳之于萬世。不論天下紛爭時起時落,大一統(tǒng)的定局還總是樂觀的實現(xiàn)了。因而中國人思想當(dāng)中現(xiàn)世的思維總是占上峰,是受著一種現(xiàn)實而樂觀的教育。但有人或許會發(fā)出疑問,就算總體的大人生是樂觀的,但小個體在歷史的某一個時間段中總還是無助的,那時怎么辦!難道中國人就沒有一點類似“宗教”的東西?答案是有的,且這就在中國獨特的古典文化當(dāng)中。一般我們說中國古典文化乃是由儒、釋、道三部分組成。儒就是指得釋儒家思想,釋是指得是佛家思想,道是指得是道家思想。這里面首先就儒家思想來說。如果按照西方的術(shù)語解釋儒家思想的話,則其乃就是一種倫理理論。此種理論就個人來說講究個體與天下的同一,人生的意義不在于個體的完善而在于平天下。也就是說天下平了個體也就自然而然的到達了最終目的。就社會(群體)來說,儒家思想是以宗族生活為基礎(chǔ)的,個體的經(jīng)濟生活、“宗教情感”等等一切無不在宗族生活當(dāng)中得到體現(xiàn)。因而宗族生活在中國古代乃是此一個社會的核心。這不單單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領(lǐng)域,更是精神生活的現(xiàn)世寄托之所在。在上有皇室這個大宗族,在下有公、候、伯、子、男、士等等小宗族。大宗族與小宗族唯一區(qū)別可能就在于其勢力和政治、經(jīng)濟權(quán)力的大小不同而已。就其思想、其架構(gòu)也都是同一的。所以儒家思想在中國如果概而言之:可以說就是一個“天人合一”的個體倫理與宗族生活的社會倫理相結(jié)合的倫理體系。其次就佛家思想而言。佛教自從漢末陸續(xù)從印度傳到我國,可謂是歷經(jīng)諸多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最終其在唐時正式在中國站穩(wěn)了腳跟,得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佛學(xué)猶如浩海一般,無所窮盡。但是研讀歷史我們知道,中國的佛教自從天臺宗、法華宗乃至禪宗以后,佛學(xué)便漸漸脫離了印度時期濃厚的“論理”色彩而“中國化”了。這也許是因為論理性的東西對于王道樂土的我們未免太過沉重。總之佛學(xué)在中國漸漸與儒學(xué)相互滲透,并漸漸由原先極強的論理性轉(zhuǎn)變?yōu)椤耙磺兄T法,依此心有,以心為體。”〔3〕,轉(zhuǎn)變成為一種把自我寄托于來世的心性信仰。最后就道家思想。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道家思想不等于道教思想。雖然兩者之間有密切的聯(lián)系,但是道家思想嚴格上講不應(yīng)該稱其為是一種宗教,而更應(yīng)該是一個人生哲學(xué)。道家講究出世,講究無為,講究順其自然。道家對于現(xiàn)世不如儒家那么積極,它是一種被動的順從。之所謂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思想如果從“莊老”開始,恐怕可能比孔子的歷史還長,至少也是同時代左右的人。所以道與儒應(yīng)該是最早相互影響的。兩者就像天平的兩端,互相的調(diào)節(jié)能夠使一個人保持一種心性的平衡以面對現(xiàn)世的殘酷。而反觀后來的佛家,也許是因為在五胡亂華的年代佛教被認為是胡人的宗教,是外來的,所以長期以來自然受到了傳統(tǒng)中國倫理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的反彈。魏晉南北朝時期幾次大規(guī)模的滅佛運動,以及“神滅神不滅”的爭論都可以佐證此點。但是正如我提到過的,佛學(xué)后來也心性化了,其被一定意義上同化了,被儒和道感染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儒和道本身也沒有“逃脫”被佛家感染的命運,道教的形成就是一個證明。如此儒、釋、道三家共同組成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而其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歷史在人類思想史當(dāng)中也算是個奇跡。到此我想可以說也許是中華這種獨特的人文環(huán)境因而產(chǎn)生了此種獨特文化思想,其并承擔(dān)了古代中國政治、經(jīng)濟、教育、宗教等各個社會職能。因此在一個宗族生活當(dāng)中一切人事都能被消融,而個體偶爾的“無助”也能同樣被佛家與道家的聯(lián)合力量所調(diào)節(jié),之所謂“去之則行,舍之則藏”。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傳統(tǒng)的中國思想之大概。但是自從一八四〇年以來,中國不單單是在軍事、政治方面受到了嚴重的沖擊,更劇烈的還是在思想領(lǐng)域的大地震!從開始的“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到后來“德先生、賽先生”中國的知識人們無不盡心尋找新的出路以解救民族危亡。然而現(xiàn)實的危及使得我們的知識人們很難全面研讀西學(xué)之精髓,往往都是功利性的“拿來主義”。在這種思維的指導(dǎo)下,作為西學(xué)最高精神的“真理”,并沒有植入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極端的思想。變革后來演變成為革命。是啊!那個時代是個飛速的時代,我們不能忍受的東西太多太多,又有誰能夠在民族的悲慘命運面前保持一種冷靜呢?這種要求未免過高了。但是也許有一個人做到了,那就是錢穆先生。也許錢穆先生這個人在大陸是幾乎要到遺忘的邊際了,然而在臺灣其被尊為“一代國學(xué)大師。”錢穆先生其書有個特點,乃是很注意國學(xué)與西學(xué)之不同。比如在《中國文化史導(dǎo)論》一書中有“本節(jié)所用“宗教”、“哲學(xué)”等名詞,皆就西方屬于術(shù)語用之。”〔4〕如此就打消了很多人爭論如儒家思想是否是宗教?中國哲學(xué)存在嗎?這類問題。因為這本是兩個不同的領(lǐng)域,用得是不同的語言,根本沒有在一個西方語境下比較的意義。同樣的道理馮友蘭先生在其一九三〇年《中國哲學(xué)史》中也闡述的很詳細。如此在這種瘋狂當(dāng)中,歷經(jīng)、,儒家思想至少在大陸遭到了致命性的摧殘。民眾的道德觀變了,變成了空洞與虛無。改革開放后,思想的禁錮被打開。如此當(dāng)代的中國思想可以說是五花八門。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新儒家思想可以說都有其一席之地,且都在論證自己在中國的正當(dāng)性,爭當(dāng)未來可能的主流意識。可是這些思潮可以是政治的、經(jīng)濟的、倫理的,但就是沒有給宗教信仰留出應(yīng)有的一席之地了。中國傳統(tǒng)的宗教信仰有嗎?上文已經(jīng)回答。問題是現(xiàn)在還可能建構(gòu)這傳統(tǒng)的信仰嗎?大概有的人是這么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復(fù)活“陸王的心性儒學(xué)”。但這種心性在脫離了宗族生活后還能存在多久,還能存在多長?當(dāng)代中國社會已經(jīng)不再是“教會”式的時代了,群體信仰已經(jīng)早被丟到歷史的倉庫當(dāng)中。當(dāng)代社會是人本的社會,包括信仰在內(nèi)都是以人為目的的,都是以個體解放為歸宿。在當(dāng)代重提恢復(fù)宗族生活式的感情,未免顯得是那么的蒼白無力。那么當(dāng)代人在信仰的問題上應(yīng)該怎么辦?我認為大概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建立屬靈的基督信仰。因為自從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代社會人類信仰最有力的支撐。而中國的基督信仰也有了一個不長不短的歷史,有一定的基礎(chǔ)。現(xiàn)在的問題是由于種種原因基督教的神學(xué)思想并沒有被理性的介紹到中國并生根發(fā)芽。但又有人會反駁說:為什么不能是以道教為載體的宗教化的道家思想或者是佛教。我的回答是正如上文所說得那樣,佛教與道家思想早已經(jīng)和儒家思想合而為一。就道家思想而言。其思想的本質(zhì)決定其根本不能承擔(dān)屬靈的信仰這個重擔(dān)。其只能在現(xiàn)世尋找答案也至多是祈求長生不老,而最后頓入迷信的怪圈子。它不能承載理性的重擔(dān)使其注定不能在當(dāng)代的宗教當(dāng)中理性的向人類傳播福音。就佛教而言。本來印度佛教是一個理性福音很好的載體,但是正如我指出的那樣,佛教的中國化斷送了中國人受洗的進程。看看現(xiàn)在的寺廟,燒香拜佛對于中國人來說從沒有虔誠一說,大家無非都是抱著信則有不信則無的態(tài)度,如此連信仰都成了功利的表現(xiàn)。因而這樣的宗教信仰,其中沒有人會真正自省自己以達到道德的完滿。但或許真正可以稱為信徒的只有寺廟的僧侶們了。但是修道院式的生活在當(dāng)代恐怕只有淪為虛妄的笑柄了。所以在儒家思想被摧殘的當(dāng)代不論道與釋都不能承載人類沉重的肉身。如果還有人對于道與釋抱有信仰的幻想,我只能送他一句話“人類的苦難比大海的沙子還要沉重,莊禪情懷的高超不就因為它比大海的沙子清逸嗎?”〔5〕
最后對于還執(zhí)迷于科學(xué)拯救人類的自大狂們以及對基督抱有偏見的人們,我只能用圣?奧古斯丁的一段話回復(fù)你們。“讀我這些三位一體反思的人,必須牢記,我執(zhí)筆是為了反對那些不屑于從信仰出發(fā),反因不合理地、被誤導(dǎo)了地溺愛理性而深陷虛幻的人的詭辯。他們當(dāng)中的一些人,試圖將他們所觀察到的關(guān)于物體的東西運用到非物質(zhì)的、屬靈的事上,他們把通過身體感官經(jīng)驗到的或憑著自然人的理智、生活實踐和技巧習(xí)得的東西當(dāng)作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屬靈的事。又有一些人,他們在思考上帝時,講人類精神的本性和情緒歸到上帝身上,這樣,他們的上帝概念就是錯誤的,使他們關(guān)于上帝的論證與扭曲的、誤導(dǎo)性的闡釋規(guī)則連在了一起。除此之外,還有一類人,他們努力想爬到勢有改變的受造的宇宙的上面,將他們的思想升高到不變的實體即上帝那里。不過,他們因受必死性之累而頭重腳輕,以致他們本不知道的東西,他們希望別人認為他們知道,他們希望知道的東西呢,他們卻實在不能知道;這樣,他們就由于武斷地肯定他們自己的謬見,而堵死了通往正解的道路;他們寧愿固執(zhí)自己的謬見,而不愿糾正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