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中國德育面對的抉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轉型期中國德育面對的抉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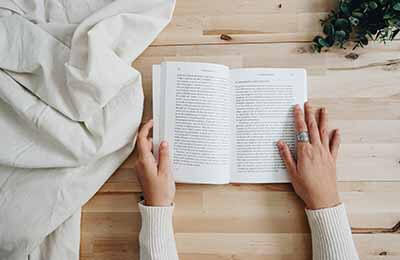
自覺選擇:一種社會哲學觀
道德、道德教育作為人們的一種主體活動,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它的發展不是純自然歷史過程,它不是預成性,也不是按照某種單一線路向前進行的。在其發展過程中,主體的自覺選擇和歷史創造性構成發展的重要一環。特別是處在社會歷史轉折關頭時,發展會更加呈現出多種可能的路向,提供更為廣闊的可能空間,人的自覺選擇更具有其特殊的意義。以這樣的基本社會歷史觀來審視中國道德、道德教育的發展,那就不能將它視作為一種自然過程,認為存在著一條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預定的”、“客觀的”發展道路,如認為道德必隨經濟發展而發展的經濟決定論等等,而是要將之作為人的自為地尋求發展的過程,自覺選擇和設計的過程。同樣地,也不能把其他國家已經走過的路,認作是我們的“楷模”,亦步亦趨地步其后塵。
充分自覺地把握中國道德、道德教育發展的可能空間,這是作為自覺選擇的前提。應當看到人們所面臨的任何可能空間都會有它的現實限定性,為此,人的選擇也總是基于現實的某種選擇。轉型期中國道德教育的可能發展空間首先是基于我們國家內部社會生活的變化,同時還應該看到在人類歷史已進入世界歷史的時代,其他國家、民族的相關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也必將影響我國發展的過程,構成為發展中的一個現實因素,為我們開拓出新的發展可能空間,其中包括現代化先行的國家在道德、道德教育發展中的經驗與教訓。這些都可能成為我們的一種“后發展優勢”;增強選擇的可能性,加強選擇的自覺性,賦予歷時性的發展以共時性的意義。俄國托洛茨基說過:“雖然落后國家被迫跟隨著發達國家,但前者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歷史落伍者的特權……容許甚至自己采納任何地方、任何時期已經完成的發展樣式,從而越過居間的等級系列。”[1]本文的論述就是基于上述的社會哲學觀。
道德坐標軸心的轉換:獨立人格的培育
要把握當代中國道德、道德教育可能發展的空間,在這里所使用的方法就不是訴諸于絕對理念的假設,或是從形而上的道德觀出發來進行思辨性推理。它要求我們對中國轉型期所存在的普遍社會事實和現象(包括道德的)做出實際的考察,探明由這種事實、現象所揭示的諸種可能,用一種“實踐理性”來進行價值的選擇,這樣才有可能成為一種自覺的選擇[2]。
當前中國最具普遍意義的社會事實是什么?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的最基本的道德發展可能空間又是什么呢?
回顧20年中國社會變革的事實,不能不看到的一個最根本的變化就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生活方式的深刻變化。人們開始從自然經濟、計劃經濟中走出來,從而也逐步掙脫了由血緣、地緣和由依附群體所聯結起來的人對人的依賴關系與隸屬關系,開始可能以一種自由、平等、獨立人格的身份參與到市場經濟以及其他一切社會活動中來。這說明市場經濟孕育了新的人與人的關系,它為現代獨立人格的發展開拓出了新的可能空間,也是中國當代道德教育所面臨的可能空間。這樣的空間為道德教育培養出一代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以及形成這種人格的各種內在道德屬性,諸如自主、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品質,提供了選擇的可能。
發展獨立人格早已是五四以來中國的先行者、魯迅、胡適等人所追求的目標,他們為“解放人性”而呼喚,為中國人爭得“人的資格”而奮斗。但是,由于市場經濟、工業經濟等發展不足,獨立人格缺乏相應孳生的土壤,再加上兩千多年占統治地位的抹煞個體獨立性的“整體至上”的傳統道德十分強大,體現獨立人格的道德文化始終不占主流地位。新中國成立以來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又使每個人隸屬于他的組織,個人的一切依賴于組織,而以往作為共產主義思想原則所理解的集體主義道德,也沒有把個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作為它的基本前提,于是,傳統的整體主義道德又以另一種形式出現。解放幾十年來占主導地位的道德和道德教育所倡導的,其實質還是一種抹煞、乃至反對個人獨立性的道德。為此,選擇以培育個體的獨立人格作為我們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基本取向,這是一種道德坐標軸心的根本轉換,是中國兩千多年道德和道德教育的根本轉型。將道德、道德教育的坐標軸心轉向獨立人格的
發育與培養,它的根據不僅在于具有其可能性,而且還在于它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表現為它是當代中國人和社會發展的根本所在。
道德就其本義而言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建立的一種自我肯定、自我發展的手段。人之所以需要道德,根本上是為使人成為人,使類的自由本性得以高揚,使每個人的獨立人格得以確立,使自主、自覺、自尊等等自我肯定的人格屬性得以涌現,在這基礎上才能構成人與人之間的最佳結合,也才能滿足人的諸種深層次精神追求與需要。只是人類長期經歷了一種道德異化的歷史,在這段歷史中,道德變成束縛、限制乃至反對人發展的工具,變成消解獨立個體存在的手段。它通過控制人的精神而扼殺人的獨立性和進取心,否定人積極干預社會生活的意向和能力。在中國,這種吃人道德異化的歷史尤為漫長,綿延至今還處處存在。
試看1999年12月3日《南方周末》所載余衛國《奴才意識》一文:1999年9月27日上午,在陜西省黃陵鎮中心小學四年級班上,一位22歲的數學教師,因葛同學未完成作業打了他兩個耳光,并一腳踹倒。又令全班50個同學每人抽葛10教棒。誰抽得重誰受表揚,抽得輕者自己受10棒處罰。40多分無情棒打將葛同學打得大小便失禁,至今病休在家。到11月21日在教室要求全班打過葛的舉手。全班同學都歡快地舉起手來,后排的學生怕人看不見,站在凳子上齊聲說:“我們打過”!以上一例也許是存在于當代中國教育中的極端之一例,但是不可否認,在中國教育中好孩子的普遍道德標準還是聽話、順從、守紀律等等,獨立自主,個性解放,還經常被視為異端,有獨立個性的學生常要遭否定和打擊。
再從當前人的主觀意識看。一項規模較大的社會道德調查表明:獨立性、尊重他人等等的品德,在中國人所推崇的品德中還居于相當的后位,其中獨立性在26個選項中居第17位,尊重他人居第11位[3]。說明改革開放20來年,在國人的主觀視域中獨立性等等品質尚占不到它應有的位置。
正是這種個體獨立性的闕如,唯上、從眾、安分守己的社會心態,以及“不為人先”、“行高于人,眾必非之”的處世態度尚彌散于當今社會之中,進一步消蝕了中國人的獨立意識、創新精神、進取思想,導致了個體精神的萎縮,弱化了社會發展的生機和動力。這種缺乏獨立人格的個人在對待他人時也難于將他人當作獨立人來對待。誠如黑格爾所認為的:“成為一個人,并尊敬他人為人”是一條道德的絕對的命令,人只有具有獨立人格的自尊、自重才會尊重他人的人格,把他人視為與自己同具相等價值、相同平等地位、同等機會的獨立一員來對待,這種對待他人的視界是正義感的來源,也是道德產生的根基。由于獨立人格的發育不成熟、不健全,依附性人尚普遍存在,人還沒有真正脫離他所屬的血緣、地緣、群緣等等關系的臍帶。在對待他人時,人們往往從中國特有的關系序列出發,凡是從這種關系序列中通不過去的,都可能成為被排斥的他者,變為非倫理、反道德的實踐對象。這也即是說,從依附性人格中無法演化出公正、正義、平等等等現代人所擁有的公共關系道德準則。這種依附性人格特質也正是當今社會生發種種丑惡、腐化現象的原因之一。“熟人好辦事”已經成為中國老百姓的處世“真理”。它腐蝕人的心靈,使由教育所曉喻的一系列道德準則在現實生活中都化為“空話”。這是道德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
綜上所述,選擇獨立人格的發展作為當今道德、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標,它的合理性不僅立足于人格和社會發展之可能,更在于它的現實需要。這種自覺選擇必將導致道德坐標軸心的轉換,引起道德和教育領域的強列震蕩,也會遭遇到種種困難和阻力。但中國的道德和道德教育也只能作出如是選擇,既然歷史已為我們開辟了這樣的可能性,人的自覺性就要把它轉為現實的存在。
共生的理念:對個人主義的超越
獨立人格要作為中國當代道德教育自覺選擇的目標,還需要解決一個合理性的問題:我們所要建構的獨立人格是否以西方現代化先行社會普遍存在的個人主義為其模型?在人類生存方式及思維方式已經發生新的轉型時代中,獨立人格的發展又出現了何種新的可能空間?中國道德教育將以何種獨立人格的發展模型、發展取向作為自覺選擇的目標?“幾乎所有現代性的解釋者都強調個人主義的中心地位”,“個人主義這個詞通常用來刻畫現代精神與社會及其機構間的關系的特點”[4]。作為現代性重要表征的個人主義是以近代物理學原子論為其方法論依據的,這種方法論把整個宇宙視作為由許多彼此分離、互不聯系的原子所組成,同樣,人的世界也是由彼此分離的、孤立的、封閉的單子式個人所組成。萊布尼茲就把個人視作為“單子”;而克爾凱郭爾所闡發的人格就是“孤獨個人”,認為只有“孤獨個人”才是具體的、唯一的、具有真理性的;霍布斯認定“人對人是狼”,是互相之間不可理喻不可溝通的。這種單子式個人的主要特征表現在主客體關系上,是相互之間對立的,是以占有客體為目的的;表現在與其他主體關系上,是排他性的,是以他人為工具的;在自我關系上,“自我”等同于他的占有物,人被物化、異化。個人主義存在的社會歷史根據主要是以追逐金錢及物質私利為本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實存在,也由于在一定發展階段中人與人之間的世界性普遍交往關系尚未充分展現,從而導致人的發展的局限性。
如今,這種個人主義人格已經遭到種種社會現實的批判。由個人主義的無限膨脹而引發的拜金主義、物質主義已成為西方社會的痼疾,更有甚者,為追逐私利而導致的現代戰爭、生態危機等等已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最為根本的是近一個世紀來人類正在醞釀著一場新的生存形態的革命,如佩魯所說的“人的革命”,它使個人主義型態人格逐漸失卻了它存在的合理性。這種生存形態的革命首先表現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之中。不論在這個過程中會產生怎樣的沖突和矛盾,不論人們能否自覺地意識到它,作為一個基本事實,這種一體化的經濟已經成為一種拉力,把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人緊緊地拴在一起,使人們之間發生了互相不可分離的關系。其次,當代交往格局的變化,隨著知識經濟的逐步形成,以及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增加了各種信息知識與文化共享的可能。信息和知識的特性是它們不受限制地流動,并具有無限擴大的能力,它為每個個體自由平等地獲得信息與知識開辟了道路,它也為不同個體之間達成共識和相互理解創設了條件。隨著個人電腦的逐步普及,出現了一個相對獨立于現實社會的網絡社會,在這一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信息的交流超越了任何時空、對象的限制,交往的范圍普遍到全世界、全人類、交往的速度縮短到頃刻之間,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個由他們自己編織而成的四通八達的大網,在其中各種對話、交流和溝通成為當代人普遍的存在與發展方式。再次,日益嚴重的全球性生態危機,人們所面對的是整個人類的生死存亡問題,每個人的利益都面對著人類根本命運的理性抉擇,在它的拉動下,更把人們的命運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上述種種情況表明,單子式個人正逐步喪失其存在的歷史根據,作為個體的人正朝著與他人共在的生存方式前進。與此同時,人們對單子式個體范疇得以建立的原子論方法論也開始做出了反思與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有機論方法論。其中如“共在”、“主體間性”、“共生”(conviviality)、“關系性自我”等等,開始成為理解人、建構人的新的概念范疇,成為一種新的人格理念。
當代的許多哲學家都對這種關于人的新范疇、新理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胡塞爾認為作為每個人的“自我”,都擁有一個共同世界,世界既是我的,也是你的、他的,自我與他我通過擁有共同世界而形成一個共同體,單一的主體性也因之而過渡到主體間性。海德格爾則把“在世”作為“此在”的基本結構,也即在“此在”中滲入了世界與他人,企圖說明個人不可能單獨、孤立地存在,他總是與他人他物不可分割地在同時、同一世界中存在[5]。哈貝馬斯認為交往是個人之間具有的關系,交往的目的是建立主體間性,形成主體之間的相關性、統一性。還有一批后現代哲學家,如格里芬(Griffin,D·R)、凱瑟琳凱勒等人則把每個個體看作是一種“關系性的自我”,他們針對原子論單子式個體的觀點,以新的有機論指出所有的實體都跟所在的世界之中的其他實體分享著內在關系,它們之間相互交融、滲透、影響,根本不存在不能穿透的界限,人與他人他物的關系都是個人人格的內在、本質的構成性的東西。而“共生”的理念則是運用生態學的方法論在確認異質者“共存”的基礎上,承認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們之間通過相互開放而建立起來的積極關系。
上述有關個人的新的詮釋說明了在哲學思維中的人之轉向,誠如有的學者所總結:“從笛卡爾以來,哲學家一直在絞盡腦汁解釋:主體是怎樣認識客體的。但是直到20世紀,哲學家才開始提出這個更難以理解的問題:一個主體是怎樣完全與正在作為另一個主體相接觸的”。簡單地說,當今哲學所關注的是每一個個體是如何進入其他個體之中的,以達臻自我與他我的某種整合。為此,對話和交往就成為當代突破單子式個體的重要哲學范疇。把對話和交往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在這種生存方式中,個體的自我中心化結構得以消解、揚棄,個人的存在獲得了開放性和創造性,也使得建立在個體獨立性基礎之上的視野融合成為可能。
綜上所述,當代對“個人”范疇的重新建構,其實質在于尋找一種具有時代意義的完整人格、人性,賦予獨立人格以新的、更為豐富的內涵,當代的獨立人格不再是單子式個體型的,而是共生(共在)型的。這種獨立人格的基本心性結構當是由與他人的深切統一感以及與自然的深切統一感組合而成,這種統一感包括了“共同”和“共容”兩重意義。從教育的角度看,首先,要使學生意識到我們生活中正在出現并擴大著的人與人之間的共同利益、共同價值以及正在形成著的共同規則、共同倫理,這些都是一個現代人所必須承認和遵守的;使他們了解當代人類發展中所具有世界化、全球化、一體化的大趨勢,“不忘人類發展的大目標”[6],對于有背于這種大目標的,或在“全球化”、“一體化”的招牌下所推行的各種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都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
其次,當今的世界和社會又存在著多極主體,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關系和價值追求,在這種多極格局下,每個個體要承認“自我”和“他者”共在一個“生態圈”之中,其中每一個對另一個來說也許都是不可或缺的。物種的持續發展依靠“共生”來維持,同樣,人和文化的生存與發展也需要有不同取向、異質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才能實現共生、共榮,才能創構新的文化、新的價值。為此,培養學生具有一種生存的同一感,學會“走向他人”,學會與不同價值取向的人共容于一體,在追求人類發展與進步的目標下,做到對他人的尊重、寬容、關懷、理解,學會通過對話、溝通,克服狹隘的文化、價值偏見,從而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7]。這種包括“共同”與“共容”的價值思維,正成為教育學的一種時代性的思維,近20年來由當代教育理念所提出的“學會關心”、“學會共同生活”已開始成為當代各國教育的主題。
綜上所述,中國教育面臨的是一種雙重的選擇:一方面它要以形成獨立人格作為它的主要價值追求;另一方面,在完成這項任務時又不可能不受到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的影響,中國教育所要培養的人,不可能游離于整個人類發展的邏輯之外,它也必定面臨把人推向共在型人格的發展使命。同時,在當前的中國,那種因個人主義無限膨脹而造成的種種惡果,引發的種種危機也已經明白地向人們警示著單子式個體的個人主義之路:“此路不通”。
當代中國所要培養的決不是單子式的獨立人格,而只能是共在型獨立人格。這種共在型獨立人格的特征可以歸納為以下各點:其一,它是一個獨立性的存在,而不是一種依附性的存在。他能以自己的獨立思考、批判精神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而不是順服、委歸于各種依附關系;其二,這種獨立性是以承認他人的獨立性,以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公正為其規定性的,正是在這種普遍獨立性的基礎上才能發展出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系;其三,共生性是一種新的人的結合關系,這種新的結合關系不是依附性關系的回歸,而是它的否定之否定。它既內涵著獨特性、多樣性的個體價值,同樣也顯示當代人在價值上的普遍相關性;其四,這種共生性也不是追求完全的同質性,它更多的是一種異質文化之間的“和而不同”。對于異質文化的理解、寬容、對話與溝通當成為一代新人的至關重要的品質。
中國的道德教育、價值教育所要走的也許是一條前人所從未走過的道路,它需要的只能是探索,是創造,是自覺的選擇。任務艱巨,任重而道遠!